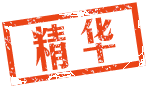|
个体精神进化论 作者简介:唐仲清,男,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副教授,律师,《黑白》杂志主编 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讲过,哲学起源于“惊奇”。还真是,只要你斗胆也来写篇哲学论文,用不了多长时间即会发现:平日里熟[视无睹稀松平常不容质疑天经地义的事物都会成为“问题”。更让人沮丧的是:用哲学思维方式去“思考”,这些问题越想越复杂,越想越无解。所以有人说哲学这玩意儿根本就是一门自寻烦恼学,没错!再则,要操哲学,还有个技术问题:大凡哲学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具有终极性的大问题,例如宇宙有无时间上的开端空间上的边际,上帝创生宇宙,那么上帝又是谁家生的娃娃,或者: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反正,这些问题都挺玄的(而且让人头晕);当你试图去描述这些命题时,又不得不使用抽象概念:例如:物质、精神、主体、客体、群体、个体、变化、进化,特令人绝望的是:哲学中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无法下定义的:最大的概念无法确定其内涵外延,也找不到此概念的对应物,所以身为古希腊最伟大哲学家的苏格拉底抢先宣告:“我只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从此哲学家拥有了天下无双所向无敌的无知;结果是什么?弄了半天哲学,似乎什么收获也没有,但似乎又隐隐约约收获了一点儿什么(是什么也说不太清楚),所以鄙人以为,哲学又可称为“迷糊学”。哲学命题必须用那一套抽象晦涩的概念术语来表达,否则,确确实实就没有哲学的模样,没有哲学那股子特殊的味儿。鄙人不幸也曾受过半吊子哲学训练,可惜慧根太浅,对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些个抽象哲学大师的砖著确实看不大明白(国内有些专家成天在比赛谁能看得明白,也许“尔学”专家们都知道这一典故:胡塞尔曾经光明磊落地宣称:本人早晨写下的文章到下午连自己也看不懂了。可偏有几个“尔学”专家说,胡塞尔自家看不懂,俺懂!而且美其名曰叫啥“客观主义阐释学”,可见,胆子小的人趁早别来碰哲学),鄙人总也改不了写文章要让人看得懂的坏毛病,还有至少自己个儿得要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这一陋习,可见,不是人人都能当上“尔”辈大师的。这些大师讲的话你就是看不懂你还不敢说不懂!大师不可能说别人不懂的话,只有别人听不懂大师的话!鄙人的开场白已经埋下一个伏笔,鄙人无心(也无能)玩空手道,但哲学,尤其是思辨哲学就这么个德性,当本文让读者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皮虚火攻心口吐鲜血时敬请原谅,鄙人自知不具有不许别人不懂的资格,你的不懂全是俺的错,鄙人这厢有礼了! 就普通词义大致可以这样阐释“个体”这一概念:个体是与群体相对的概念,是指一个个单独的个人。 问题是:如何阐释“单独”的个人界定进而“个体”:我们不妨来做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仿爱因斯坦的方法): A、个体可用特殊的姓名来界定 反驳意见:①人的姓名具有重复率,即使像俄罗斯人父姓母姓夫姓本人姓氏一大堆凑成一个人的姓名,仍可能出现重复;②人的姓名仅只是个文字符号,不足以标识人的本质特征。 B、个体可用形貌特征来界定 反驳意见:①现有科学资料显示,世上总有一个与你长得酷似的人;②如用形貌特征界定个体,那么个体这一概念即可扩张到动物甚至植物;或者反过来说,界定动物个体的标准也可用来界定人。 C、个体可用空间占有的特殊位置来界定 的确,人是一个物体,每一“个体”在空间中总是会占据着某个不可替代的位置(当其运动时,所占据的空间也发生变化),正如斯特劳森在《个体》一著中指出:“每个人的身体是以某种方式占据着相对于这个人的知觉经验的具体位置。……这个身体对于他作为具有各种知觉经验的对象来说,也是惟一的”。 反驳意见:①个体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空间占有,但哲学意义上的“个体”显然不会满足于这一界定;②身体不仅对他人,而且对自己来说也是惟一的,那么是否可以断言“个体性就是身体的惟一性”?但“人是身体”存在主词谓词矛的缺陷(因为主词如果已是“物质”,那么等于说“特质中的某个物体人是另一个物体(身体);如果主词是“精神”,那么等于说“精神”(非物质)存在中的某类别(人)是物质中的某一物体(身体),正如笔者前述,任何概念如果上升到“最高哲学”范畴都是不可定义的,既然不可定义就会出现许多几乎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非A是A这样的逻辑矛盾,当然,哲学家们有时候也把这种混乱状况尊称为“辩证法”),可见,用身体对空间的占据,身体的惟一性来界定个体仍然不尽人意。 D、个体可用感觉的惟一性来界定 正如萨特在其论文《自我的超越性》中指出“我总是能够把我的感觉或思想当作是我本人的”,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我”的某种感觉或思想是任何人都体会不到的。 反驳意见:①个体终归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感觉可能是真切的,但感觉却是非实体的;②感觉的惟一性只能由当事者本人体验得到,但他为要证明这种惟一性即需要将这种感觉表述出来,传达给他人,而他一旦试图表述和传达,必须使用文字和语言,而任何语言文字都具有一般性、概括性,简言之,任何词语对感觉的表述都会丧失感觉的惟一性,即使像普罗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那样精微的描述也无法表述出感觉的惟一性;③类似“牙痛”那样的感觉虽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某一当事人存在不可重复的联系,但是“牙痛”这种感觉却有着共通性,甲乙丙丁只会体验到自己的牙痛,但其感觉的内容(或特征)却可能是共通的,雷同的;既然感觉可能相似,那这感觉即使在某一时刻不可重复地发生于某个人(例如甲)的身体中,也不能用这种可能与他人感觉相似的感觉来证明这个人(某甲)的个体性。 E、个体可用思想意识的特殊性来界定 由于感觉具有只可体验难以言表的特征,而这恰好可成为其惟一性的保证(当然同时无法证明自己),至于思想意识的所谓“特殊性”就更加可疑了。 反驳意见:①思想意识的物质质料即语言文字具有一般性、共通性的特征;②在同一社会人文环境中生活,即使在那些标新立异者的思想意识中也有大量因袭大众意识的成分;③特定个人的自以为特殊的思想意识与相同抱负的人存在很高的重复率。 …… 上列思想实验还可以无限延续,正如康德的正题反题可以无限延续一样。但这ABCDE想必已让读者诸君领教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能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因为哲学家是善于提出一些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见:个体性确确实实是一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却无法精确地定义。中国古代人非常智慧地用神秘主义来解决此类疑难,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有魏晋玄学的方法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不好表达么,我便大有深意地微笑着说,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又如《易经》的魅力正在于它的模糊性,正因为模糊,大师们便可作死无对证的任意解释;另外,神秘主义相比理性主义还有一个情感特征,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都激动兴奋地被欺骗活动中,可见任何学术都可能导向娱乐。但是,严格意义的哲学总要努力进行更加精微的思辨,鄙人以为,即便是矛盾百出混乱不堪的精微的思辨也比神秘主义的逃遁更强,爱迪生试验了5000种材料都失败了,但他获得一个辉煌成就,告诉人们:这5000种材料不能用来作灯芯,用时尚的话来说,努力为自己作论证的(而非得象忘言的)谬误也是一种“知识增量”。 在界定个体时,必会遭逢“主体”这一概念。如以属种逻辑来划分,个体归属主体(因与主体相对的概念是客体,个体只要不能被归入客体(当然其身体也可谓客体),那它只能划归于主体),但在德国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看来,个体与主体仍有区别: 我们可以说,主体(和“我”)意指一个一般的东西,“人格”意指一个特殊的东西。“个体”意指一个单个的东西。 通过“我”(ich),每一个人都指向自己本身,就如指向一个主观的存在者(有别于一个现成的东西),但却并非必然地指向一个独一无二的主体。 个体的东西乃是能够从每一个普遍性要求中作为例外,并且从一个一般者那里断裂开而演绎出来的东西。 前列ABCDE思想实验已经提及,姓氏界定个体是不完满的,这一点,莫里哀的《晚宴的东道主》中的梅尔库尔与索西亚之间的对话可见: 梅尔库尔:谁去? 索西亚:我! 梅尔库尔:谁,“我”? 梅尔库尔的反问表明,他对于第一人称单数代词的虚弱的界定作用无论怎样都不满意:通过这个界定作用,为此与自己发生关系的主体之个体性并没有得到清楚明确的说明。某人——任何一个人——因此都仅仅把自己表象为主体: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这一个种类的样品,并与之同类。 弗兰克的分析对我们的启迪在于:主体易于被一般化,所谓一般化即指,主体所承载的自我意识完全可能全部或至少部分是群体意识,而任何时代的群体意识又都可能是内容相同相仿整齐划一无个性的。为什么后现代要宣称“主体死了”也许原因之一正在于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个体,无论其身体、感觉、思想、都应当是普遍性之中的例外。只有主体中那些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的特质的东西才有资格用来界定个体。什么是有特质的东西呢? 如弗兰克所述,“我”并不一定导几独一无二的主体,换言之,即使某一特定的个人以“我”的名义存活于世,但它主要就是一个“普遍意识”的承载者,那么,这一个我的个体性总是十分微弱的。可见,个体性从一开始就要求每一个人,不仅自己的身体与他人是分离的,在许多情形下还可能是对立的(就像恶狼一样面面相觑),而且更重要的是,为要创生、保有自己的个体性,我还必须在感觉、思想方面努力做到跟别人不一样:由此可以推导出:个体并非一个既定的存在物(作为单个的“物体”不足以用来界定其个体性),个体是我有意识创生出来的东西。感觉会受到身体所处位置的外在强制,用经典唯物主义的术语来说,感觉所具备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种种限制(当然),某位已故伟人曾经提出过“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流行歌曲注解为《跟着感觉走》,可见感觉似乎更具有真理性,又如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倡导“触觉是最可信赖的感觉”,这些命题意在说明感觉直接经验到外物,故而其可信程度更高),换言之,感觉虽然更能保证个体性所期待的“惟一性”,但存在两方面不足:1)感觉也许形形色色,但它不是个体的更高级的精神;2)感觉太易受外界条件所决定,缺乏自主性与稳定性。正如进化论的宣传家赫胥尼在其《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指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具有自发运动的能力,也就是说,人能无端自造出某种行为的原因,而这一点,受制于外界条件而生发的感觉则是无能为力的;由此可见,欲成为个体,得要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权威者说我们凭借改变我们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生活,鄙人则认为,我们意欲过上自己的而非社会替我们安排的生活,首先应当让自己成为个体,因为:个体性如此微弱的芸芸众生同样拥有“生活的外观”,有的似乎还自感幸福地生活着、生活着。欲成为个体,则须以个体精神进化为目标。精神进化当然也须以感觉为其演进之源泉,但感觉具有受动的、有限的、盲目的特征。因此,明晰的、主动的、目标明确的意识改造应是个体精神进化的主要内容。 之所以提出“个体精神进化”而没有提出“主体精神进化”,乃由于主体相对于个体而言是一个“类”概念,相对于个体的人格的“单个性”和“绝对的规定性”简直就是一个虚构,另一个原因则是“主体死了”。 宣布偶像死亡的大胆作法源于尼采,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此宣告宗教信仰(尤其是基、基督教)的消亡,并在宣布上帝死了(旧的价值体系完蛋了)的同时“重新估价一切”;后现代哲学家们胆子更大(在前笔者已经提醒过胆子小的人别来搞哲学),干脆宣布人死了、主体死了,意义死了,一切都死了,现在还没死的将来都会统统死啦死啦。关于主体的死亡,德国哲学家彼得•毕尔格在其《主体的退隐》中评价福柯《词与物》中对待死亡的态度时指出: 福科的这一文本真正言说的内容透过Promesse 一词,即一种希望、许诺,表露了出来。主体的死亡,对于言说的我仿佛是一个解放,将之从没有赋予他可以生存之处的构架中解放出来。 我既是运动的主体,又是运动的客体,它想从自认为是与不变的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形象中脱离开来。其后隐藏的思想是:我并不能自由设计自己,而是更多地服从于话语的和非话语的实践。 (福柯)主体一词有两重含义:借助控制与依赖而受制于某人,以及通过意识和自我认识与它的自我同一性联系在一起。 借鉴福柯对主体概念的阐释,可见个体同样不是一个自由设计的、既定而不变的存在物,个体并不因为“个体”这个用词的变化就能填补“主体”的空虚空洞;个体性必须通过“话语或非话语的实践”才能构建。由此可见,个体若欲为个体必须得进行精神之进化,否则即为一物体; 对人来说,即使对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来说,没有什么“纯粹的”、“与人生哲学无关”的认识,正如毕尔格在评价卢梭时指出: 追求真理于卢梭而言首先不是认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意义上的问题。 简卡尔的我清楚自己是一个般性的我,是理性处所,而卢梭感知到的我,最起码自传作品中的我,却是一个绝对的例外:“我敢断言自己与任何活着的人不同”。这一转向使得我的确定性具有了另一种品质,它的基础不再是理性的普遍性,而是个体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这个个体——这正是卢梭大胆行为充满挑衅之处——要求一种普遍性,即在一个堕落的文明中保持着自然本色的人(homme naturel)。 卢梭意下的“自然本色的人”当然不是原始的、落后于普遍文明的人,而是努力摆脱普遍的、堕落的文明,同时在其身上孕育着新的文明的身在现在时态的人,是活着的未来人(而非复古主义、新儒学意义上的活着的古代人),“自然”并非该词的字面意义,而是对抵抗现代文明抹煞个体性的一种言简意赅的强调。个体精神进化论坚决反对空泛的主体性,而主张个体自我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of selfhood );因为,正如德国哲学家在其《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指出的: 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的人不再是他自己的孤立的自我。个人融化在群众中,不复是他在单独自处时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个人在群众中成为孤立的原子,他个人对存在的追求被牺牲掉了,因为某种虚构的一般品质占据了支配地位。 要想把自己从群众中抽身出来进而构建其个体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独处,咱自己个儿一个人呆着总算是铁板钉钉的“个体”吧,咱要筹足了资金能置办一亩三分地,也学古代圣贤到大自然里做隐士去!晚年的卢梭、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统统都采用了退隐山林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当然这些伟人们能用这种办法保有甚至增进其个体性应该都没问题,但对一般人来说这种办法就不一定灵验了。因为身体的独处状况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上就保持了个体状态;因为“堕落的文明”和“大众意识”已经溶化在咱的血液里,逃得再远仍然属于“群众中的一员”。不难窥见,个体精神进化是一种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心理训练,还需要有意识地建立起专属自己一人独享的意识形态;只有精神足以同普遍性、大众意识、堕落的文明相对抗,你才真有力量从群众中抽身出来,才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并且心安理得的“个体”。 个体的形成,个体性的塑造必须有赖于个体精神进化,我们不得不对“精神”这一概念作一探究。 笔者在前已指出,哲学思辨不时都会遭逢“最高哲学范畴”,此类范畴往往又是不可定义的,“精神”也不例外。历史上,对“精神”的定义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1)关系论: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来下定义,经典唯物主义中最著名的要数列宁的定义,即物质是不依赖于人们感觉的客观实在,这种客观实在又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或者:精神、意识是与物质、客观存在相对的哲学范畴;2)属性论:该定义法的典型也许要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意识是大脑皮层的活动”;关系论并没有对概念下定义,只是言称精神不同于物质,至于精神本身为何物(是什么)却无从得知;属性论用“活动”来界定概念又与精神作为范畴应具有的“实体”性质不相吻合;与属性论相近似的另一定义法姑且可称为“功能论”,即精神是人所独具的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的能力;又如王晓华先生定义的“精神是身体的自设计功能”(参见王晓华《个体哲学》第17页),等等。显见,“功能”与“活动”之间只存在细微差别,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逻辑矛盾:如果精神仅只是物质的属性,其本身并非另一个“实体”或“存在”,那么“精神是什么”这个命题便不能成立,是一个“伪问题”,另外,运用科学方法来解释人,人的精神是否妥当,在有人看来也已成为问题,法国哲学家德日进神甫指出:“人类学,依赖物理学和生物学,也试着尽其全力解释人体的构造和它的生理机构。不过若把这些外貌放在一起,则所得的画像和实体却相距甚远。目前科学所能重建的人,也不过是一种动物而已”。(参见德日进《人的现象》第105页);由此可见,现象学将本体论问题“慧搁”起来确实是个明智之举,但囿于本文主题,既然论及精神进化,即使顺避了对精神下定义这个太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对此概念仍不免发几句议论。 1)正像“本体性”那样,对于每一个体来说,尽管精神具有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文字表述的特征,但每一个体却又真切体验到精神的存在; 2)精神的最精致的形式是语言、逻辑、思想,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科学文化知识越丰富的人其精神越是进化;也就是说,精神并不只是一个生物的、生理的、智能的概念,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将具有善德但没有多少知识的人贬斥为低级的人,同时也会把类似希特勒那样的天才推崇为精神进化的颠峰人物。 3)任何精神都无法脱离身体这一实体,但精神亦可成为支配身体的内在动力,可见,言称“精神是身体的自设计功能”只是指明了精神的生理基础,但没有指出精神的独立性,未能高度重视精神的独立性,既无法界定人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更无法阐释“个体”与“精神进化”。正如雅斯其斯所言:“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 4)为要理解精神进化,必须假设精神是一种不同于物质的“实体”(这一点经典唯物主义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时就已指出,“大胃分泌思想”就是庸俗唯物主义,因为它由此否认也物质和精神的对立,当然,经典唯物主义并非笔者这样“假设”,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声明精神不同于物质——对此观点的批判性分析参见《黑白》2006年第二期《中国人的日常意识批判》),同时亦应注意:虽然我们可以依据一定标准去确定某人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精神状况”,但也应当十分清楚:精神是一种最易变化的存在,谁也难以保障精神进化的“定型”。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进化”概念。 动词“进化”源自拉丁词“evolvere”,本义是铺开或者展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指明,生物学的任务是要证明: 生活在世界上的这些数不清的物种是怎样演变出来的,它们是如何在结构上和在互相适应方面达到了简直令人称羡的完美程度的。 玻意耳对自然万物完美的合目的性的解释是:存在着一位“为时钟上紧发条”的上帝,上帝一开始就制定了法则,其后,自然界就按照他颁布的那些不变的原则行事。显见,与玻意耳同类的有神论者们都没能解释出合目的性是怎样在自然界中逐渐形成的,而把这一合目的性的设计归法为本身更加无法解释的上帝,而且是人把自己对合目的性的理解强加给了上帝。达尔文对进化的解释当然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描述,提请注意的是:照英国学者贵比恩所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进化》中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说:达尔文从来没有认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所发生的修改,必定包含有在某种绝对意义下的进步或前进的意思。按照他的理论,生物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经常条件下,都将会与之相适应。从根本上说,达尔文简直就没有谈及斯宾塞所猜想的那种生命进化,后者指的是一种不断建造自己的运动,生命可以通过自身所具有的那些能够进行动态自发组织的性质而进入到更新的、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按照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社会进化的过程,正如生物进化过程一样,生存竞争的原则起着支配作用。斯宾塞认为人类有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之区别,优等民族就是最能适应进化规律的民族,即最符合于“适者生存”的原则的民族,因而他们应当成为一切民族的天然的统治者。而劣等民族则由于他们不适应进化规律,只能受优等民族统治,必然要动优等民族淘汰(参见刘放桐编《现代西方哲学》第62页)。笔者认为,最能体现“低级到高级发展”之进化观念的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形态的理论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以下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衡量社会历史形态的标准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生产力;二是道德觉悟(广义上也应包括社会制度方面的“进步”,如不再有剥削、压迫等等)由于自认已掌握了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自信豪迈地宣布“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是,自从低级—高级进化观产生以来,就有人持反对意见(例如卢梭就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导致了人类不平等、罪恶、等等),直至1995年,美国哲学家杰里德•戴蒙德仍然宣称: 我从不认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对于人类是绝对的好事情。今天的大多数人是否真的比远古的大多数狩猎者—采集者生活得更幸福和更健康,这其实是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谓的自我毁灭的现实危险,肯定要比1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大得多。(参见比恩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第52页)。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往往需要“设定”某些基本的价值观才能够构建理论,又戴着有色眼镜去“反映”社会事物。例如,低级—高级之进步观念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前提性的假设。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在任何环境下都具有适应性,如果以己之心度他人之量,我们甚至也可以推断生物在任何环境下也会觉得“幸福”,反倒是自以为进步了的人类会有无尽的烦恼。如果认同这种貌似客观的虚无主义,可以说,所有社会科学都丧失了存在的资格,进而对于社会的发展任何人都没必要瞎操心。对此,笔者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出“动物也许经人更幸福”“愚人可能比智者更快乐”这类命题的,多半是些学者专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从不提这类本身无法证明的问题。笔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尽管至今没有得到历史的验证,但对社会发展进化的理论模式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即是说:社会总会(也应当),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至于历史形态的称谓则是无关紧要的(也许马克思憧憬中的共产主义会在美利坚首先实现,那都是有可能的)。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低级—高级的进化观的真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或者说即使像马克思那样的天才人物,其几十年的短暂一生也不可能研究大千世界的所有问题),该理论始终忽视了个体,个体精神进化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终极性,也就是说,忽视了个体精神进化而以“社会”为叙事主词,相当于虚构“主体”的宏大叙事,而社会的单细胞却是一个个自身应具有独立性的个体,所谓“愿做革命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即是对个体性的彻底否定,因为镙丝钉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而只是革命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社会变革可能成为个体精神进化的事半功倍的外力推动,但问题是:社会变革的方向目标又总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规划设计,如果将个体精神本身的自发进化的需要置于微未之地位,其结果便是个体的精神自觉被盲从所取代。希特勒凭其狂热演说会赢得数千万人的拥戴者,正是德国人民集体丧失个体精神自觉的恶果。个体精神自觉最通俗的认知模式是:“我认为是对还是错”,而不是“你说得对还是错”。 个体精神进化是落实每一个体的事业,其具体方案只能由本人来制定,但依笔者之愚见,个体精神进化仍然存在共通的目标,那就是:1)反抗愚昧;2)追求善德。 鲁迅先生以批判剖析“国民劣根性”为其毕生之事业,其最有名的带有纲领性的名言是:我在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看见歪歪斜斜地写着两个字,那就是“吃人”。笔者以为,中国历史之所以会成为食人的历史,其最深层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愚昧”。吃人者要吃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倒是愚昧的被吃者不但浑然不觉,而且还能陶醉在自己皮肉被烤焦散发出来的肉香味之中。中国历代统治者都精通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统治术,而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贡献给中国人民最智慧的人生哲学则是“绝圣去智”。真是太深刻了!因为愚昧能战胜一切痛苦,因为愚昧所获得的最丰硕的科研成果就是麻木甚至无感觉;怪不得中国历代统治者们发自肺腑地感叹:“中国人民,真好!”还有些领袖人物对这样配合统治的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临终之前还忘不了讲一句“我爱我的中国人民!”被夸奖被垂爱的人民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激涕零。但在鄙人看来,这一主一奴组建的和谐社会从根本上是建立在老百姓的愚昧无知之上的,人民不必过分地指责统治者们愚民,而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反对自己的愚昧。只有人民不再愚昧,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愚昧,统治者才会黔驴技穷折戈沉载。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廓尔曾说“生活是人一生的任务”“人必须敢干成为个体的人,只有这样做,人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笔者以为,要想成为个体的人,只有在抓紧进行精神进化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个体的人,才能像克尔恺廓尔那样有资格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这个个体”,而不只是自己的姓名。 个体精神进化的第一步就是反抗愚昧! 从生物学的角度观察,个体发育一般指多细胞生物从受精卵开始直到发育为成体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细脆分裂、器官形成、性成熟等阶段。人的生命首先是肉体的发育,但人的生命之异于生物还需要精神的发育与进化。肉体的成熟并不必然伴随着精神的成熟,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痴长”的危险。在人类精神现象中有一种“愚昧满足感”的怪现象,这种心理现象在理论家那里便成为智者多忧愚者多喜的意识形态,但鄙人以为,反抗愚昧作为个体精神进化的第一步同样是人一生的任务,因为生而为人,除了肉体会按自然规律不必操心地痴长,还应当有意识地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进化,要不然简直相当于披着人皮的牲口。这话说得有些难听,想必会遭到“人生而平等论”者们的激烈反对,但是,尊重自甘堕落者的这种尊重是真心的么,否!这是对人民高度的不负责任,是愚民统治术的合谋!狡猾的在上位者私下里期盼着人民的智能懒惰,只有让人民成为了牲口才方便“牧民”哪!或者,赏你们一句“人民万岁”那样的口号亦可。欧仁·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是针对万恶的剥削制度,但对每一个个体需要唤醒和开发的精神领地同样可以对它们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个体精神进化的第二内容即是追求善德。在此有必要声明:反抗愚昧与追求善德并无时间上先后相继的顺序,并非要将愚昧打翻在地了,接下来才去追求善德。可以说,反抗愚昧和追求善德是同时并举,相辅相成的进化手段。 个体精神进化论十分强调精神进化的“自发性”,该处之“自发”并非与“自觉”相对的概念,而是指谓:精神进化的一切需要都应当是个体的发乎于内的自发需要,而非将一己之身当作“外在道德观念”的工具来役使。举例来说,性道德(外在道德观念之一种)告诫我们,嫖娼是一种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是一种既不尊重妇女也不尊重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滋长卖淫妇女不正当生存方式参加财富再分配的行为,我如果听从这些道德训诫不去嫖娼,那我最多算是“践履”外在道德,但如果,我根据道听途说耳闻目睹或者亲身经历体会到,例如:嫖娼极易染上性病,但我既没有医治性病的充足经费,也没有打针吃药的忍耐精神,再加上我这人做事情受不了一点儿分心因素,上半截在做形而上学的沉思,老是担心下半截鼻青脸肿流血流脓,这个,我真受不了——鉴于种种因素,我便采取逐量减少几近于无的方式,最终放弃了嫖娼这一热爱生活的不道德的娱乐活动。只有对善德的自发需求才是可靠的,因为对善德的自发追求是我(I)与我(me)的真实的内在关系。什么是最真实的生活?那就是自己对自己说实话,说的实话自己真心倾听的生活;所以,真诚,而不是被骗或自欺,乃是个体精神进化的必具条件。而所谓真诚,首先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德,鄙人以为,真诚是一切智慧中最大的智慧,只有对己真诚,才能认清本我,才能追寻到深入骨髓的举世无双的简直就是超验的幸福感。当然,这种幸福感的真切体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没有,但这种幸福感肯定存在,我们虽无法体验却知道它的存在。可见,追求善德的准确含义并不限于“做一个道德的人”,而是要努力成为一种更完善也更幸福的人,这是一项孤独中的默默无闻的事业,但我将是这项事业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我成为善德中人至少不会再危害社会治安,他人也可受益)。正如美国哲学家苏珊·李·安德森评价克尔恺廓尔那样:甚至早在挣扎迷茫之时,克尔凯廓尔就已经知道惬意生活的关键不在于别人的赞赏和认同,而在于不断地认识自己、不断地努力去发现自己能够变好: 在认识任何别的事物之前,人必须认识自己。这样,只有在内在地理解自己、从而看清自己的道路之后,人的生命才能获得平安和意义……在精神世界里,首先最必须做的是,在第一道光线到来和阳光照耀之前工作段时间。(克尔恺廓尔《日记》1835年) 萨特在他那篇著名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指出: 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颗花椰菜。 但人只有在自觉进行个体精神进化的前提下才可能对自己的主观生命作出规划。而要从事精神进化,人必须首先培养自己的反省能力。德日进神甫对反省在认识自己的实践中予以遍度评价: “反省”乃意识获得转向自己和掌握自己的能力,认自己为具有特殊的统一性与价值的对象——不再只了解别的东西,而且了解自己;不只知道,而是知道自己知道。这是人从内在的深处认识自己,从前分散的知觉与行动此刻才有一个在这中心中,一切印象与经验融事为一,由是而认识自己的组织。 抽象、逻辑、理智的抉择和发明,数学、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