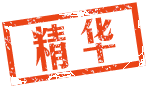九、此刻
看你的手,我的孩子。
——一位越南母亲说
我的手存在七十万年了
“我仅仅是一个延续,
我从来不曾死过。
如果我曾经哪怕死过一次
我的手怎么会还在呢?”
我是个一直诞生的人……
天下有花开般的劳作
满眼尽是大自然的命运
没云,我们哪来水喝
没因陀罗网,哪来无常
“爸爸,请别抱怨无常,
没无常我怎么能长大?”
他不会想着他会长大。
他不会想着他不长大。
他不会想着他已长大。
“上个世纪我曾是谁:
我只得见今天的我。”
唯当下使我活在当下。
“上个世纪我曾是谁:我只得见今天的我。”见何家炜译《灵光集:兰波诗歌集注》,商务印书馆,2020,第148页。
2019年10月26日
十、一把椅子
我记得椅子这个词。
我想说——我只是再没有兴趣了。
——露易丝·格丽克《阿弗尔诺》
但我很有兴趣,
一把椅子有世界的一切
树木、森林、木工、太阳、
云、水、风以及我们的屁股……
椅子,我们天天坐的椅子
椅子,几何与抽象的椅子
如果没有椅子就没有世界
否定椅子就否定了宇宙的存在
“如果我们成功地毁掉一把椅子,
我们也足以毁掉整个宇宙。”
谁说的?一个越南禅师?
当然,这也是我想说的。
无边的无始亦无终的椅子,
它坐进了纳博科夫的冬天,
坐进了张枣的冬天,
也坐进了我们的冬天。
可很快,有个美国诗人说:
“世界上所有椅子都帮不了你。”
但百年前,佩索阿却说:
“基督教是关于椅子的一场大梦。”
2019年10月28日
十一、两次对话
如来死后会发生什么?
佛问阿奴逻陀:如来可以色身见否?
不也,世尊。
如来可以色外见否?
不也,世尊。
如来可以受、想、行、识见否?
不也,世尊。
两千五百年后……
有人问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电子是否保持同一位置?
不是。
电子的位置是随时间改变的吗?
不是。
电子是否静止不动?
不是。
电子是否运动的?
不是。
2019年10月28日
十二、人身难得
1
我写诗有那么多条原因
其中一条会令你感到奇怪
“我写诗磨损着动物们的铁蹄”
我活着,我天天要运动——
但医生说:为防止哮喘
唯一良药是静止不动
我吃蔬菜,就是吃太阳
我喝白水,就是喝云天
我走路其实是在练习呼吸
2
从云到水到光到树到纸
一页纸里包含多少事物?
“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他生气需要多长的时间
多少天?多少年?可消灭
愤怒就是消灭你自己呀
借问驾车人要到哪里去?
驾车人说不知道,问车吧。
不二法门也是方便法门?
注释一:“我写诗磨损着动物们的铁蹄。”见金斯堡诗《序言:北京即兴》,《金斯堡诗全集》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118页。
2019年10月28日
十三、废话诗
1
太平天国欲造新奇美金陵
民国之美则结束于中山陵
讲堂抛弃了都市来到森林
自然成为我们幽静的导师
2
爱走路的人专注于每一步
他不会盘算要走多远的路
持戒最严的人将不敢行走
因为行走就必然踩死虫虫
3
你今天执着于当下并不能
保证你明天就不向往未来
在画家眼里这是一碗米饭
但我渴望的却是一双芒鞋
4
世上有比写诗更妙的事吗
人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要的
想想当年你如继承了王位
现在你必错失骑牛的滋味
5
有事无事尽管写句废话吧
你怎么知道他爱吃卤鸭子
那敛翅的瓢虫刚打完麻药
医生就要为它做开­手术
2019年11月8日
禅意与诗韵的心灵幽会
——柏桦先生《聆听佛陀》组诗品鉴 邓万康/文 诗人柏桦先生的《聆听佛陀》组诗,似静谧夜空中闪烁的星芒,幽微而深邃,将读者引入一个充满灵慧与哲思的境界,于无声处触动灵魂的弦索。 灵慧意象:禅意的具象与心灵的投影 旃檀佛像是组诗中最为瞩目的精神坐标。它从西土启程,“旃檀佛诞生于西土 / 在那里住了 1280 年 / 后自行离去,开始漫游……”,仿若一位超凡的行者,在历史的风尘中跋涉。在龟兹的古老土地上,它或许见证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异域的风情与信仰的光辉在其周围交织缠绕;步入凉州,那粗粝的风沙与质朴的民风,成为它传奇经历中的一抹厚重底色;抵达长安,在盛世的繁华与喧嚣中,旃檀佛被赋予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成为宗教与艺术、信仰与追求相互辉映的焦点;而在江南的水乡泽国,它又融入那温婉细腻的人文气息里,如同一朵盛开在尘世中的圣洁莲花。其辗转于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见证寺庙的兴衰荣枯,每一处遗迹都是它信仰之路的注脚,每一段传说都是它精神传承的回响。它象征着信仰的坚韧不拔,犹如灯塔在茫茫尘世的波涛中,为逐梦灵魂指引方向,在时光的长河里,始终散发着恒定而温暖的精神光辉。 呼吸意象则如生命的隐秘脉搏,在《呼吸颂》里奏响独特的禅韵。“呼吸于呼吸,步行于步行 / 吃饭于吃饭,穿衣于穿衣”,这看似平常的生活举动,被赋予了深刻的禅意内涵。呼吸,这一生命最基本的律动,成为连接身心与宇宙的微妙纽带。在一呼一吸之间,个体仿佛能够感知到宇宙的气息在身体内流淌,使日常琐事升华为神圣的修行。每一次吸气,像是吸纳天地间的灵气与智慧;每一次呼气,仿佛释放出内心的杂念与烦恼。如此,呼吸意象构建起一个宁静祥和的心灵禅境,让灵魂在尘世的纷扰中寻得一片栖息之所,于喧嚣中聆听生命的本真之声。 诗韵天成:简约与深邃的诗意协奏 诗语似精炼的禅语,简洁却蕴含无尽深意。如《佛陀说》中所云:“佛陀说 / 岁月并不是得道的保证。 / 有几样东西是不容低估的—— / 年幼的太子、小蛇、 / 一点火花和年少的僧人。”寥寥数语,摒弃了繁复的修饰与冗长的叙述,以一种近乎直白却又极为精准的方式,将深邃的哲理呈现在读者面前。“岁月”与“得道”的关系被轻轻挑起,引发对生命历程与精神追求的深刻思考。而“年幼的太子”或许象征着纯真无邪的初心与与生俱来的慧根;“小蛇”可能隐喻着灵动多变、难以捉摸的世事无常;“一点火花”恰似瞬间的灵感或顿悟之光;“年少的僧人”则代表着对信仰的执着与热忱。这般简洁的表述,如同空谷中的一记钟声,振聋发聩,使读者在瞬间被击中内心深处的思考触点,开启一场心灵的深度探索之旅。 节奏韵律方面,《抄安般守意经之十六口气息观息法门》宛如一曲与呼吸同步的生命乐章。诗行的长短、音节的错落,皆与呼吸的节奏巧妙契合。诵读之时,仿若能够感受到气息在诗句间缓缓流淌,如同生命的能量在身体内循环往复。每一个停顿、每一次抑扬,都像是心灵在呼吸的引导下,对生命的节奏进行着细腻的感知与体悟。这种独特的节奏韵律,使诗歌超越了文字的表意功能,成为一种能够直接作用于身心的艺术力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沉浸于一种宁静而专注的精神状态,仿佛与诗人一同进入了禅定的境界,在诗意的海洋里,领略生命韵律与诗歌艺术的完美融合。 尘世绘卷:时代与心灵的诗意映照 《阿弥陀佛》犹如一幅时代的长卷,在历史的横轴与心灵的纵轴上展开斑斓的画面。诗中提及张爱玲与“三高”,那是一个时代物质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微妙缩影。在繁华都市的诱惑与压力之下,人们在享受物质丰富的同时,也面临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危机。张爱玲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都市人群的一种典型代表,她的生活方式、情感纠葛以及身体的病痛,皆反映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性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挣扎与徘徊。 知青的经历则是时代浪潮中青春热血与命运无常的真实写照。从女知青丁若兰在蚊帐里的哭泣,到男知青们在串联途中的种种遭遇,以及边境线上的冒险冲动,每一个场景都饱含着青春的激情、理想的憧憬以及面对现实困境的无奈与迷茫。这些知青们的故事,如同镶嵌在时代画卷中的璀璨宝石,虽然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但汇聚在一起,却构成了一幅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与青年心态的宏大图景。 公审死刑犯的场景,宛如一道冷峻的闪电,划破时代的天空。它代表着社会秩序的维护与正义的伸张,同时也暗示着在时代变革过程中,社会道德与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与重构。这一严肃而庄重的场景,与诗中其他元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张力与思想碰撞,使读者在感受时代脉搏跳动的同时,也对社会正义、人性善恶等问题产生深刻的思考。 玻璃诗人的出现,则为这幅时代画卷增添了一抹清新而灵动的文化色彩。他们以独特的诗歌创作视角与表现手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着诗歌艺术的新路径。这一文化现象反映出时代对文化创新的包容与鼓励,也体现了诗歌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始终能够成为人们表达内心世界、反映社会现实的有力武器。 柏桦的《聆听佛陀》组诗,通过意象的深邃寓意、诗韵的精妙构建以及对尘世万象的诗意描绘,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心灵深处、感悟禅意与生命真谛的大门。在这扇门后,是一片宁静而广阔的精神天地,等待着读者去驻足、去沉思、去体悟,让灵魂在诗的滋养下,获得一次难忘的精神洗礼与升华。 2024.12.06 邓万康,诗人兼事评论。1964年生。成都人。著有诗集《浪漫黑与白》《流水警醒》两部。主持《汉诗探索》公众号;并主编《风向标》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