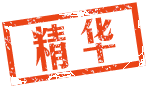|
|

楼主 |
发表于 2025-2-20 09:09:49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原采访虹影
关于伦敦:
1.李:您曾经在伦敦居住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也曾说过,“伦敦这个城市就像是情人”,是不是正是这个像情人一样的城市给你的写作增添了许多灵感,才让您写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来呢,请您给我们谈谈你眼中的伦敦好吗?你在伦敦的生活状态?
虹影:伦敦是迷宫,永远远距离面对每一个异乡人。那是一种很孤独的隐居生活。排开配合欧美出版社做宣传我的书的份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绝见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几个极亲密的朋友往来。清早起来将地板清理一遍,打扫卫生。平常,做菜、养花养鱼,花园里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梨树我走时都开花了,鱼池里荷花都冒出芽了。现在到了北京的家,一个人坐拥“书城网城”,一个人对墙打兵乓球。
在伦敦我的书房是个白色阁楼,夜里一打开大斜窗,全是亮丽的星星,我知道中国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国。所以带着这种感情,想象力更丰富,发挥得更自如,没有什么限制。这是跨越时空的写法,也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行为。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从80年代离家到现在,可以说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十年,经历过很多奇事怪事。对写作者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却不同。如同我看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国际新左派已经开始征求签名,反对进攻阿富汗。我认为西方不会满足于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个人。俄国很积极报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决整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对于异乡者,这就是一个切身大难题:英国许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帮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经死在那里。英国穆斯林社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大题目,暂且不谈。说小题目:十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你为哪一个队欢呼,就是哪国人”。这个“泰比特测试法”还真难处理。当时泰比特到伦敦大学演说,汽车刚进校门,就被学生包围起来猛踢猛砸。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不用拳脚,而是用战争。哪怕这次战争过后,“泰比特测试法”依然会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巨大问题,与过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锁国界。无论《阿难》还是《K》都是写这冲突,写我们内心深处的“泰比特测试”。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现在已经是对抗势态。白种人对伊斯兰的恐怖,以后可能还有对黄种人的恐怖,会变成顽强的潜心理。欧洲的白人,自从多佛事件、澳大利亚船民事件之后,对“移民”两字,谈虎色变。但是没有移民,哪来现代世界?海关能挡住思想?
2,李:听说您非常喜欢小动物,也因为在家在伦敦的郊外经常能看到火红的狐狸,觉得自己性格当中某些特征与它相似才给自己的博客起名为——“火狐虹影“呢?
因为狐狸不为人所豢养,爱自由。 您是个酷爱旅行的人,你觉得旅行给你而言,最大的诱惑在何处(风景、异性还是民俗)?艳遇,发现新事物。如果用一个地方来形容您本人,您觉得哪个城市与国家与您的性格最匹配,或者接近您?
虹影:在我许多作品里都有这种“童年记忆”,但并不是“个人化迷恋”。比如《孔雀的叫喊》和上海三部曲里,都有对身世的探求,对家的执着和热爱。在上海三部曲里,我抓住了上海很边缘的女性,而且是实际存在的女性,《上海王》,有一种王者的姿态;《上海之死》有一种悲剧之美;《上海魔术师》里兰胡儿说她恨这个城市,不如说她爱这个城市,如果她和加里有后代的话,他们的后代会回到这个城市,带着他们父母的故事。
对于这个城市的记忆或眷恋,来自我骨肉之中,也是我对我父亲的一种怀念,或是对家乡重庆的一种怀念。我写了布拉格、纽约、伦敦或者武汉,其实都是为了再现重庆那个城市在我童年中的记忆和认识而已。
3,李 您是一直在流浪并寻找自己“心灵故乡”的人,据说到如今都没找到,您心目中的“心灵故乡”是什么样子的?
虹影:心灵故乡永远在他方,如同兰波所说的。有书桌还有红狐。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那儿,一切和这里不同,那些鬼怪实际上都是与这个世界相处不了的人。他们彼此性情相似,不必用人造的装饰包裹起来,一人拥有一个小小的岛。我划舟访问他们,沙滩便是纸,足迹就是文字。
4.李 我们都知道你曾经获得英国华人诗歌比赛的一等奖,长篇《K》在意大利获得罗马文学奖。在伦敦和罗马领取奖项和在国内有什么不同呢,能分享一下当时获奖的心情以及经历吗?
虹影: 罗马奖(Premiero Roma),有“意大利的奥斯卡文化奖”之称,以六年为期,涉及领域包括文化、政治、文学、历史、医学等,影响力覆盖全欧洲。今年的获奖分文化和平、电影剧本奖、电视栏目主持人奖,历史学方面的奖,还有文学奖,获奖名单上,除了在几位意大利本国卓有建树的文化人士,只有两个外国人的名字。其一是今年四月刚刚谢世、但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教皇保罗二世,其二,是罗马奖首次给一个中国作家:因《K》而获文学奖,也因我的自传《饥饿的女儿》在意大利的广泛影响,深受注目。七月一日晚上九点半,颁奖席上坐着由意大利前首相、著名教授、影视评论家等十四名知名人士组成的主席团评委。三千人参加,男女衣服丽都,整个夜晚出动了警察,指挥道路,斗兽场里外都是黑衣警卫,电视转播,记者们摄影师在一旁。有意大利公主Donatella Chigi Albani Della Rovere出席,教皇保罗二世四月去世,由红衣主教来代领,他还带来现任教皇的祝贺。
有军乐团在台上吹奏的图:仪式开始前奏意大利民歌、国歌和欧盟歌。
典礼结束后,由Donatella Chigi Albani Della Rovere公主在她附近的庄园里的CLUB,给酒会宴请特殊嘉宾。典礼从9点半开始,到11点半结束。晚宴从11点五十开始,持续到凌晨。
我和我的意大利出版家都饿了,但他一直很绅士,小心翼翼地替我提着包装好的奖杯,一个1750年的花瓶,还替我拿着鲜花,他比我还高兴。他两次重复对我强调:“虹影,你是和教皇保罗二世一起得到奖的唯一的女性!”
第二天我在旅馆,打开意大利的报纸,一看:我的照片在教皇照片的下面,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感觉。
在授奖词上,评委会认为“虹影作品撞击人心,具有不畏世俗的勇敢精神和高超的艺术手法。”领奖前给我两个问题,一是我《饥饿的女儿》里对长江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二是作品里性爱描写秘密是什么?后来上台领将时问题主持人临时变为:“你对中西方的看法?你作品中的情爱描写,尤其是房中术的秘密是什么?”我说 我在中国成长,在西方生活了十四年,这两种文化很不一样,我很难在中国得到这样的奖,虽然我爱西方,但我更爱我的祖国等等。
我有幸夹杂在两个文化之中,体会到两个文化的不同,并把其中最极端的东西用一个爱情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本书也最使我费尽周折。我花了四年时间在官司上。而且吉林法院还因为《K》一书中的“性描写,太淫秽”永久禁掉,处罚我赔款和公开在杂志上道歉。
很多人会认为西方对道家房中术感兴趣,其实在中国,人们对此也不了解,也很好奇。我在国内很多大学做演讲,大学生们根本不知道素女经、房中术。如果研究道家房中术,人们会发现,他们一直在谈论的“女性中心主义”爱情观在中国由来已久,不是西方的新近产物。《K》就是把中国这种特色文化介绍入西方的。西方无法理解房中术,就像他们不理解中国式的爱情,和中国从不进行AA制的婚姻一样。
5.你是在国外逐渐被大家所熟知后才被国内的读者更为了解的,这种现象在文坛比较少见,你觉得产生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虹影: 40岁后突然成了这么一个“是非”之人,很多人只是传说我的官司、包括是“美女作家”而不会去认真了解我的作品,有记者问我:你相信这也是命运的一部分吗?
我说,是的。那年一个朋友看见《阿难》出来,他说:虹影,我还以为你已经被打死了,你不可能再写东西,“因为,你不可能抽出时间来,你不可能有这样的精力,像你这样的性格的人,你肯定就整个陷进去了。”我说我不可能,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知道我的命运是这样的,我就做了一点抗争,我作了一点努力,虽然这个努力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我做了。我就是想要给他们看一下,我依然能够写,而且我想10年或者20年后如果我不在了,当别人回忆我的时候,最好别写这个官司,尽量来说我的书。
我现在惟一能够证明我自己的,就是我是个优秀的作家。我想,我不吭声,熬过今天、度过明天我就有后天,我只要活下来,我就肯定有一天会比现在过得更好。就是有那种狠劲儿在里面,我不会屈服,我知道在整个一生当中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想我咬着牙就可以顶过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