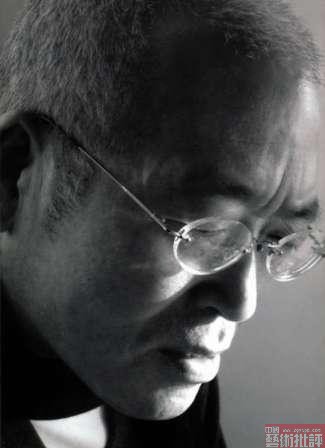
岛子像
摘 要
后现代主义在其历史化的过程中显现出日愈清晰的总体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现代性的否定,而对创造性的推重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艺术在美学意义上承当了作为文化思潮的超越性,不仅多视角、非逻辑地表达思想和观念,且积极创造新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方式,后现代艺术美学的特征随之得以矗立。
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的同一性。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本体论。从后现代艺术美学意义上来理解“方法”,则主要是指从艺术创作实践、艺术批评实践把握现实,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式的总和。正是“方法”形成了特征,特征使本体可见、可识、可道。
本文据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形态与现象的阐释,归纳其美学特征,从中分析出诸多能够显现本体的方法,力图认知其发生的义理与发展的图景。
ABSTRACT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postmodernis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lear after so many years of development, whil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s the denial of modernity represented by the emphasis of creativity. Postmodern art not only expressed ideology and ideas in multiple angles and multiple ways but also creates a new life space, pursuing a new life mode and a way to express life freely.
There is somehow a connection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noumenon, that’s to say, methodology cannot exist without noumeno while there is no “pure” noumeno. To understand “method” in the angle of art aesthetics refers to grasp the reality through artistic creation and artistic criticism and then to realize the summation of approach, means and mode to reach some aim. It is such “means” formed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racteristic makes noumenon visible and also makes it become something we can discuss.
To realize the argumentation the reason why postmodern art appear and its developing prospect, the paper gets some means that can be used to visualize the noumenon through expatiating the postmodern art phenomenon, concluding it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关键词
后现代艺术美学 不确定性 解构 寓言性 身体返魅 伪后现代主义 多元主义方法论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art methodology Indeterminacy Deconstruction
Allegorize Enchant to body False-postmodernism Pluralist methodology
引 言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西方出现了半个多世纪,进入汉语世界的已将近30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强劲趋势更加显示出后现代时代的特征,从精神价值体系到大众日常生活,从哲学、艺术、教育到跨国资本、电子媒介、流行时尚,举凡各类事物,无所不及。后现代主义内部的推进者、研究者姿态纷呈,异见迭出;而在其外部,坚持现代性保守立场的批判者、否定者以及众多把后现代主义简单化、妖魔化的憎恨者、讨伐者,则以反作用力的效能使其思潮跌宕起伏,气象万千。后现代主义能够葆有普遍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与后现代性——作为后工业、全球化和后历史社会之同义语——这一宽广的范畴互涵互涉。后现代主义不仅远未消弭,反倒在其历史化的过程中塑造出自身的总体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对现代性的否定,诸如否定一元论、独断论、机械论、父权制、历史决定论、纯粹理性,并力图摈弃和超越个人主义、经济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是在这些部分的否定而非整体决裂的基础上,后现代艺术美学范式随之得以矗立。
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化、多样性和开放性而摈弃封闭性、先验性、党同伐异及其绝对真理。相应地,肯定、倡导及摈弃都是为自由选择和创造开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由是,对创造性的推重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后现代艺术在其美学意义上承当了这一文化思潮的超越性,不仅多视角、非逻辑地表达思想和观念,且积极创造新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方式 ,所谓“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人生劳作的主要乐趣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不同于作日的另外之人”(福柯)。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将艺术从形式的藩篱、政治工具的钳制、消费主义的蛊惑解放出来,回到是其所是的身份。现代主义艺术之为“现代”,是与其排除更大范围的文化所具有的流行美学、社会学、伦理学和道德规范程度相联系的;与之相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质是,艺术家和受众共同接受具有交互且持久的兴趣的主题、承认艺术的所有作用的意愿。如同在整个现代性中那样,存在的独特性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即我们时代的“存在意义”,将优先并明澈地在审美体验中敞开。
观念以知识为依托,观念的转化依赖于知识,任何观念都是知识孕育的结果,以知识为基质和立场的差异才是创造的起点。然而知识必须建构于方法,并运用方法去获得。方法也不等同于技艺或技术,任何方法的运用实际上都含有特定的观念,未经反省的观念,便会凌空蹈虚。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才发现了解构论、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话语,逐渐打开经典学科的壁垒,开始用“方法”去替代哲学的世界观。后现主义观念产生之时代背景和它自身信靠的知识本体,使其美学观和创作手法与以往的艺术思潮、流派和风格都有明显差异。后现代艺术美学即后现代艺术哲学,它转换了美学所充当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色,游离于19世纪以后的传统哲学体制和审美范式,取消传统美学人为假定的僵硬界限,特别是取消美学与非美学的严格区别。因此,现代性美学所维护的特权地位,诸如审美的纯粹性、自律性、天才论、再现论、典型论、乃至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都遭到瓦解、疏离或转换的命运。由于不存在统一的永恒不变的美的标准,那些想以一种特殊的美学观点来定义美学和艺术的企图已被证明是不合法的,美学不是传统理论的囚徒。因而,作为一门传统的哲学学科,它已经过时且了无生气。美学的形而上学本源已经破产,审美标准对于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理论的支配性干预已经失效。在传统美学终结之处,衍生、演变出众多艺术门类或文化的批评理论,形成艺术美学的新生态。同样,美学家的身份也随之变换,在“视觉”或“图像”转向之后,随同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的崛起,由一个面壁虚构美的神秘本质并试图为艺术立法的艺术哲学家,变为一个内行的艺术理论家或艺术批评家。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在后现代条件下积极寻求普遍的、跨文化的乃至超人类的艺术、文化和生命特征的真实意义。同时,美学作为研究艺术的方法仍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就在于,艺术是人类本真的存在方式,美则是艺术必须关怀并不断质疑的价值理想。后现代艺术美学的意义与价值,也还在于新的思维方法、新的创作方法的提出。
在后现代艺术美学意义上来阐释 “方法”,则主要是指从艺术创作实践、艺术批评实践以及艺术史料把握现实,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式的总和。正是“方法”形成了特征,特征使本体可见、可识、可道。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的同一性。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本体论。尤其后现代艺术本体意义并不凝固在某种统一定律之内,存在的只有变化的意义。我们只能进入具体的艺术现象、艺术批评话语、艺术作品,通过辨证地使用后现代知识不同来源的影响,方可对其变异、游移、缺憾以及建设性的实践付诸探赜索隐的阐释。
一、不确定性:澄明心性的方式
在渊源上,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与西方思想史中的怀疑主义传统多有关联,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盛行极端怀疑主义,学园怀疑论者提出了大量的论证,以表明什么东西也不能被认识;他们并且劝告人们要依靠或然性去生活。公元前一世纪形成了皮浪(Pyrrhon)怀疑主义运动,从感官怀疑主义发展到逻辑怀疑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2]皮浪怀疑派嗣后幸存下来的唯一著作《怀疑主义基本原理》把怀疑主义描述为能力或精神状态,把作为感觉经验的对象之现象与对于这些现象的判断相对立,以使人们能悬置判断,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任何东西。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平静”的状态。怀疑主义在近代的几个世纪持续笼罩着欧陆哲学,理性主义哲学出现了笛卡儿的怀疑一切。经验主义哲学出现了贝克莱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康德由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后指出,世人不可能认知现实存在的真正本质,因为人的知识经验受到人之精神所具有的时空、因果等先验原则制约。先验的知识结构虽能揭示认知主体,却对其反映的认知客体有着不确切感,而对其认知对象之外的“自在之物”则绝对无知。从康德的不确定性——不可知论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其共同倾向是借由探究认识本身,反省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这或许就是解构主义前世的种子。需要指出,与现代性哲学——为理性的进步服务,追求确定性,去思考未思(The Unthought)的东西——不同,后现代性思想家(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开始)尽管也试图继续思考那些未思之物,然而他们已经放弃了完全把握未思之物的透明性或自明性。
在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初期的后现代研究中,曾根据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离危机,归结出一个联想性的特征序列,这个序列容纳了后现代主义中众多领域的特征,它包括索绪尔和雅可布森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德律兹、罗兰.巴特和克丽斯蒂娃的文学理论以及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音乐家和视觉艺术家的艺术见解。[1]扬弃哈桑这个序列潜在的二元对立等级价值模式不论,他所厘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几乎就是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这个概念的繁衍。
哈桑所定义并反复解释的不确定性无疑有概念的增生作用。他认为,所谓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是指由种种不同的概念帮助描述出的一种复杂的现象,这些概念包括:“含混(Ambiguity)、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异端(Heterodoxy)、多元性(Pluralism),随意性(Randomness)、叛逆(Revolt)、变态(Perversion)、变形(Deformation)。“变形”还可以进—步用目前流行的十余种表达解体的术语来说明:反创造(Decreation)、分裂(Disintegration)、解构(Deconstruction)、离心(Decenterment)、移置(Displacement)、差异(Difference)、分离(Disjunction)、消失(Disappearance)、分解(Decomposition)、解定义(De-Definition)、解密(Demystification)、解总体化(Detotalization)、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另外,还有许多技术术语也能说明反讽、断裂和沉默的含义。上述概念符号凝聚着一种要解体(unmaking)的强大意志,影响着政体、认知、爱欲和个人心理,影响着西方叙述的全部领域。[3]由是看来,不确定性是多重的、复杂的所指。因此后现代艺术创作与批评理论都瞄准了这种不确定性的阐释学,可以说后现代阐释学是古代怀疑论的继承者。
真正的艺术永远要向其自身的本质挑战,因而增强了艺术家思维中的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二战”之后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价值准则长期陷入混乱,它们更加焦虑的是社会已不再适于明确的定义,曾经为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类型和标志如今已变为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事物,作家和艺术家感应社会生活的变异和情感症候,其艺术作为一种敏感的触角迅速反映着这一切。一方面思想抛弃了其本质主义的基础,文化和历史就像现实本身一样,受到同一种不确定性的支配;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对于物质世界的新发现,诸如测不准原理、量子论的波粒二相说等,也使他们的观念受到暗示并作用于经验世界。罗布—格利耶说:
在我们周围,世界的意义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是有异议的。无论它是什么意义,艺术作品怎么可能阐明预先就明了的意义呢?……现实是不是有一种意义?当代艺术家是不能回答这一问题的:他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不再相信由陈旧的神圣秩序、随后又有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秩序带给人的任何凝固的、现成的意义,但是,我们会把我们整个的希望转给人:只有人所创造的形式,才能带给世界以意义。[4]
在“新小说”派的观念中,认为“在作品成立之前,什么也没有,没有肯定,没有主题,没有信息”,只有一些“暧昧不定的构思”,因此,小说家们在现实中所能做的是探究那种混乱的多重复合意义,罗布—格利耶强调小说的虚构功能,利用其创新技巧形成纯粹组合的方式,他的《在迷宫中》描述一名士兵在一个小镇上的游荡,始于许多虚拟的离题的内容,是若干叙述主题的变化和重复形式的混合,而这些变化构成了小说自身。
“新小说”的写作趋鹜于“非人化”的“零度语言”,以此克制共同经验的表面现象。在一些文本中主人公无名无姓亦无性别,有的干脆以字母、符号代替,这些人物既无过去也没有未来;时间和地点也是暧昧不明甚至随心理的时空先后倒置。布托尔的长篇小说《变》(1957),通篇将主人公称作“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你把左脚踩在门坎的铜凹槽上……”[5]这里的“你”即非第三人称的“他”,亦不是第一人称的“我”;既非旁观者的叙述,也不是自叙;它既像似一种敦请(使阅读者参与本文之中);又近似一种指令(将主人公安置于特定的语境)。这些不确定性使阅读产生了多义性。这种文学文本所表现的世界仅以其自身的文本结构为依据;主观性让位于文本性。
不确定性在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单调乏味的苦役,克服形而上学乡愁而致力于把握那些带有神秘编码的偶然事态,这本身同时暗示着不可描述性,使感觉能尖锐地去感觉不可能的事物,它因此而显现为观念艺术—过程艺术的审美准则。约瑟夫•波伊斯的“社会雕塑”,将不可塑的材质,如油脂(动物的)、蜂蜜、声音、光影、动作、语言乃至动物和人都僭用到创作中,其著名的《油脂椅子》在视觉形象上简单得令人困惑,它只是一块切成楔形的黄油,置放在椅座上,抹成一个45度的角。正是这样一件有巫术意味的“摆设”,体现出不确定性精神。波伊斯自释道:“我使用油脂的原意是要激发讨论。这种材料的可塑以及其对温度变化的反应特别令我喜爱。这种可塑性具有心理上的影响力——人们本能地感觉它与内心的过程以及感情有关系。”[6]波伊斯的“社会雕塑”假借不确定性为艺术观念注入一种兴奋剂,他追问并来反证雕塑能够是什么,转而在空间意义上延展差异性,指向永远在发生的“现在进行时”,他的所有雕塑性质都是流变的、未完成的——“过程在它们的大部分之中继续着:化学发酵、变色、腐烂、干枯。每种东西都处于变化的状态中”[7]。
不确定性使风格形式要素退居次要位置,重要的是要反映并诊断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的各种变化细节;因而艺术的自主性就不只是精神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将对世界的探讨转变成探索时代图像的艺术品,而更加注重寻求实时性(日常生活内容)和即物性(利用新的媒介)。德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诗歌“新主体性”诗歌,就是这种形态的作品,其代表诗人布尔克曼(R. Bulincoman)《向西一、二》中写道:
讲故事的人在继续讲,汽车在继续生产,工人在继续干活,政府在继续执政,摇滚歌星在继续唱,价格在继续,纸在继续,动物和树木继续生存……穿过一幢住宅,风吹起旧报纸,飘过空荡无人的灰色停车场,荒草与灌木丛在废弃的地基上生长;在内城的中心,一道工地的篱笆刷成蓝色,蓝色的篱笆上钉一块牌,招贴画上画着禁令;招贴画,工地篱笆和禁令在继续,房子墙壁在继续,城内在继续,城郊在继续。[8]
布尔克曼的本文隐含着解构的策动力,由于主体的离散、游移,漫漶而使奢侈的能指聚合于平行的、互相排挤、互相重迭甚至互相冲突的语境里。
后现代主义诗歌回到一种低调的、非自我中心的叙事,一种善于利用语言和经验中松散的事物、偶然的事物、无形的事物以及片段记忆的事物之叙事。美国“语言诗”派(Language Poems)[9]诗人接受随意的非诗歌的言语形式,如信件、谈话、轶事和新闻报导,使用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等,以便在不同历史时间框架中插入未完成的、临时的和被历史进程渗透的状态,重新肯定文化中的历史物质性,而现代性文化从来都忽视或消除这种物质性。当不确定性变成自觉的艺术方法,带来的结果则是艺术形式的更大扩展和内容的变化,“现代主义更趋向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神秘性,而后现代主义尽管表面上具有神秘性,实际上却无可挽回地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10]
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不确定性所包涵的随机性、偶发性与东方禅宗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禅宗境界的标志之一便是万物同一,梵我同一,心物同一,一切皆空。禅的目标是把握生命的中心事实,否定“无明”(逻辑二元主义),在言筌不逮之处,在意识尚未觉醒的地方,捕捉人生具体而自由的各方面的价值。禅是为了洞见神秘的人生和玄奥的自然,并能悟得全新的观念,才摈弃逻辑推理的方法。因为逻辑学的方法论在深层的精神要求面前一无所能。禅的真理原本是“无”、“空”、“寂静”、“不可思议”,所谓“圣道通幽,言筌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设施也。”[11]倘若仅仅执着于功利目的,即或执着于佛法,执着于“戒、定、慧”,则皆属没有悟性,其结果势必与无情的顽石、朽木无异。为此禅宗六祖慧能教导众信徒:“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12] 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其名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13] 此偈直指人心,认为人的本心既一切,天生清净,无所谓美/丑、净/垢,只要见到本心,便可顿悟成佛。此偈是出于慧能对学通内外、为众僧推崇的神秀之偈的应答。神秀在前的偈子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14]他试图指证,心灵的明镜蒙上了“尘埃”,通过不间断的“拂拭”即可使之明净。比较起来,五祖弘忍认为慧能彻悟了禅的神髓,足可继承其衣钵。但由于慧能之偈传达了“虚无”之境,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便认为禅宗是一种虚无主义。对此,日本禅师铃木大拙出面澄明道:
禅的虚无不是全然否定。禅有其独特的肯定。这种肯定是具体的、自由的、绝对的、无限的。……禅的否定不是逻辑意义的否定,禅的肯定也不是逻辑意义的肯定,因为‘本体’不能被人为的思维规范,也不能被‘是’与‘否’的判断形式以及所谓认识论的诸般公式束缚。[15]
我们还可以据此进一步分析。禅的“虚无”,是相对于现实唯物论而言。在现实唯物论那里,存在着一种唯一的、独立于一切感知的实在性,经验论以及现实主义认为现象的存在就是实在性,禅宗和整个佛教都否定现象背后存在不变的实体。禅宗在诸多公案里谈到“空”时,总是某种现象的显现,一种诗化的哲学表征,它丝毫不反映固定实体的存在。后现代物理学的波粒二相说告诉我们,一个电子既能被看成一个微粒,又能被看承一种波(Oned),这两个概念在常识中或许就是荒谬。但如果根据佛理,原子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固体,或者一种唯一的确定性的存在。缘此起见,由无数微粒凝结而成的粗浅表像世界,何以能够获致其固定的实在性?这种“虚无”的真理,消除了我们对于表像的固执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佛教禅宗肯定现象的最终本质是“虚无”,“虚无”本身即有无限生机,诚所谓“石女生儿”、“露柱怀胎”、“枯木里龙沉吟”、“骷髅里眼睛”是也。
禅的精神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在美学意义上处于交互融渗关系,约翰•凯奇汲取了禅宗思想精髓和《易经》的义理,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偶发音乐”放弃了西洋音乐的传统形式和数理的作曲法则,1954年在黑山学院的音乐节上以钢琴“发表”其长达34分46.766秒的音乐作品——只有“演奏形式”而无音律,因而“4’33’’”这一曲名仅指作品的演奏时间。在时空的并存性质中,“无声”只是相对状态,“不确定性”显现于此状态之中:室外的骤雨,室内屏息的听众(作为高音的神经系统和低音的血液系统、心电图的韵律),以及“像祈祷一般的”沉思默想,实质上表达了禅的明心见性;“哑人解唱木人歌”,“无弦琴韵流沙界”,回到相对意识尚未生起之时,聆听“无弦琴”、“无孔笛”般无音天籁。
概括而言,对不确定性的追求是后现代艺术美学的根本特征:在内容上,与现代性对总体、中心、秩序、同一性、理性的追求相反,它怀疑确定的秩序、拒绝宏大叙事、否定审美的统一标准,为美的多元性、差异性、复杂性留下了解释空间;在形式上,后现代艺术美学摈弃了现代性的形式美概念,非艺术地表达艺术,从外在性抵达美学,各种艺术门类的界限、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被超越,进入广泛的文化表征领域。美和艺术的本体特征是自由,与社会总体中根本的非自由是永久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总是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真实原因。
由于不确定性方法通过对语言滞累和逻辑的遮蔽采取“随缘任运”的破执、祛蔽,因此而衍生了一个无法还原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随意又多样的,它(为城市和世界)规定了那种悬而未决的态度,这……隐含着世界及宇宙间事物之意义和关系一种根本易变性的宽容。”[16]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不确定性突破了经典的二元对立的壁垒并洞悉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诸如宗教/科学,神话/科技,心性/理性,通俗文化/高雅文化,女性原型/男性原型乃至东方/西方、自我/他者等等,转而寻求多元的联系或者折衷,使二元因素彼此限定和沟通。
二、解构: 空间书写之建构
从上述所探讨的不确定性因素中,我们辨析到不确定性是作为解构策略来拆除、分离逻各斯中心论的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创作方法。可以说,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是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形态,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解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场量形态;它既是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一种方法论,又是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一种美学意识和上手状态,而且还将是一种建构方法。
解构主义的始作俑者德里达反对逻各斯语言中心论思想,认为必须以书写语言学(Grammatology)来替代,并且他也反对西方长期认为音符超过字符的传统,认为书写语言是独立于声音语言系统的另一种符号学。德里达反对索绪尔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17]分开而使二者成为两个相对立的封闭系统的方法。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是依靠语言分解的过程,追溯语句的本文的“踪迹”(Traces),“踪迹”之间彼此不断发生交感,并可以任意串连,使得语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同相异的“踪迹”可能出现于另一不同的“踪迹”之内,“踪迹”之间相互依存,因此永无绝对统一涵义的可能,意义是一连串无止无尽的连锁反应中的“差异”和“延异”所出现的状况。德里达自创“延异”(Différance)一词和“差异”((Difference)的发音完全相同,而所代表的意思完全有别,德里达如此定义其“延异”概念:
‘延异,是结构概念,因为没有‘différance’,就没有结构,它是结构的最一般的结构,但这必须假定人们不把结构理解成古典型形而上学的结构,或者古典结构的形而上学。……这些差异——例如,它们可以产生出分类科学—一是的延异结果;它们既不刻在天上,也不在头脑中,这也不意味着它们是由某些说话主体的活动产生的。从这一点来看,延异概念既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结构主义的,也不能看成是发生论的,相反,这样一种二者择一本身就是延异的结果。[18]
“延异”将“差异”的空间实现和发生融入此时此地,这种意义指向时间化了的效果,使得读者—观众在阐释文本的过程中,由于参与“踪迹”反应程度的不同,而使得意义成为永不能确定的主观性。所谓“解构”的动作,就是书写语言中符号不断地被追踪,因“延异”的使用产生原义不断地被拆解,符号反应程度的不同,而使得意义成为永不能确定的主观性,所谓“解构”的运作,就是书写语言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不断地产生新义仍不断地拆解,所以“在场”反应时间某种程度的逗留,时间发生后旋即成为过程,全然“在场”自无可能,因而没有任何方法窥得语意的全貌,更无从由语意的表达形式印证“真实”或反应“真实”,语意处于无尽的不确定性中。
德里达在其《文字学》中通过对索绪尔、卢梭等人的理论分析,找出表面严谨、清晰的原作中的疏漏和裂隙甚至等级秩序的暴力倾向,然后扩张其显露的裂口,使原作的确定性显出种种飘忽不定的差异,使原来似乎严整的结构消失在符号游戏中。[19]这种消除结构(Deconstruction)的写作即解构的批评方法。解构批评往往指向作品文本的自我消解性质,论证语言符号的修辞性和隐喻性所支配的任意虚构性。
但要解释后现代艺术创造中的解构方法,还必须从结构谈起。在现代艺术史上,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m)系于现代主义在20世纪初的运动。结构主义曾出现于布莱克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实验中。1912年毕加索在将其绘画中的几何造型与拼贴转变为三维空间形式时,创作了首件金属片与铁丝做成的吉他。一年后苏俄雕塑家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在毕加索的巴黎工作室中看到了这些作品,返国后便开始创作雕塑史上几乎是首创的完全抽象的雕塑。他也表达了最具影响力的结构主义原则“材料的真理”,主张特定真实的本质促使圆柱型成为最适合金属的造型,而平面只适合木材。
结构主义对“二战”后的艺术影响极为显著。结合不同材料(多半靠焊接)是20世纪40—60年代初主要的雕塑方式。在技术之外,它影响了思考艺术与科学技术关系的方法。这种源于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的理性手法不仅涉及国际风格的建筑设计、构成艺术、抽象雕塑、动感艺术、极限主义以及艺术与科技结合的计划,甚至融入了硬边绘画与几何抽象乃至所谓的工业美学。从现代艺术史料中可明显看到,结构主义艺术家设想有一个形而上结构决定符号的义理,成为意义的本原或中心,并力求在作品中再现这个结构。而后结构主义者和具有解构意识的艺术家极力否认任何内在结构或中心,主张作品本文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不存在终极意义。罗兰.巴特用剥洋葱头作比喻,否定作品封闭性的不变内核,指出艺术作品:
是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边到头来并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惟有无限层的包膜。其中包含的仅仅是其自身表层的统一。[20]
如果说,解构主义在上述架上艺术仅彰显在个别性的创作方法中而不具鲜明的学理性,那么,在解构主义建筑设计和建筑作品中,则从意识、学理、风格和美学方法论层次达到石破天惊般的变现,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确立了解体、离散和转换的先兆。这是由于建筑发生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三重复合结构,其自身在形态上亦不能自外于物质材料构成的空间结构。解构(Deconstruction)则必然与结构(Construction)联系在一起,然而解构并非对系统性结构的简单拆解、摧毁或否定(现代性的革命往往如此),它所探讨的对象是关于本源、形而上学与构成本源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关注结构的封闭性和整个哲学内在性的结构问题。解构与分解的严格区分,就在于分解所减缩的基本要素在解构那里成为必要的题材。
这样,解构不仅广泛涉及到一切建构活动,而且必然涉及到系统的建筑学主题(Motif Architectonique)。德里达认为:建筑最隐蔽的意图是控制社会的沟通、交流。广义而言,其最终目的是控制经济。他因此建议,后现代主义建筑必须清醒地反对现代主义的垄断与操控,反对现代主义的空间霸权,反对把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孤立起来的二元对立方式。
解构主义建筑师多半都具有跨学科的学者型知识储备,兼具自由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开解构主义建筑先河的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即以具有广博知识的理论家、批评家而著称。自20世纪60年代起,艾森曼将乔姆斯基(Noam A. Chomsky)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作为自己思考建筑的语言模式来加以运用,对封闭在空间内的时间进行挖掘。80年代以后,转向德里达的“文字学”理论所展示的解构规迹,以延异取代逻各斯,沉浸于“雅克造的房子”中。此后,进一步结合自然科学理论,如拓扑几何学。法国生物学家鲁奈•托姆根据青蛙之卵的胚胎变化而提出的突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以及罗兰•巴特的“互文性”、重复书写之羊皮纸文献(Palimpseit)的转义等不同学科领域,大量地移置、参照性地引用到建筑作品中。
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纳尔视觉艺术中心(1983—1989),是艾森曼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解构主义作品,显现着参差的非统一性、迂回、无序乃至随心所欲的解构特性。在布俗大厦(1992)的设计中,“海底扩变学说”(Place Tectonics)的隐喻意象加以应用,表现出地球变动所产生的裂痕,山地震引发的建筑物坍塌前的“瞬间凝固”与“替合”状态被“记录”下来。因而从依附性的读解、支配性阐释制约中,将“内在时间”转换成“外在性”读解和非确定性的阐释。菲利浦•约翰逊(Philip Johnson)曾说:“艾森曼是一个谜:”这种评价是缘于“解构之谜”的性质——任何关于“是”或“有”的本体论判定都无法抵达先验的目的,无法确定又无法解析,既非整体性的事物,又非单义的或统一的“在空间与时间的表述上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联系”(艾森曼,1991)。
解构主义建筑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逐渐生成一支精锐的建筑家系谱,包括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弗兰克•盖瑞(Frank Gehry)、丹尼尔•雷伯斯金(Daniel Iibeskind)、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库柏•辛门布劳(Coop Himmelblau)、渐近线设计组(Asymptote)和埃瑞克•欧文•莫斯(Eric O.Moss)等,其支谱在日本建筑界随之形成。
在此系谱中,弗兰克•盖瑞(Frank.O.Gehry,1929—)是一位已经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建筑家。盖瑞惯用的解构方法是,将一个工程尽可能多地拆解后分离成多元之迭合,这与其说一座建筑物是一个整体,不如说是由几部分具有雕塑外观的体积构成。盖瑞的建筑可以视为一种新颖而令人惊奇的“抽象雕塑建筑”,它由非平衡、不稳定、不规则诸多体积拼接、组合,呈现着大幅度的分离、聚合,又具有飞扬、跃动的形态各异的空间张力。概括而言,盖瑞的创作资源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绘画与雕塑使之获得审美的普适性,类似英国女建筑家扎哈。哈迪德,她倾心于从俄国构成主义、至上主义的抽象逻辑人手,分解出其未见的可见性,替补在场的缺席。替补的作用是在解构意识驱动下,行使着既是补充又是替代的双重意指功能。其次,是仿生学的造型,主要是鱼、蛇及飞鸟的动感形态之抽象化表现及其鳞片、翎羽的魅人璀璨。最后,是异样的装饰材料,在西班牙的临河小郡毕尔巴鄂建造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外部饰面采用了钛合金——从俄罗斯购置的一批廉价工业材料。从加里弗尼亚宇航博物馆、弗里德里克.R.韦斯曼美术馆、巴黎的美国中心、迪斯尼音乐厅到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盖瑞的“解构”才华如同暗夜的星辉,使20世纪的公共建筑焕发出建筑作为艺术之母的后现代光芒。
在后工业社会,建筑艺术的命运被经济控制是一项令人遗憾的事实。建筑的非艺术存在、非“诗意的栖居”使之日愈朝向齐一化、技术化和科层化的境况滑落。所谓金钱与权力交织的诡谲的“盘丝洞”,是当代建筑业的基本隐喻。敢于涉足此一领域并将“解构”进行到底的女建筑家,无疑将获得人们的敬意。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1950—)的奋斗足迹,是当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她的胜出首先是以“解构”的锋利锐角,击败了“香港之峰俱乐部” (The peak competition Hong Kong l982—1983)600多名国际投示方案的竞标者。哈迪德的设计语汇以爆炸般的建筑碎片、锐利的弧线、飞扬的动感,震撼人心的力度以及危险的替代,跃人世界建筑的明星舞台。“建筑可以是无重力的,是可以飘浮的。”哈迪德再度不可救药地使建筑的“本源不在场”,毅然给出了历史上女性设计的最重要的建筑——著名的英国卡迪夫•贝歌剧院(Cadiff Bay Opera House,1994)这一设计使她成为与长谷川逸子相互对举的国际女建筑家。
有关解构主义建筑的深层讨论,最终无法绕过丹尼尔•雷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1946—)稀世的设计杰作——1989年设计的柏林博物馆(又称犹太人博物馆).这不仅因为雷伯斯金响应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命题,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或无从建构可能更为野蛮。问题是必须追问诗性的真理如何可能;人类信靠什么方可“诗意地栖居”;或者,在无从建构之处何以上手解构,解构又如何生成建构。
柏林博物馆是关于历史踪迹的诗学,是藉由对苦难的深度体验而产生的死亡抽象,因而它显现出迷宫属性的延异结构,里伯斯金称之为“复线的狭路相逢空间”。建筑中历史踪迹与死亡抽象交错为关联网络,相互限定、沟通,在形式的曲折迂回中无限延伸,又相互游离、分散,形成贯穿整体的非连续性空间。这种关联,这张交错的网,就是文本,它全部生成于另一个文本的转化。无论是诸要素还是系统本身中,都根本不存在单纯的在场和不在场,都是踪迹的痕迹。柏林的踪迹是一个无穷延异的结构,历史与死亡在此保留着可资指涉的差异:犹太人的悲剧命运踪迹,犹太艺术家的生活踪迹。这些踪迹并不在场,而只是在设计中不断分化自身、延搁自身并指涉自身的印象。踪迹的本源就是踪无所迹的可能性在场,在分延运动过程中显现自身。
里伯斯金藉由柏林踪迹“延异”着四重结构:1、犹太智慧对日耳曼文化的介入和影响,在此形成的踪迹是对他者的非自然的替代,但同时产生出一种二律背反。2、大屠杀年代纳粹惨绝人寰地迫害犹太人运动,令上帝“不在场”的血腥历史,以死亡集中营的死者姓名和死亡地名的铭文形式留下符号的踪迹,这揭示出本源的不在场,而死亡成为缺席的替补。3、根据奥地利犹太作曲家勋伯格(Arnold Schonberg,1874—1951)未完成的歌剧《摩西与阿隆》脚本而构成。由于歌曲的存在而歌词不在,踪迹先于存在者而存在;相反,当歌词试图替补踪迹(歌曲)“如此说出自身”时,踪迹自身随之消匿于自身的隐蔽状态中,而继续在能指的路径中延异下去。4、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犹太思想家本雅明的著作《单向街》(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文本生成另一建筑文本,在迂回曲折的连续性空间引入60个连续断面,显现对应于《单向街》本文——由60篇随想录、箴言等组成,其中收编了1923年撰写的《德国通货膨胀的巡视》。它是本雅明生前发表的惟一具有审慎性的自传性著作,“对自己的回忆成为对一个地方(一条街)的回忆”,“他围绕这个地方游移,在其中不断变幻着位置。目标是成为一个能够非凡地使用街道地图的人,知道怎样迷失,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想象的地图确定自己的位置。”[21]
本雅明在《柏林纪事》中的隽永的格言“需要多次练习,才以学会迷失”,在此转换为雷伯斯金的隐喻性设计语义,它是关于隐喻的隐喻,使在场成为符号的符号和踪迹的踪迹。本雅明曾画过一张个人生活图表,看上去像一座迷宫,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系都是一个通往迷津的人口。这些反复山现的隐喻,如地图和图表,记忆和梦想,迷宫和拱廊,狭景和全景,都唤起一种独特的城市幻象,唤起一种独特的生活。德国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曾这样评析本雅明的“迷失”(迷恋于细碎事物)——本雅明所具有的恰恰是卢卡奇(Georg Lukacs)根本缺乏的,他对这样一些事物有独特的眼光:有意义的细节,身边琐事,思想和业界中的新奇因素,非常规的个别事物。本雅明对这类细节,这类意义的碎片符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幽微语言感觉。[22]
雷伯斯金将犹太人博物馆称之为“Between the Lines”,包含着启示录式的双关语,作为建筑物的博物馆的功能性已被解构,它所收藏的是踪迹的存在(Being)/非存在(Nobeing),是犹太人(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现代性文化身份的痛苦碎片;同时犹太教所寄寓的弥赛亚拯救精神,在此显现着藉由民族记忆踪迹的另一种收藏,思想碎片的引文式收藏,实现对人的拯救之替补,而本雅明的生前即被理解为一种近似革命态度的“非专业价值”的收藏家 [汉纳•阿伦特(Hannad Arendt)语]。凭借历史与死亡的踪迹,隐蔽的附属物和被遗弃的梦想,来建构历史的意象,而这也正是雷伯斯金解构式建筑所蕴涵的隐晦的思想魅力。
诚然,解构主义的踪迹诗学并非神学意义的表征,但是“本源不在场”在这里被逆转为“上帝的踪迹”却是构成精神复原的决定性时刻:无音乐的旋律,无本文的箴言,无展品的博物馆、非存在之存在,都如同一个以《圣经》为国度而满世界流亡的民族,这是一种有上帝而无宗教的弥赛亚状态,“是因为它永远在全部逝去。竭力迫寻这种逝去,即使在人的那些原始状态,也应该是世界政治的义务”。[23]这一“上帝的踪迹”在其延异过程中敞开了显现与意指的曲折迂回路径,把飘流破碎的有生(Levivant)和无生(Noe—Levivant)联结起来,形成结构的替补,在此意义上替补即延异的别名,延异比存有更古老,解构即拯救的策略。
三、寓言性的再生
寓言是一种长久“被遗忘和误解的艺术形式”(本雅明,1928),它主要是被本雅明弥赛亚式的修辞学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启动,逐渐广泛地凸显于后现代时期的艺术批评理论和艺术创作方法中。
寓言与象征(Symbol)的不同在于:象征有别于寓言用故事来喻示某个道理或观念,它以形喻义,形义一体,达至经验的圆满性,甚至超验的神秘性。象征主义以“交感”营造“象征的森林”;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画派则执迷于梦幻的象征意义,以梦幻的形式自发地创造象征。
本雅明认为:寓言和象征是两个内涵不同的艺术规范概念。象征构筑着自足、完满、总体化的理想世界本文;寓言却构筑衰竭、分离、破碎的死亡世界的文本,“寓言在思想的国度如同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是对世界之“苦难历史世俗的理解”,因而也是“世界衰微时期”艺术的标志,在这种寓言艺术中,“历史并非永恒者的逐步圆满,而是一个必然衰竭的过程”。而正是在死亡意象横亘的世界历史中,救赎的革命性才得以再生。在此,本雅明同时种下了解放神学的“一粒芥子”。
本雅明对寓言的厘定经由语言论美学的转向,在杰姆逊的话语中“延异”为一种“寓言美学”(Allegorical Aesthetics)的意向:
所谓寓言性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希腊文的Allos(Allegory)就意味着“另外”,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的故事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24]
杰姆逊将阐释理解为基本的寓言行为,依据于一个特定的阐释性主符码,去重写(Rewriting)被给定的本文,从“语言的牢狱”中释放出一种“超历史”,一种超越能指迷宫的历史所指。其“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ze)的宣谕,实则寄寓了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意欲充当历史寓言破译家的雄心。
历史在“重写”的阐释或“解符码化”(De-Coding)中显身,寓言就必然与“历史性”结缘并将所指的问题付诸于实际行动,不仅因为寓言假借时间的过去(历史事件)揭示时间的现在(历史的叙事),更因为寓言性能指在后现代时期是以物质异化形象回归的,它就必然依重于思想家和艺术家破译现实界(The Real)的敏锐观察和创造性。
寓言就是讽喻,它正话反说地讲述寓言之真理,说它就发生在现在,而且是通过人与面具之戏剧作用陈述这一真理。[25]寓言被现代主义的非历史、反传统话语放逐的缘由,首先在于现代主义排斥历史化的叙事,主张本文封闭的内在性;其次是将“纯粹语言”作为“本体语言”的执妄,遮蔽了对历史衰竭的真实体验。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寓言的指涉很少出现在艺术上。
建筑批评家查尔斯.詹克斯(Chcrles Jencks)在谈到后现代主义的寓言风格时指出:
在人们所熟悉的寓言形式如《天路历程》中,明显的故事与其潜在的意义是清晰而易理解的;而后现代主义寓言既不让我们确定主要故事是什么,也不让我们确定它所暗指的隐含神话可能是什么。[26]
回归历史性图像、叙述性与物像,相对于象征和抽象,后现代艺术使寓言向历史的现实性逆转,走向观念的精神仪式。
20世纪晚期主要的寓言性艺术家是意大利人与德国人。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古奇(Enzo Cucchi)、依门朵夫(Jorg Immendorff)、基弗尔(Ansehn Kiefer)与米登多夫(Helmut Middendorf)。德国艺术家基弗尔的作品引用着《圣经》福音和历史地点及条顿民族的神话(Teutonic myth),演绎歌德的《浮土德》以及其它文化象征为当代德国生活的寓言。基弗尔的寓言性作品媒材大幅度地混合着沙砾、水泥、稻草、植物、铅、锌、书籍、工业油漆乃至废毁的飞机,造势于恐怖、压抑、破碎、荒寂与衰败的物像形式寓意,这种前所未有的惊人寓言结构本身是对非精神历史具体的现象式表现。美国画家柯尔斯科特(Robert Colescott)称他的作品是“在黑幕中的艺术史杰作”,是“比较可以让人理解的种族主义寓言。”
波伊斯至死都在充当着寓言仪式大师。波伊斯的艺术从言语、思想开始,在说话里学得,形成观念,反过来又将言词、思想当作雕塑,在物性中彰显。“扩展艺术观念”及其“社会雕塑”是其寓言方式,救赎是其寓言的主题,贯串于他怪异的历史/文化/政治的图像志和修辞学;以国际主义取代种族主义,以创造取代毁灭,以人类的生存感取代民族感,以绿色取代棕色,以暖取代冷。这些指向作用于语言学转喻而富有社会功能。波伊斯的作品反复使用油脂、毛毡、十字架、雪撬救护车,使用冷/暖相互对立/转化的媒材,使用伤残躯体的模拟物:死动物标本、骨头、绷带、烧焦的香肠、剪下的指甲、牙模,这些表像隐晦的存在物即构成隐喻的基本材料,而隐喻又是寓言得以成型的材料,是构成其“社会雕塑”的前提。在时间的纵聚合轴上带有隐喻性质的物象,被移置到特定的语境中,或移置到空间化的现象式环境中,因而改变其含义和性质,这就是转喻。转喻对波伊斯的救赎寓言来说,显现着个体与历史精神伤痕的一种顺势疗法。
在地景艺术(Earth Art)中,与环境直接相关的隐喻性转换而产生的寓言效果,成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寓意对象。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在大盐湖假借当地的神秘传说(湖底的漩涡)而制作了《螺旋形防波堤》,是以地点特殊性而产生的杰作。特定场所的作品,根据其中可转喻的因素,来设计它的总体,使它的结构和内容在环境中展现逻辑性的延伸。克里斯托早期作品《铁幕》(1960),用几十个油桶堆积在街口造成交通堵塞,则更为直接地制作一个政治寓言。克里斯托与珍妮•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de Guillbon)以风景为表现形式的方案中,最令人激动的是在澳大利亚创作的《包裹海滨》(1970),花费了100多万平方米的聚乙烯布和35英里长的绳子覆盖一英里的海滨,以及在美国科罗拉多的赖弗尔豁口,用1200英尺长的巨大缆绳在两山峡谷之间挂起一道重达4吨的黄色幕布《峡谷幕布》(1970)。这种看起来十分奢侈的创作,本身是一种社会经济寓言,一方面这些环境艺术家要负担另外一些有商业价值的创作方案,用来抵偿巨大的材料开销,但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了商业经济手段来反抗商品化的经济中轴原则。“贫困艺术”(Art Povera)常常利用环境、物像,构成寓言性作品,如赫尔曼•达门(Herman Damen)的《母牛诗》(Cow Poem,1969)将诗文烙印在母牛身上,母牛既是自然景观,又是人文(传媒)景观,语境被拓扩,随着媒介(母牛)的场景移动、变化,本文的寓言性也不断地改写。地景艺术家们在其构造的“寓言”中,充当了自然托管人的角色,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绿色政治)方面有力的根据和支持。
现代艺术史中运用叙事本文营造寓言者并不难寻绎,但假借视觉叙事构成“认识方式的认识”却十分罕见,而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则是个例外,他的代表作之一《 这不是一只烟斗》力图沟通文字与图像两种语言,并将语言和形象的传统关系打乱,词语的闪光划开画面,使之碎片横飞。图像和文字得以正反对接,形成相互转化的怪圈。他抑制叙事的理性逻辑,抵消了超现实主义的梦幻因素,接着诱发解释并质询解释者,进而寓意对事物的想象或记忆不能与事物的实体或存在的真实性相混淆,所有事物的真实性都不等同于它外在开显的那样。如此一来,所谓绘画的真实性也并不是它所表现的那一事物。于是,“这一只烟斗”就成为一个向规则和常识挑战类似于“白马非马”的吊诡(Paradoxical)命题。在那里事物失去命名/被命名的双重权属,同时失去名与实、所指与能指的指谓关系。对此,福柯认为,马格利特是在用绘画的方式进行哲学认识论的探索。[27]
综上可鉴,后现代的寓言性方法拒斥单纯机械地使用历史题材、宗教神话,艺术家们并非僵硬地挪用生活或历史场景的片断,而是以卓越的想象力对一切虚假意识和真理面具明快而隽永地揭示。
四、后女性主义艺术:身体返魅
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在1960年代晚期于法国兴起,其理论承袭了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解构,在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思想分析策略影响下形成。1968年“政治与精神分析”组织在巴黎成立,打出“女性主义下台的标语”标志着女性主义向后女性主义转折的关键时刻。
后女性主义是后现代性的一种表征,它对立于现代性的线性有目的时间模式,对立于解放论的政治运动和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积极邀请女性去探索(包括女性身体的)主体建构的复杂性:一种趋向是以解构主义式的“主体”概念,超越本质主义决定论的性别主体;另一种在其内部生成的趋向是彻底非二元论的生态女性主义,承认性别身份的社会构成因素,更强调生态学的细微改变。然而两种趋向形成的文本特征皆可称之为身体的返魅(Enchant to body)。
尼采和韦伯都曾深刻论证过,近代以来的世界之合理化、世俗化、官僚化和现代化是一个祛魅化(Disenchantment)过程,返魅是对总体现代性的祛魅而言:一方面是藉由女性身体的历时态审视,指证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荒谬史实;一方面共时性地在对历史衰败的真实体验中,在意指系统之外或“历史的剩余物”开显破碎的主体,建构开放性的本文空间。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感知宇宙创造的经验中,寻求以自然为基础内在于大地和女性身体的女神原型。
后女性主义的这些不同理论主张、思想观念在当代女性艺术创作中都有相应的表达,使得差异和实践有了立足之地。
后女性主义最有名的游击女孩(The Guerrilla Girls),是一个共相而匿名的美国女性艺术群体,她们头戴大猩猩面具,以隐匿式的“纪检组织”形式(反讽的反签名、“作者之死”),穿插、迂回、袭扰着艺术界、艺术体制及其人文结构,其主要方法和目的都在于解构/建构女性的身体本真。
重写艺术史之行动,也就是使历史朝向“Her-Story”的现实性转换。游击女孩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到20世纪达3000年的艺术史话语中,寻觅被“活埋”、 “阉割”的女性艺术家,诸如:丁多列托(Jaeop Tintoretto)的女儿玛丽娅.鲁芭斯蒂[Maria Rubusti(1560—1590)]在父亲的画室展现出异常的才力,而在难产过世后,则使其父亲的创作一筹莫展,失去致命的“秘密武器”;阿特米莎•简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不断在作品中重复“朱蒂斯砍下霍拉法尔尼兹的头”这一历史主题,来诊治被父亲的同僚强暴的痛苦经验;罗莎•邦荷尔(Rosa Bonheur)要隐藏自己的姓名才能外出作画;卡蜜尔•克洛岱尔(Camille Claudel)因大胆表现女性情欲,以致身败名裂,却让其情人罗丹心照不宣地坐收渔利,让男性中心主义艺术史家昧心地去虚构“性、谎言和雕塑”;墨西哥壁画运动英雄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妻子芙丽达•卡洛(Frida Kahlo)那些痛苦表现自传性内心挣扎的魔咒式作品,要在其过世后才被认可;身为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妻子——雷•克拉丝纳(Lee Krasner)直到变成寡妇后才真正能显山露水。
西方艺术史的内部镶嵌着一部性别歧视的视觉表征史,父权制美学的厚黑学效应遮蔽并扭曲了女性的创造力、才华和本真,女人被性经济所剥削,只有其裸体才能走进这种“历史”及其博物馆和美术馆,女性裸体画也几乎是西洋画的代称——演绎着在男性的性权“凝视”(Gaze)下变形的身体政治史。
游击女孩们力图在“重写”艺术史的性别身份过程中,既作为女性艺术的当下“产婆”,又以另类手法转换被压抑了数千年的女性艺术,以直喻式的身体语言(反讽的面具和“魔鬼身体”形象、海报、日用语、明信片、引言、对话)来颠覆男性传承的学术/艺术权威,造成特殊的“后感性”效果,实现女权策略。身体的返魅,在游击女孩的话语中最终显现出超越语言的行为:超越构成自身镜像外在操控,积极寻求对话和互补的社会空间。
自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不懈地反省女性身体的历史处境与现代性权力的阴险模塑,构成了一个逶迤的系谱化脉络: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南希•夏皮洛(Nancy Spero)、卡洛丽•史妮曼(Carolee Shohneeman)、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吉娜•潘(Gina Pane)、安娜•门迪塔(Ana Mendieta)等女性艺术家以自身的身体为震惊性和挑衅性的媒介,开启了“身体寓言”的历史文本,由于大量涉及阴户、月经、子宫、卵巢、乳房诸魅惑器官的灿烂表露,而蒙受“坏女人”的诟称。不难辨析,后女性主义受到德里达批判“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启发,他的“不可言说的延异”、“自由游戏能指”书写概念,被以身体为文本的、阴性书写的革命性潜能所肯定。法国妇女出版社主编、作家艾琳.希苏(Helene Cixous)的“身体书写”就一再强调,文本的欢愉(Textual Jouissance)有如女性性欲,是无法被定义、被符码化和理论化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有机论、微生物学、生态学批评,申张了性别差异,使本文打上“身体寓言”的印记,力图指出肉体作力意象源泉和视觉形式结构的重要性。
美国当代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n)在《生为女人》一书中,阐明了“身体返魅”的基本意向:
女性的生命现象……要比我们已觉察了解的含义深刻很多。父权制的观点导致女性生命现象囿于自身狭隘的细节之中。女性主义也为此望而生畏,难以释放想象力。我相信总有一天它将认识到我们的肉体特征不是命中注定,而是一种源泉。不是对自身肉体的压制,……而必须能成为自身智慧的有力基础,并触及那和谐优美而深沉幽邃的胴体。[28]
身兼女性艺术家、女性艺术教育家和批评家的朱蒂•芝加哥在20世纪70年代以现身说法的身体文本,创作了《伟大女性》系列用来描述历史上的女性,并预示了里程碑之作《晚宴》的成功,有力阐释了有关女性身体的返魅的观念对于理解妇女如何形成她们的社会境遇的概念:
当我完成《全部曝光》(Let It All Hang Out,1973)时,它脉动的形式令我惧怕。我从来没有看过类似女性观点的图像,既强大有力又充满性欲。……在《剥开》(Peeling Back,1974)中,我‘剥开’阻挡主题的视觉形式结构,以显示我的女性本质。这对我的艺术创作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灵感主要来自长期合作伙伴——艺术批评家露茜•利帕(Lucy Lippald)对我的中肯批评。[29]
持有生态学观点的美国东海岸女批评家露茜•利帕(Lucy Lippard)在其《来自中央:女性主义论女性艺术》(纽约E.P.Dutton,1976)中认为,朱蒂•芝加哥的作品是“对抗性地使用向中央集中、有弯曲线条的、有厚实质感或激发感官享受的形式化的子宫或阴道图像”,这种阐述倒不如朱蒂•芝加哥的表白来得切实具体:
在一系列瓷器模型中[注:指《阴道是神殿、坟墓、洞穴或花朵》(Cunt as Temple,Tomb,Cave or Flower,1974)],我使用阴道的形状表达不同的自然造型。我试图由女性方式的基础,统一各种形式,并且超越奥凯菲(Georia O"Keeffe)那种被动但有力的花朵形象,而转为有活力的图像。这可以用来隐喻女性的力量,我同时延伸这种图像到《晚宴》之中。[30]
与朱蒂•芝加哥那一代运用讳莫如深的“性喻”表达与公共话语冲撞的“性喻”的女艺术家不同,20世纪90年代出道的年轻女艺术家更为直接地在性感手法里加入“坏女孩”的寓意。这一代所谓的“坏女孩”包括“愤怒的年轻女性”,“垃圾女孩”:尼科尔(Nicole)、艾森曼(Eisenman)、泰茜•伊敏(Tracey Emin)、克丽斯特菲克(Elke Krystufek)、赛茜尔•布茹恩(Cecily Brown)、莎拉.鲁卡斯(Sarab Lucas)、苏•威廉姆斯(Sue Williams)、珍妮(Jeane)、露易丝•韦尔森(kouise Wilion)、伊歌•雷克斯凯特(Egle Rakauskait)等,较为杰出的是意大利的范尼莎,毕克鲁弗(Vanessa Beecroft)。
1998年春季,毕克鲁弗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推出由20位时装模特组成的行为艺术展。这些俏丽的女模特儿有的身着金光闪烁的古驰比基尼、尖细的高跟鞋,有的则全身赤裸,面对受邀的500名观众穿梭巡游,时而冷漠地蹲、坐,时而紧瞪双眼,木然伫立。毕克鲁弗的用心在于“借尸还魂”——戏仿时装摄影大师纽顿(Helmut Newton)滥情,矫饰的广告影像形式(例如:Lives in Monte Carlo,1920;They Are coming,1981),加入女性主义观念,反其男权盯视之道而用之。
伊敏最具争议性的装置作品,是搭起一顶帐篷,里面以实物和虚拟方式标注与她睡过觉的102个男性的姓名与踪迹,其中还骇人听闻地杜撰了一个故事:虚构与其双胞胎兄弟乱伦怀孕并流产一个婴儿。1971年发表《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檄文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琳达•诺克琳(Linda Nochlin)对艺术中的“坏女孩”现象评价道:“所谓‘下流、色情’是一种魅力,它象征着活力、激情与反叛。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坏’已被女性接受,但在70年代则完全不可能。”[31]
女人并非一个抽象的不变的客体,女性身份同样也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概念的集合,它意味着女性自身不断追求可能性的无界场域。作为一种始终局部性的存在——人类有身体且他们/她们是身体,身体返魅完全符合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以及转喻下的语言唯物主义对具体事物的爱恋。后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身体犹如美丽的迷宫:蜿蜒曲折,相对而可逆,无始无终,生死轮转,令人心碎地迷恋又重返;女性身体是一座先于本质而存在的惟一寓言建筑。无论“成为一个女人”(波芙娃)或“女性并不存在”(拉康)都在力图消解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尊重女性利用其自由的表现方式。克丽斯蒂娃(Kristeva)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蒂迈阿斯篇》中的“玄牝”(Chora)概念,来解释母道——符号的神秘混沌特性,“玄牝”不可言说,无可名状,存在于任何名相形式之前,它在阴性气质和语言的流动韵律中,留下前意义化的踪迹。这不由使我们怀想起2000多年前的老子尚柔贵雌的道家美学。[32]
生态女性主义代表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想,自然/文化/女性被置于阴性的生态美学价值之下得到重估,其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象征性的及政治的关系。史普瑞纳克(Charlene Spretnak)反对将女性经验/女性的性别身份视为社会“总体化”的结构,而主张感知自然与女性经验的统一(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1997),身/心二元论被她的修辞统一为“身心”(Bodymind)。妇女身心的性爱过程,随月亮盈亏和大海潮汐的节律之定期来经,妊娠和分娩中自我/他者界限的混同,乳汁在哺育期对食物的转化等方面所产生的意识状态,都在表达和提示着存在的统一整体性,这也是生态学/宇宙论的本体奥义所在。[33]因而可称之为存在统一整体的返魅。
五、挪用的“合法化”、“拟象”或伪后现代(主义)
挪用(Appropriation)就是借用、启用;从反面来说也是非法的僭用、盗用。因此它更能表明后现代时期深刻的两歧性;关涉资本主义与技术的新的方式:信息、媒体、消费主义、美学、商品化的内爆(Implosion),以及相关的更为后现代理论所关注的主题。
挪用是取其它文脉中既存的图像——艺术史、广告、媒体现成物等,再结合新的图像和媒介材质,组接出新的作品的方法。或者,某位艺术家的名作,可能被转借为挪用者自己的表征。如此借用的形式可以视为“摭拾物”(Found Object)的平行性同义词。然而(后现代的)挪用者并不是将寻得的图像置于一件新的“拼贴”(Collage)作品中,而是将寻得的图像再处理、再描绘、或再摄制。从褒扬的方面评价,这种占取的挑衅行为嘲弄着现代主义所尊崇的原创性。现代主义艺术家频频向其艺术史上的前辈们点头示好,马奈(Edouard Manet)借用了拉斐尔著名的构图形式;而毕加索推崇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与委拉斯奎兹(Diego Velazquez);更有甚者,形而上大师契里柯(Giorgio de Chirico)剽窃自己的作品《不安的缪斯》多达18次(幅)。[34]当坎贝尔浓汤罐头(Campbell"s soup)与布利罗盒(Brillo Boxes)启发着艺术创作时,情势便已然改观;在杜桑的《泉》之后,波普艺术是挪用的先驱,安迪•沃霍尔则是其教父。
挪用与拼贴相似,不只是一种创作的技巧或方法,由于关涉到艺术品生产方式所寄寓的意识形态因素,于是成为表达对当代社会各种赞成或批评观点的工具。有关挪用的最极端例子是雪莉•莱雯(Sherrie Levine)翻拍、挪用威斯顿(Edward Weston)的摄影作品,并且将蒙德里安的水彩画当作精确的摹本。她的作品质疑构成一幅杰作、一位艺术大师或艺术史本身的传统观念。这位女性主义艺术家选择挪用男性艺术家的作品,意在让观者审视艺术史脉络中女性文化身份的位置。
杰夫•昆斯是少数以挪用手法创作立体作品的艺术家,他的雕塑由不锈钢或陶瓷制成,模仿着被丢弃的物品或“媚俗”的人物形象,近期的平面作品愈加平庸、委琐。戴维•萨利与朱利恩•施纳贝尔,则以挪用手法从历史、当代艺术与通俗文化中,创造出一种迭加的图像网面。他们的艺术是多层次自由联想的图像,往往冲着逻辑性的解释挑战。
艺术家从过去的风格模仿绘制同样的风格,导致许多人以为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复古运动,其实这种拟古只不过是挪用手段的一部分而已。同时,更多的艺术家抄袭运用现时的图像、影像,而被抄袭的影像、图像有的已是复制品。例如,电影的静止画面、流行摄影、广告图片(照片)、数码影像、时装、热门流行音乐或别人的绘画等将其原有意义抽空、移植、剔除原有的权威性与影响以致支离破碎、暧昧又晦涩。这种非平衡、非整体性,避免观众/读者一目了然的直率解答而采取迂回假借的表达方式,却正是艺术家们刻意要表达的内容。除了达达的杜桑之外,劳森伯格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后现代主义挪用手法有先导性深远影响的地位,其创作技巧如集合艺术(Assemblages)和复合绘画(Combine Painting)一直到再创作/复制(Reproduction)等,这在当今已不希奇。总之自波普艺术(Pop.Art)以来,拼贴、并置、穿插、摘录、集合或复制种种旧有的文本、图像、物像、影像等,已然是后现代艺术家最常见的方法,是否原创或真迹似乎全然不再重要。
然而,追问这种现象带来的复杂性并不止于反对/赞同的立场或采取暧昧态度。
从复制、挪用到“拟象”(Simulation),存在着跨国资本主义的“自私基因”和同化逻辑,在此变异过程中生成了一种伪后现代主义(False-Postmodernism),它以“先锋艺术”的合法化面具操纵着伪装机制,在传统审美标准判断阙如的境况下屈从于商业化的惟一尺度,从而背离了历史先锋派精神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一项未遂方案”中指责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派对现代性与启蒙运动所树理想的反动”,[35]切中肇的,不无道理,但这只是后现代主义众多形式中的支流,属于赞成并受益于既定体制的文化犬儒之道。在后现代艺术系谱中,仍然可以发现秉持历史先锋派衣钵的意识形态批判形式,只不过其先锋性不再直接对抗权力机构,而在方式上更有智能地揭示福柯所称的微动力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的机制——一种反机制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所谓观念艺术之“观念”道器从来不排斥社会学、政治学的涵义——除了诸如游击女孩、雪莉.莱雯、玛丽.凯利(Mary Kelly)、巴巴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汉斯.哈克(Hans Haacke),尚有需要另行探讨的柏林墙倒塌前后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后社会主义艺术”(Postsocialism)、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的观念艺术和台湾1980年代晚期解除戒严前后的视觉艺术。
本雅明早在1936年指出,摄影术的发明,使复制成为艺术生产力解放的标识,艺术原创性的“灵韵”(Aura)与自主性会消失,从而也将会带来艺术的民主化。事实上,在伪后现代主义那里,此项忧喜参半的预言已走向本雅明的政治无意识深渊——知识的反面不是无知,而是蒙蔽与欺诈。伪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与跨国资本主义玩家,循从再生产方式扩展的模式达成了共识。复制/挪用/“拟象”的游戏和制造某种知识(无知阴谋的制造)有关。表面上,艺术生产力、艺术品的生产正在大批量地扩展成为广大民众包括第三世界皆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唾手可得之物,而在现实经验中却日愈受到跨国资本(后现代帝国经济)的操控。
杰姆逊在分析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一系列复制形象,如玛丽莲•梦露中就发现了“形象的物化”。作为超级影星的梦露被变成一种“好莱坞”商业文化符号,是她所不能省视的,影星标志着文化市场偶像,体现出时髦、诱惑、欲望、商业价值的“类存在物”或“拟象”,最终她被异己的媒介(货币)所占有,成为货币的属性:
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人的力量。这样,它的奴隶地位就达到了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藉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3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沃霍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相反,他是一位商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公开宣称“我想变成一台机器”,这种表白潜藏着对世界的冷漠、厌倦和讽喻的雅痞态度。在这个机械的时髦主义者背后,实际上是客体、影像、符号、“拟象”的潜在上升,同时也是价值的潜在上升,其适切的例证是艺术市场本身。……沃霍尔自然是以“拟象”取消现实、不断增加“拟象”以致终结一切美学价值的后现代媚俗艺术家。问题是杰姆逊等知识左派的某些后现代话语,往往把后现代局部而表面的商品化特征理解为本质特征,存在着“政治无意识”的归约简化倾向。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遗传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总体性精神;以波普和后波普艺术为代表的流行艺术也并非后现代艺术的唯一形式,尽管它从新的艺术风格方向象征性地预示了后现代文化性质的转型,却并不具有1960年代就已经成熟的地景艺术、贫困艺术、行为艺术等后现代艺术的典型性与颠覆性色彩(即便波普艺术是美国化的后现代典型),更何况在美洲大陆还有影响全球文化视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将后现代简化的倾向——至少在美学的范围已经如此——易于导致一种庸俗的后现代主义(Vulger Postmodernism),继而势必抹杀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之复杂异见,混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之深刻洞察。
应当承认沃霍尔机械时髦主义的幽默不只是“博人一笑”,而在“笑”的背后还藏着一把自由市场经济的双刃剑;当利奥塔以“作为消费者的知者”取代传统训练的知者时,他既不敢坦然维护“新知者”的立场,也不置可否地隐约承认差异性被彻底商品化的无耻现实。
在伪装机制已被资本帝国“合法化”的媚俗艺术中,如果谁还在“诘问”或“区别”这究竟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观念”表现方式,还是一种滑稽模仿式的玩世不恭——或者象上一代思想家探索原创真实性的“灵韵”那样来“区别”复制/挪用/“仿真”(Simulacra)之间的微妙技巧,那么,假如他不是甘愿被愚弄,必定也难以避免伪后现代主义的共谋和艺术史形象贮藏库“扒手”的嫌疑——这个判断同时关涉到全球化/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命运和文化身份问题。
后殖民—东方主义则代表着另一种伪后现代主义,它庇护并怂恿艺术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大腕以及形形色色的平庸大师。在大众消费文化领域,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符号的操纵,广告的挪用/复制/“仿真”提供了后殖民文化的绝顶恶例,如“贝纳通的联合色”(United Colurs or Benetton)这一口号即虚拟自夸一种“享誉全球通行无阻的国际名牌”,贝纳通肆意“挪用”新闻图片并“转换”为“创意广告”,使新闻照片的“超真”性质迅速商品化,从中获利,典型的“创意”是一个白人婴孩吸吮一位健壮体格的黑人女性乳房,一名非洲雇佣兵手握一块充当战利品的人类大腿骨,此类被“挪用”的影像符号实质是一种被剥夺的文化身份并丧失了与其相关的历史脉络,它所显示的黑人女性只配做“第二性”之外的“乳娘”角色,非洲雇佣兵的“另类”形象被扭曲为永远不可以进人“文明社会”的“食人蕃”。
后现代世界也是一个为单一超级强权主导的世界,旧有的欧洲殖民已被新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所替代。在此境遇中,东方主义被转化为一种全球化的权力症候,变成实践功能的权力工具,并不懈遏制外部的质疑和反抗。在第三世界沉默的大陆架和潮湿的丛林中,后现代主义跟随着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式的依赖、寄生情境携手潜行。后殖民的内化症状随之显现:盗版、走私和毒品的经济学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粘合剂;“新人类”带着健忘症狂热拥抱美国倾销的好莱坞影视文化;经济新贵与“新生代”的歹徒饶舌式(Gangsta Rap)传媒集团合谋,垄断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中产阶级审美享乐主义赞助着一种基于虚脱和赝品的艺术及其市场,使“真正的赝品”(Genuine Lmitations)遍地开花,充当时尚。与此相呼应的则是第三世界先锋艺术的后殖民化,19世纪小布尔乔亚式的阶级晋身在此类艺术家的意识和行为中重演,他们纷纷寻求一种伪后现代主义予以认同和包装的理念与风格样式,惯常将旧意识形态的残留意象,持以白痴式的加法或毫无商洽地盗用,赢得艺术市场意识形态的嘉奖褒扬。
悖谬的是,艺术的“成圣”过程,既是鬼魂也是偶像的形成过程;艺术的卖淫形同黄金的卖淫。艺术的终结只能印证艺术向其时代所做的伪证,屈从于资本主义的魔法和幻影,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样:货币存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一直(从来)都是一个伟大的影子:“Was Ubrigbleibt Ist Magni Nominis Umbra”、“铸币的肉体只是一个影子”(Numoch ein Schatten),[37]货币的意识形态是鬼魂、幻觉、幻影、表像的全部表征。
上述状况在更为激进的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思考中,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已经无法理解消费社会及其文化美学,犹如幼童把自己的镜象当成真实的自我并完成对自我的认同,在资本主义形而上学的生产之镜中批判其社会,同样也是一种幻象。这项论述由此而发展为以符号媒介—消费主义模式为中心的“超现实世界”,在那里人即符号,大众即媒介,“诱惑即命运”,[38]而一切诱惑都是裸露的,如同产品与真理。就连物质与表像、事物与观念之间也不再有区分。当“仿真”和“拟象”摧毁了现实中的一切对立面,进而把现实完全内爆于自身,“超现实”就成为一个彻底的自我指涉的世界。[39]在这些观点中,鲍氏“拟象说”对我们解释后现代的视觉符号生产无疑具有启示意义,而对于那些个尚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纠缠、错位、混杂的社会,则纯属不经之论,因为赛博乌托邦—互联网络既可以给第三世界的大众社会大众带来福音,也可以为福柯所揭示的“规训社会”、“全景监控”增势,造成“美丽新世界”式的奴役方式。
结 语
不言而喻,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什么与艺术相关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力、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等等,都成了问题。人们原来以为直觉与朴素艺术方法的丧失,会随着反思带来的无限广阔的新机遇而得到弥补。然而事情并未如愿以偿。[40]
这段引文与本文开头不确定性问题构成了互文性,其所描述的情景俨然就是后现代艺术的处境,但它确乎出自阿多诺(Theodr W.Adrono)写于1969年的《美学理论》,这着实令人惊异。
我们在经验中发现,后现代艺术和美学超越了现代性宏大的统一性原则的最后限制,使自身建立在个体心性、解构—建构的空间书写、身体文化的自然返魅等价值意义之上,艺术哲学和艺术历史的地平线渐次露出新的本体晨曦。
然而,随着全球化已经把空间变成信息呼吸道,艺术创新变化的心率日益加快,以至没有一种新形式可以比被它取代的形式更具有优越性。各种观念、手法、媒介材质以及“视觉工厂”的无界开放,使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艺术,从而任何人都可以是艺术家。这种状况表明,如果在原则上承认任何对象可以是艺术,那么,普遍的创新,新的方法和范式开发的可能性就会带来新的陈腐;如果艺术家不再是一种象征着社会性或创造力的身份,那么世上就不会有艺术家。我们果真要让上帝连同主体、作者都一并殁去?
这样,“艺术何为”的追问,就再次迫使本文的意向回到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中:这就是继承历史先锋派精神“拒绝艺术的彻底商品化”和“整体功能的理性体系”;[41]同时努力恢复艺术拥有自身丰沛法规的作用,亦即“艺术使真理产生”的方式——“它是真理进入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即真理成为历史性的方式。”[42]应该看到,多元主义情势在本时代已经不可逆转,不可能出现全球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至少在艺术领域发展多元性方法论的积极形式是值得珍重的。只有在不同传统、不同心灵、不同理想的交锋—对话层次上才会生长多元性,理想的知识建构该是一个相互包容又相互激荡的海洋。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概念实在论的陈旧哲学立场,放弃唯名论的“后现代”术语,利用前现代性、重建现代性、开发后现代性。
上帝掰开面包,面包掰开上帝。
2005年10月修改
注 释
[1]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肢解俄尔浦斯:走向后现代文学》(The Dismemberment Of Orpheus:Toward A Postmodern Liter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82年版,PP.267—268。这个表格所列出的30多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二元模式的栏目,对后者(右栏)表现出明显的价值肯定倾向。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 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版,第296—300页;另见斯托(Charlotte L.Stough):《怀疑主义的认识论研究》(Greek Skepticism:A Study In Epistemology .Berkeley: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3]见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刘象愚译,时报出版公司,台北 1993年1月版,第三章第5节关于“不确定性/内在性”探讨;第四章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进一步定义,第155页。
[4]罗布—格利耶:《快照集 为了一种新小说》,余中先译,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2001年10月版,第211页。
[5]布托尔:《变》,杜普芳译,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83年4月版,第1页。
[6] [7]多尔.阿西顿:《20世纪艺术家论艺术》,米永良 谷奇译,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1989年斑,第132—133页;另见海涅.史塔赫豪斯:《波依斯传》,吴玛俐译,艺术家出版社,台北1991年10月版,其中“学说”章专门评介波依斯“扩张的艺术观念”、“社会雕塑”和有机材料问题。
[8] 贝恩特.巴尔泽编着:《联邦德国文学史》,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460—461页。
[9] 美国“语言诗”派(Language Poems),系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旧金山、纽约和华盛顿等地出现的诗歌写作群体,其诗歌作品的语言特征是强调语言重要性的同时消解通常的语言关系;注重诗歌的政治作用。
[10]杰罗姆.马扎洛(Jerome Mazzaro):《后现代美国诗歌》(Postmodern American Poetry),依利诺斯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80年版,P.viii。
[11]见《楞加师资记》第一卷。
[12]见《坛经》“定慧品第四”。
[13][14]见《五灯会元》第一卷。
[15]铃木大拙:《禅者的思索》,未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9年10月版,第25—27页。
[16]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引王尔德语,王宁译,原载《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52页。
[17]]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一般原则l”的第一章“语言符号的性质”,高名凯译,岑麒详、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版,第100—106页。
[18]参见德里达《意义:“与亨利. 隆塞的会谈”》,1967年12月号首次发表于《法国文学》第1211期,第6—12页,1981年收入《立场》首篇。(Jacques Derrida, Position, Trans. by Alai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19]见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99年12月版,第二部分第一章“文字的暴力:从莱维.斯特劳斯到鲁索”。
[20]罗兰.巴特:《文体及其形象》(Style And Its Image),原载查特曼(S。Chatman)编《文体文论集》(Literary Style:A Symposium),纽约1971年版,第10页。
[21]见苏珊.桑塔格为本雅明《单向街》(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所撰英文版导言。Edmum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译,New Left Books公司,纽约1979年版。
[22]Ernst Bloch:“Recollections of Walter Benjamin” On Walter Benjamin, Critical Essay and Recollection, 1976,P.340.
[23]Walter Benjmin:“Theological—Political Fragment”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P.156.
[24]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精校本),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版,第130页。
[25]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国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69页。
[26]查尔斯.詹克斯(Chcrles Jencks)编:《后—先锋派:80年代的绘画》(The Post—Avant—Garde:Painting In The Eighties)学院出版社,伦敦1987年英文版,P.47。
[27]福柯:《这不是一只烟斗》,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1998年12月版,第114页。
[28] 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n):《生为女人:作为经验和制度的母性》,诺顿出版社1976年版,第62页。
[29][30]见朱蒂•芝加哥《穿越花朵》(Through Flower),图版,作品自释部分,纽约1975年英文版。
[31]Michelle Falkenstein,:“What’s so Good About Being Bad”, New York:Art News Volume, Numberl0 ,1998.
[32]见老子:《道德经》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33] 参见史普瑞纳克(Charlene Spretnak):《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张妮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认知身体”一节。
[34].参见Kim.Lrvin:Beyond Modernism:Essaya On Art From The1970s And1980s ,有关复制、挪用的专题论文“骗子”德. 契里柯V. S. “沃霍尔”,纽约1988年版。
[35]参见Jurgen 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t ”In Hal Foste,Ed.,Postmodern Culter,Londen:Pluto Press,1985,Pp.3—15.
[36]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1版.第13卷,第99页。
[3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版,第154页。
[38]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版,第180页。
[39] 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 Tr.By Sheila Faria Glaser,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Michigan:1994,pp.121—127.
[40] Theodr W.Adrono:Aesthetic Theor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P.1.
[41] Theodr W.Adrono:Aesthetic Theor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P.339.
[42]Martin Heidegger:“The Origin Of Work Of Art,”In Basic Writings,San Francisco:1977,P.187.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