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阅读周刊“读书在线”栏目,2019年2月)

王家新,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教授。1957年生于湖北。1992—1994年在英国等国旅居,回国后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楼梯》《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坐矮板凳的天使》《取道斯德哥尔摩》《雪的款待》《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选》《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等。
1.您最近在读的是哪本书?为什么读它?
最近在读杨周翰译奥维德《变形记》、贺拉斯《诗艺》(合订本,“杨周翰作品集”之一,上海人民),自年前在南京先锋书店购得该书后,就陆续在读。我一直感到自己需要重返中外古典,这并非为了什么“守成”。读了奥维德,就理解了曼德尔施塔姆为什么会说他自己“诞生于罗马”,为什么会声称“古典诗歌是革命的诗歌。”
2.您阅读次数最多的书是哪本?为什么?
近半年我读米沃什《冻结时期的诗篇》(林洪亮译,上海译文)最多,有两遍,都是旅行时带上读的。一是这本诗集大都是米沃什早中期最好的诗,一是林洪亮翻译得也不错,能够传达出米沃什的风格和特有气息。米沃什在晚年为这本诗集所写的前记也使我深受激励,他毫无疑问是位巨匠,但却表达了面对缪斯赐予的谦卑。这是一个伟大诗人通过他个人漫长的道路所重获的虔敬,尤其让人感动。在我们这个年代,许多人都已骄狂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发自生命的虔敬,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说实话,面对米沃什这样的诗人,我只能感到羞愧。
3.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哪本?为什么?
近来读到的好书中,有黄灿然译的《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译林,“俄耳甫斯诗译丛”,凌越主编)。去年六月在柏林期间,我曾专门去访问布莱希特的故居和墓地,也曾试译过一些他的诗。但黄灿然的这本更全面,也更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布莱希特。过去我们热衷于流行的现代主义,还体会不到布莱希特诗中那独特的腔调和刺人的老辣。但现在不一样了。布莱希特在希特勒时期面对恐怖言说的良知和勇气,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罕见的声音。让我深为佩服的,还有他那反讽的心智和独异的艺术才能。正如他的戏剧革新,他在诗歌写作上也为我们打开了诸多新的可能性。我愿意向老布好好学习。
黄灿然的这本布莱希特诗选,如同他译的卡瓦菲斯,都属于从英译中“转译”,这也再次证明了这也是抵达到原作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在这里并非提倡“转译”,而是要为优秀的或“必要的”转译本说几句。近来有些人对“转译”刻意贬损,实际上并非从文本质量、翻译艺术、中国诗歌和读者的需要出发,而不过是在找一些说辞。译诗当然最好从原文译,但我们同时得破除那种盲目的“直译可靠论”或“直译优越论”。这就是说,判断一个译本,不仅要看它的来源,更要看文本本身和翻译本身。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大量从原文直译的译文并不理想,甚至充满了很多“硬伤”。倒是一些转译本问题要少一些,为什么?因为从英译中转译,首先就借助了英译者对原作准确、透彻的读解。当然,原因还在译者:由什么样的译者来译?限于篇幅,这里不多展开。我们应看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对当代诗歌有重要影响的译诗集,有许多都为从英译中转译,如北岛译《北欧现代诗选》、绿原译米沃什《拆散的笔记本》、王希苏、常晖译布罗茨基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叶维廉译《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张曙光译《切.米沃什诗选》、黄灿然翻译的卡瓦菲斯、瓦列霍、陈黎翻译的辛波斯卡、李以亮翻译的扎加耶夫斯基、陈东飚、西川等人翻译的博尔赫斯,傅浩翻译的阿米亥,等等。年前在海口,我与作家韩少功相聚时也谈到当年他翻译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影响。韩少功的翻译为从英文中转译,后来也有不同的“直译本”出现,但他对昆德拉的“发现性”翻译是可以抹杀和取代的吗?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向冯至先生学习。冯至本人深爱里尔克的长篇散文诗《旗手》,但卞之琳从法文中转译出该诗后,他就没再译,因为卞先生的转译本十分优异和可靠,他本人只是在后来从德文原文帮卞先生校看了一遍。
这也说明,不同的翻译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一种排斥关系。伟大的作品不仅召唤着翻译,它可能也不拒绝“转译”,经过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转译”,它会回到一个新的、更丰富的自己。不管怎么说,如同“直译”,优秀的“转译”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最起码它会拓展、刷新人们对诗和诗人的认知,或用本雅明的话说,它会服务于“语言的互补关系”。
4.您床头现在放着哪些书?为什么读他们?
我现在床头放着的是阿九翻译的拉金诗全集(河南大学出版社)、胡桑翻译的奥登文论集《染匠之手》(上海译文)和欧阳昱翻译的阿米亥诗集(四川文艺),它们都很厚,放在床头上慢慢读正合适。
5.您最欣赏的作家有哪些?为什么?
我喜欢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有许多。诗人中,在我的《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人民文学,2017),专门写到十五、六位曾对中国当代诗歌和我本人有深刻影响的西方和苏俄、东欧杰出诗人,书名“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取自叶芝“The Master who taught my soul to sing”),也正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还有很多未包含进来,尤其是中国古典诗人(这也许留待以后了)。这也是我和老朋友多多的一个区别,多多早年曾被茨维塔耶娃、波德莱尔、洛尔迦吸引,现在就只喜欢策兰、夏尔,而且言必称策兰。我理解多多为什么这样,而我则是“转益多师是汝师”。我向大诗人学,也向小诗人学;我向好诗人学,也向坏诗人“学”;我向鲲鹏学,也向一只小麻雀学。总之,我现在的“课程”就是向一切人、一切事物学。
6.您最期待出新作品的作家是哪些?为什么?
我最期待出新作品的是诗人布罗斯基,可是他已英年早逝了。他未能活到像米沃什那样长。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依然活着,幽灵般活着。这里,以我上个月写的一首小诗为证:
一个梦
很怪,昨夜竟梦到布罗茨基,
嘴里叼着烟,怀里抱着一只猫,
在那里发表宏论……
接着他真的就变成了一只披着满头金色头发
有着神秘眼瞳的波斯猫,
而在他用爪子猛地挠我的一瞬,
我醒来,灼伤般地醒来……醒来,我想我已有好多天没有写诗了。
或,写得太多了。
7.在您看来,诗歌翻译应该秉持哪些原则?怎样的翻译才是好翻译?您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过程中,有哪些感想?
说到“原则”,对我来说首先仍是“信”(至于“信达雅”的“雅”,早已为我们所质疑)。我认同的,也是那种“可信赖”的译者。当然,问题更在于怎样达到这种忠实可信:有那种亦步亦趋的、字面意义上的所谓忠实,但也有一种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高的忠实”,那是卓越的、伟大的翻译所达到的境界。
只不过直到目前,有些人对“忠实”的理解仍是那样陈腐和死板,或者说,他们对翻译的认识仍停留在那样一个最初级的阶段。翻译,当然要求“忠实”,但是,如果不能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赋予原作以生命,这样的“忠实”很可能就是平庸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本雅明就这样说:“如果译作的终极本质仅仅是挣扎着向原作看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译作。”比如陈敬容译里尔克《预感》的名句“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如按德文原文和英译,都应译为“知道,了解”,而不是“认出”。但是,陈敬容译得又是多么好!这才是风暴到来之前对生命的最深刻辨认。也正是这样的翻译,使里尔克成为了里尔克。
至于庞德、王红公、策兰等西方诗人译者的翻译,我也都做过专门研究。他们的翻译成就和影响,也印证了本雅明所说的“原作在他的来世里必须经历生命的改变和更新”。我虽不像他们那样大胆,但有时也不免冒一下险。比如我译的茨维塔耶娃的《这样的柔情是从哪儿来的》最后几句“我该拿你怎么办——你这/年轻狡黠的、飘泊的歌手?/你的睫毛——能不能更长一些?”一位汪姓译者抓住这一点做文章,甚至说我什么“造假睫毛”,因为原诗应为“你的睫毛比任何人的更长”。我当然知道,我依据的两个英译本其中之一就是这样译的:“your lashes are—longer than anyone’s.”但是我取了另一个英译本“…whose lashes couldn’t be longer ? ”该诗是茨维塔耶娃写给与她短暂相恋的曼德尔施塔姆的,我有意这样译,把全诗最后变为带有反问、祈愿意味的句式,不仅为了传达原诗中的那种柔情和留恋,也为了在最后带出一种余音未尽的双关效果。难道这就不“忠实”了?
问题就在于,什么才是诗的翻译?什么才是诗的创造?像汪姓译者这样死抠,真让人不免怀疑他读了“白发三千丈”后是不是真的要拿起尺子去量李白的头发!好在懂诗的人们都自有判断。来自俄罗斯的凯瑟琳就通过俄文、英译、汉译的比较分析了我翻译的茨维塔耶娃的《约会》,文前她引用了阿克萨科夫的话“......那种译者自己也参与了他的作品诞生的艺术家的伟大的创作时刻。”这已提示了翻译是译者与作者的合作——为了一部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的诞生。她分析了我为什么把“Living on. As the earth continues.”(“Землю долго прожить!”)译为“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她指出:“把‘大地’(earth)翻译为‘泥土’,因为这在中文中更具体,更有一种生命血肉的感觉。实际上,他这一句译文在中文中给人的感觉更强烈,也更好”。而全诗的最后一句“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Feinstein的英译为“In the sky arrange my burial”,原文为“Я себя схоронила в небе!”),她认为“这一行真的很强有力,悲痛并崇高。 Feinstein和王家新的译文都很确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意思。比较起来,王家新用的‘是’比Feinstein的‘arrange’(‘安排’)更为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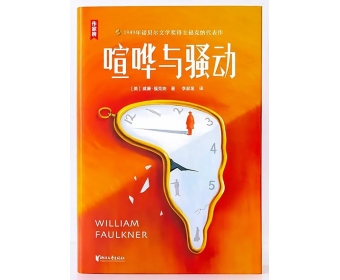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