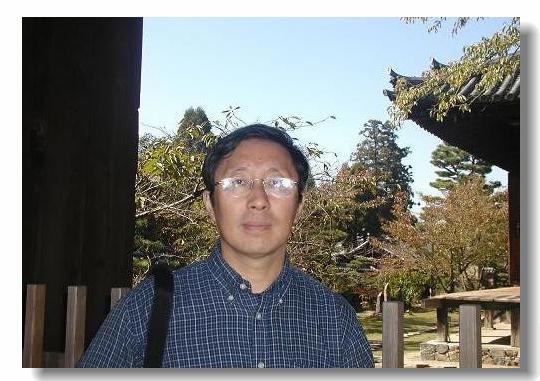
许纪霖
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
——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文 / 许纪霖
摘要
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关键词
鲁迅 ; 周作人 ; 陈源 ; 《现代评论》 ; 《语丝》 ; 《莽原》
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目录
一 出身、场域以及与体制的关系
二 绅士与名士:“文化惯习”的对立
三 语丝派文人内部的名士与斗士
四 狂飙一代的“新流氓主义”
五四的新式知识人,在1910年代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然而,这批曾经在同一个壕沟里向传统旧学并肩作战的同道,进入1920年代之后步入了分岔之路。其中,最大的分歧有两条脉络,一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相信救世之道在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后来趋向了温和的自由主义;而坚信通过皈依主义、全盘解决中国危机的,随之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另一条分歧的脉络,在依然坚守启蒙理想的知识人中间。《新青年》随着陈独秀迁到上海、变为中共的机关刊物之后,京城知识圈中,继承《新青年》启蒙传统的杂志,最有影响的,当为《语丝》与《现代评论》。这两群知识人虽然同以启蒙者自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一半的精力用来打内战,其中有很多意气的成分。
值得追问的是,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分歧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往不少的研究将二者的分歧,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为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固然不错,然而,知识人的内部分化,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有时候文化气质的不同,要比意识形态的分歧,更能导致情绪上的对立。这两份杂志,虽然活跃于国民大革命早期,但两派知识人依然坚守启蒙的初衷,并不热衷皈依什么主义,更对政治本身保持警惕的距离。显然,彼此间的争论,文化上的相互鄙视要远远高于政治之间的分歧。
本文将从这一特定的问题意识切入,透过激烈争论的表象,研究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知识人背后的“文化惯习”差异,如何形成了名士与绅士之间的不同格局,二者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延长线上,他们与学术体制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其次,分析在语丝派文人内部,作为名士的周作人与作为斗士的鲁迅又有什么样的微妙差别,酿成了之后进一步的分歧;第三,鲁迅在《语丝》之外与高长虹等合作创办《莽原》,更激进的狂飙青年又如何攻击周氏兄弟,试图从五四老师一代手中夺过舆论的话语权。1920年代中期启蒙知识人内部这些剧烈的分裂与对抗之中,鲜明地呈现出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的不同面相。
一 出身、场域以及与体制的关系
《语丝》与《现代评论》,都是在1924年底创刊,几乎同时诞生。这两家杂志的精神趋向,都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传统,有一些共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现代评论》的主将陈源在《西滢闲话》中有多篇讽刺中国国民的文章,语言极其刻薄:“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也一声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他还挖苦小市民根深蒂固的奴性,说沪案(五卅惨案)的时候全国总罢市,北京没有一个铺子关门,也没有一个店下半旗,“然而只要警察下一个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挂上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挂上龙旗”。几乎与此同时,《语丝》刊登了林语堂致钱玄同的信,林语堂咬牙切齿地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钱玄同回信表示赞同:“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在“群氓”面前,都有一种傲慢的精英意识,代表着五四知识人共通的精神趋向。
然而,到了1924年的五四末期,已经与新文化运动早期迥然异趣,旧学的敌人已经被打败,舆论的话语权转移到新派手中,随着新学的引入和海外留学生的回归,各种互相冲突的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新派知识人的队伍也开始庞杂、多元,于是,启蒙阵营之中“态度的同一性”日趋稀薄,而相互之间的分歧开始表层化,话语权的争夺,从新派与旧派之间,转移到启蒙派内部。于是《语丝》与《现代评论》,成为了京城知识人的主战场。
这两家杂志,都拒绝标榜任何主义,在思潮上也有兼容并包的大度,周作人为《语丝》拟的《发刊辞》声明:“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这种表白有鲜明的五四遗韵,的确,语丝派的核心作者群很多就是原来《新青年》、新潮社的成员:周氏兄弟、俞平伯、陶孟和、刘半农等,他们所继承的,是五四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无独有偶,《现代评论》在《本刊启事》中也宣称:“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既然不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旗帜,又都以自由与独立为标榜,向各种歧见开放,那么,他们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核心分歧,在于“文化惯习”的不同。“惯习”(habitus),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与习惯(habit)不同,所谓的“惯习”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位、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所以对立,主要不在于意识形态,而是各自的共同体所形成的“文化惯习”不同。
简单地说,现代评论派知识人的“文化惯习”是绅士型的,语丝派知识人的“文化惯习”是名士型的。两个杂志的冲突,正是两种“文化惯习”的对抗。
“文化惯习”的形成,与不同的场域有关。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要了解两派知识人不同的“文化惯习”,首先要认识他们各自所活动的场域。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差异,在于他们与学术体制的关系,前者的场域在体制之外,而后者的场域在体制之中。
这里说的体制,并非政治体制,而是知识人所栖身的学术文化体制。在传统中国,知识人活动的场域,乃是以科举体制为核心的知识—政治系统,知识人只有获得功名,特别是举人、进士以上的高级身份,方能成为士大夫,进入这个体制。这个士大夫体制,奉圣人的经义为经典,有共同的价值观;以纲常名教为尺度,有内外的交往规则;以诗书琴画为中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长期在士大夫群体中浸润的读书人,在半封闭的场域中逐渐熏陶出士大夫的“文化惯习”。从汉代的儒生到宋元明清的道学家,都具有一脉相承的正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可以将之理解为是一种绅士风度。
与绅士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种名士的气质。所谓名士,也是正途出身,只是少了一点正统士大夫的方巾气,多了一点文人的潇洒自然、风流倜傥,最典范的如魏晋的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有狂狷豪放之气。他们有士大夫的身份,却不屑于在体制内部的场域活动,更愿意在山野自然或江南园林喝酒吃肉、抚琴低吟,创造一片个人自由的小天地。从魏晋的嵇康、阮籍,唐代的李白、李贺,明末的李卓吾、公安三袁,到清朝的袁枚、龚自珍,在中国历史当中串联起了一条与绅士迥然不同的精神脉络,所谓的名士风度、名士派头,指的就是这种与正统道学家对峙的“文化惯习”。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的士大夫体制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学术知识体制。然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惯习”,却以新的方式延续下来,演化为新绅士和新名士,新绅士的活动场域主要在大学体制内部,而新名士虽然也不乏大学教授的职业,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更多地以文人的身份在学术体制外的民间报刊上获取文化的象征资本。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如同法国的启蒙运动一样,其实是一场文人的运动,虽然《新青年》的核心作者大都是大学教授,但除了胡适、高一涵等个别人在国外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外,大部分人都是半路出家,像他们的前辈梁任公一样,都是以文人的风格译介西学、指点江山。《语丝》被认为是《新青年》的继承者,部分也是因为这种文人论学、文人论政的话语传统。曹聚仁说:“在五四文化运动低潮之际,《语丝》是填上了《新青年》的地位了。”语丝派中,一部分是学术体制中的名士: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俞平伯、江绍原等等,另一部分是职业编辑或自由撰稿人,比如川岛(章廷谦)、章衣萍等等,还有在教育部担任佥事的鲁迅。无论在学术体制内外,语丝派诸君都有共同的文化徽记:名士派头。
然而,到了1920年代以后,一批拿了“庚子赔款奖学金”或者自费出国留学的,纷纷拿了欧美洋学位回到中国,这是五四前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现代评论》的核心作者王世杰、陈源、徐志摩、周鲠生、钱端升、陶孟和、杨振声、李四光、陈翰笙都是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海归。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专家学者,与语丝派那些短期求学日本的“土鳖”教授在精神上截然不同,他们深受中西主流文明的熏陶,厌恶玩世不恭的名士派头,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道学家遗韵,也有西洋文明的绅士气质。这些西洋的留学生们,很多是拿了“庚子赔款奖学金”,生活比较优裕,不像语丝派文人当年留学日本时混迹于底层,吃过苦,受过累。杨振声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曾经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美国文化已足以与欧洲比并,一般人民又多安富尊荣,所以此处学生的生命较为安泰。来此留学之中国学生,久居乐土,几忘中国所处之地位与一般学生奋斗之艰难矣!”他们回国以后共同创办《现代评论》,虽然不是故意要与《语丝》打擂台,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派知识人很快变得阵垒分明,发生了冲突。像顾颉刚,早年因为是新潮社社员,也没有出过洋,本来属于语丝派,但他的精神气质更接近学术体制里面的绅士,与语丝同人的名士气格格不入,后来就跑到现代评论派的阵营去了,从此与鲁迅结下了心结,在同事厦门大学的时候,两人闹得沸沸扬扬。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哈佛硕士毕业的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林语堂,按理说应该属于海归阵营,偏偏他从小就有潇洒自由、性灵活泼的名士派头,在哈佛求学的时候就看不惯学院中人一本正经的工匠气和绅士味,回国以后宁愿加入语丝派阵营,跟随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叫板论战。
两派知识人冲突的背后,固然有政见的不同,但“文化惯习”的对立所导致的相互看不起,显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留学西洋的知识人自视甚高,相信自己有特殊的知识,理应是社会的中坚。鲁迅称这些西洋留学生是“特殊知识阶级”,他说:“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鲁迅说这些如过江之鲫归来的留洋博士,在国外未必好好读书,只是关起门来炖牛肉,“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炖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
鲁迅的挖苦有他的刻薄,但也并非全然没有理由。就比拼学问而言,至少海归们的国学就不是语丝派的对手,无论是要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学衡派,还是同样批判传统的现代评论派。鲁迅随意挑出《学衡》杂志的几处硬伤,讽刺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我所佩服的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有发表的勇气”。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是不屑与其争之,而对同样是新文化阵营中的《现代评论》,因为它在新派年轻人里面拥有与《语丝》同等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竞争者,鲁迅则是紧紧盯住不放。有一次,陈源随意说了一句:“就以‘四书’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鲁迅立即敏锐地抓住对手的破绽,狠狠挖苦了一番:“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即便陈源想去北大图书馆临时抱佛脚,“却连‘佛脚’都没有”。
而现代评论派那一边,也看不惯语丝派的名士气,更认为他们没有学问,“不在文学水平线之上”。陈源承认鲁迅的小说是好的,但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他公开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给徐志摩的信,嘲笑周氏兄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接着又补了一句:“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现代评论派不承认对手是学者,对此鲁迅颇为不屑,他说“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说我没有“学者的态度”。“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
启蒙运动本身就具有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气质,法国的启蒙运动有伏尔泰与卢梭的双峰对峙,德国启蒙运动中有康德、黑格尔理性传统和歌德开始的狂飙运动,同样,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是如此。张灏教授指出:“理性主义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浪漫主义却是讴歌情感的激越。五四思想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想,同时并存而互相纠缠、互相激荡,造成当时思想风云中最诡谲歧异的一面。”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并没有完全分化,《新青年》《新潮》启蒙者的内心世界当中,同时内涵着这两种精神。然而,到了1924年,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正式分道扬镳,其标志就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的精神对峙。
这两家杂志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继承五四的精神传统,他们的关切是共通的,批评的对象也是相近的,不是军阀,就是国民性。不过,两家参与现实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语丝》的气质更接近《新青年》和《新潮》的话,那么,《现代评论》则继承了《每周评论》的风格,关注“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宣称“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现代评论派是专家型学者,不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就是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他们对时事的分析是专家型的,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一事一议,就事论事,秉持专业主义的立场,理性而温和。五卅惨案发生以后,虽然王世杰、钱端升、周鲠生他们也是义愤填膺,但在讨论如何应对如何抗议的时候,并非一味地拉高声调、采取激进的姿态,而是从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详细分析如何通过法律和外交的手段,在现有的格局之下通过有节制的抗争,为国家赢得最大的、可能的利益。
现代评论派以专家自命,一言一行背后都要讲究学理。不要说王世杰那些学有专攻的社会科学家,即使像陈源这样的人文学者,也是言必寻据,喜欢“掉书袋”。作家苏雪林如此评论陈源的“闲话文体”:“《西滢闲话》何以使陈氏成名,则因每篇文章都有坚实的学问做底子,评各种事理都有真知灼见。尤其时事文章对于当前政治社会的各种关系,分析清楚,观察深刻,每能贡献很好的解决方案。”苏是陈的好友,自然有溢美之词,但这段评价很能体现现代评论派作文论事的风格:一习惯搬用专业学理,二喜欢分析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相比现代评论派的专家型学者,语丝派基本是一群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文人。《语丝》杂志与政治保持谨慎的距离,主要从事于文化和社会批评,《语丝》编辑孙伏园说:“《语丝》同人对于政治问题的淡漠,只限于那种肤浅的红脸打进黑脸打出的政治问题,至于那种替政治问题做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等等问题还是比别人格外留意的。”《语丝》不关心政治本身,但非常在意政治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这才是启蒙所要针对的问题所在。不过,到了国民大革命前后,政治大事接踵发生,如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语丝派有满腔的激情与正义感,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独缺的是专业主义的知识。五卅惨案之后,《语丝》上弥漫的多是这样感性而激情的文字:“我们不是刚睡的狮,我们是将死的狮子……可怜而又可耻的我们!”“拿着白旗在街上讲演的兄弟们和姊妹们!你们不要痛哭流泪地多发议论了。你们应该流血、不应该流泪”;“我们不能屈服,我们宁愿灭亡,全体灭亡”。《现代评论》将五卅惨案作为一件外交事件来对待,态度专业和冷静,同样是启蒙,诉诸的是读者的理智;而《语丝》以浪漫主义的激情话语,更多诉诸的是民众的情感。现代评论派从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出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可能”,但语丝派的姿态则是马克斯·韦伯的“信念伦理”,以一己的信念价值判断是非善恶,不在乎运动所带来的实际后果。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专家与文人碰撞在一起,自然是刀光剑影、火星四溅了。
三一八惨案是另外一个例子。两派都对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群众强烈不满,但现代评论派专家们的态度是冷静而现实的,希望通过法律解决,而语丝派文人是激愤的,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连一向平和温热的周作人也一连几天什么事都做不了。正在这个时候,陈源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希望“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未成年的男女孩童们更“不参加任何运动”,并且暗示背后有黑手“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陈源的这种看法是一贯的,因为他自认超越于任何党派与政治势力,“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这种自命站在独立与理性、对强权和民众两边都批评的立场,本身并没有错,但一旦运用于刚刚发生了流血与屠杀具体场景,对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自然激起了语丝派文人的愤怒,周作人以少有的愤怒揭露《现代评论》收取过章士钊转来的段祺瑞提供的一千银元开办费津贴,批评陈源“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理论,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
语丝派文人在学术体制的边缘乃至外面,因此他们对体制那个场域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其与官场和军阀有千丝万缕的暧昧联系。鲁迅厌恶学界的官气,认为“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他所暗指的就是现代评论派这些在体制里的学者。在女师大事件当中,学生是“鸡蛋”,杨荫榆与后台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是“高墙”,在鸡蛋与高墙之间,《语丝》毫不犹豫地站在“鸡蛋”一边,他们讨厌陈源这些现代评论派名为公允,实际在为“高墙”帮腔,成为军阀与官僚的帮闲,因此鲁迅讽刺陈源这些绅士是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语丝派将陈源、章士钊和段祺瑞视为一伙人,《现代评论》就是一张“白话老虎报”(老虎暗喻章士钊),周作人颇为鄙夷地说:我与陈源个人始终没有嫌怨,但“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
学历出身的差异、活动场域的不同以及与国家体制关系的区别,这三点构成了语丝派文人与现代评论派学者的彼此对立,但这些还仅仅是外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在的“文化惯习”迥然有异。
二 绅士与名士:“文化惯习”的对立
如前所述,民国以后,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体制演变为现代的学术知识体制,但是在体制内外或体制的中心与边缘,不同的场域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惯习”:新绅士与新名士。新绅士处在正统儒学的官僚士大夫延长线上,到民国以后与西洋的理性主义相融合,演化为体制内学者共同体的文明修养;而新名士继承了庄子、魏晋名士和阳明学的传统,到民国以后与西方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体制外文人共同体的精神气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种“文化惯习”暂时纠缠在一起,没有分化,但到了《语丝》和《现代评论》阶段,二者便分道扬镳,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绅士与名士在“文化惯习”的对立,首先体现在信念立场上,是公理与文明优先,还是个人的真实优先?按照葛兰西的观点,现代评论派属于19世纪的“传统知识人”,在上帝死了之后,知识人因为掌握了理性,因此拥有上帝一样的权力,代表了普遍的正义,也代表了人类的普世文明,他们必须摆脱个人的好恶,更要超越党派的偏见,以公理的化身和文明的名义发言。陈源在《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总结了刊物的宗旨,自认“在中国的评论界里开一新例”。他批评中国人只有党同伐异,缺乏是非善恶:“在他们看来,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对的,凡是仇敌,什么都是错的。”但本刊同人是“本科学的精神,以事实为根据的讨论是非”,而且“是所有的批评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谩骂。这也许是‘绅士的臭架子’”。
陈源以绅士自称,他所说的“臭架子”,乃是一套文明的礼仪,其背后的支撑点,一是理性,二是公理。然而,在语丝派文人看来,所谓“绅士”,无异是现代的道学家,其核心就是“伪”。鲁迅嘲笑说:“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一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在鲁迅看来,不要以“公理”“公正”“中道”这样的大词掩掩饰饰,这些都不过是道学先生的虚伪,有什么话直说便是:“假使一个人还是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在论战的白热化阶段,鲁迅对戴着“正人君子”面具的现代评论派下了狠笔:“我又知道人们怎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
一方是掌握了公理与文明的正人君子,另一方是自然率性的真名士,从历史延长线来看,这场争论是明末的耿定向与李卓吾争论的2.0版。耿定向是理学大师,在意的是“重名教”,而李卓吾是狂禅,重视的是“识真机”。名教来自于公认的天命、天理,而真机则来自于个人的一得之见。这也是理学的天理说与心学的良知说的差别所在。传统的天理到了近代以后转变为普遍的公理,从英美回来的学者专家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科学与文明,它代替了天理成为了终极的价值标准,一切言论与行动皆应以此为准则,因此他们要超越私见和门户之见,在舆论场上主持公论,陈源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之后,便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但在语丝派文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新名教和伪道学。林语堂平生最讨厌名教与道学,因此他才会背弃海归而投身《语丝》,他说:“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显然,在林语堂看来,所谓“公论”,恰恰是一种垄断性、宰制性的话语霸权,属于“别人让你说的话”,真理不在于“公”,而在于“私”,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都有一己之真理,愈是“私见”与“私论”,愈能接近真理本身,因为真理是在众多的“私见”的交往和竞争之中呈现出来的。
最让语丝派文人鄙视的,是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的伪道学,是他们的伪饰,缺乏真的生命和真的“私见”。鲁迅颇为刻毒地批评说:“只要不再串戏,不要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文明本身就是面具,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方能合乎礼仪地交往,道学提供的是绝对的价值,而名教则是教人如何做人与交往。但从魏晋名士到明末的李卓吾,再到语丝派文人,最厌恶的正是所谓的公理与文明,他们认为公理就是假道学,文明即是正人君子的伪善的面具,他们要的只是真:真话、真人与真性情,真的就是好的,甚至是善、是美,真之上,没有更高的价值。然而,在正人君子看来,真并非最高的价值,真性情之上,还有普遍的善与普遍的文明,公共的善与文明必须规范个人之真。
语丝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很有一点究竟“做真小人还是伪君子”的意味。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