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天色昏暗,后来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窗边目睹了毕生仅见之景:一道闪电上天入地,整个穹庐如同一个巨大的灰釉陶罐自颈至底裂开了一条转折生硬的大口子。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静坐读书。我读的书是《四个短途旅行》,读的遍数是第三遍。白鹤林的作品犹如一座幽深的迷宫,我没有带上线团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了进去,最后几陷自己于进退维谷之境。我得老实地承认,与其他几位我已经论及的诗人相比,白鹤林的大多数作品并不好懂,因而他带给了我更多的考验。我一直没有找到那漏出光线的地方,没有找到刀的刃口。例如,《秋天的荆丛》,全诗仅一百四十六个字,然而包含了众多的指称:“鸟群”、“一个人”、“我”、“你”、“谁”、“涉过季节之河的人”、“燕子”、“我的情人”。我隐约从全诗第三行窥见了“我”与“鸟”的某种互相置换的关系:“我敛翅栖在黄昏的内部”;又自以为是地将第六行的“燕子,我的情人”确定为复指关系;除此之外,我对其它指称之间种种相距、相切、相交的秘密不甚了了。这首诗似乎是一首思乡之作,然而对这一主题的游离又十分严重。白鹤林的言此意彼是出于一种技术上的考虑,还是信笔所致的结果?或者,所谓的言此意彼本身就是我一厢情愿的理解,一个错觉?另一首诗《旧报纸》,“对于整个城市 或者一群喧泄的鸟/旧报纸意味着手的混乱//对于一个房间 一个独居者的词语/或者一个房间的一面灰白的墙/一个时代的某种虚构//旧报纸意味着盲目和丧失”,六行诗后面那巨大的矿藏若隐若现:我刚发现了金子可疑的光芒,马上又为依稀嗅到了铜的气息而改变了主意。文本对我的服从和抗拒随着我的深入阅读而永不停止。这对于受众而言,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折磨,还是一种无穷无尽的享受呢?至于三行诗《古代》,“一个英国女子/硕大的帽子上的/一簇红玫瑰”,则仅仅提供了一个借代物,或者说一个隐喻体,你只能由此出发,靠自己的双脚漫游古代。白鹤林诗歌文本的另一层甲胄来自于对歧义句的使用。我曾经对他的一行诗“远离贫穷的孩子和书本”(《放蜂的人》)做过严谨的语法分析,结果发现了三种语义向度。这是一笔糊涂帐,还是无意中借助于汉语语法先天存在的某种不规范性而衍生出的附加值?杰出的学者叶维廉先生曾举“云山”的种种英译clouded mountain、cloud like mountain和mountains in the clouds为例,揭示顾此失彼、左支右绌的英译者们在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语义流失现象,心情是颇为遗憾的(《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那么,他对于白鹤林这种截然相反的做法肯定要表示推许了。但是我仍然心存疑惑。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凡我三次诵读但仍然不得其门而入的诗绝对不是好诗,直到我用一个闷热的办公室的下午,细致地比较了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回忆》和白鹤林的《梦(或吃桔子的人)》,我的观点才有所改变。这是两件关于时间和速度的作品,都采用了将一幅又一幅的图片依次变黄的办法,让最后的归宿慢慢来临。钟表匠人“拨慢了上海钻石表的节奏”,但是不能减缓一个小女生梳羊角辫的童年的散开、背影从巷口的的消失、脸庞的憔悴与衰老和因加速生活而死于透支。吃桔子的人坐在很旧的沙发上回放了自己的一生:走在回家的路上与一根玩木相撞、每一个未来的黎明都会消耗一个成年男子过剩的体力、秋天的空地正对着天空如他逐渐仰起的脸开始衰老、他闻到自己腐烂的气息来自于干净的尘埃。两首诗的相似之处还在于结尾处对某种气味的涉及和孩子的再次出现,当然还有克制、讲究和向内收紧的叙述方式。所不同者,西渡更注重场景的更迭,而白鹤林在沉郁氛围的整体营造上则较为在意。但他们都给我带来了惊怵和感动,因为我童年时代坐在老家的木头门旁经常承受的恐惧在他们的诗中得到了延伸,而我一位兄长最近的病与死则又一次历历在目。另一方面,这两首诗相互碰撞后外壳的破碎和内核的呈现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和满足,就像我所喜欢的散文家洁尘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绝大多数人都亲近浆果的艳丽和随和,也就尽力使自己成为一枚上等的浆果,硕大、悦目、可口。而一颗好坚果是让人费劲的,它的美味来之不易”。艰难的阅读,用牙齿撕咬式的阅读,并不全是疲惫和枯燥的,只要在最后豁然开朗,伴随着这种阅读的,还有一种智力上的成就感。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在坚果的内部继续跋涉吧,并且耐心地做好置身其中的温度、声响、色彩和形状的点滴记录。
白鹤林是一个看重“怎么写”甚于“写什么”的诗人,“诗歌是一项古老而永恒的民间技艺,它需要的不是推广、普及和热门,而是一部份人(甚至是极少数人)的细致、精湛和持久的工作”(《享受诗歌》),这种表述与“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之类观点大同小异。白鹤林正是这样一个精益求精的手工艺人。上文中我已提及,他的《梦(或吃桔子的人)》深受西渡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体现为西渡一路学院派风格:精雕细刻的语言,克制、内敛的情感,策略化的叙述,缓慢有力的速度,意象洁癖,人文主义气质,在某些大师面前的谦恭态度甚于对个人创造力的信任,诸如此类。白鹤林曾写有两件作品,《玫瑰的言词》和《旷野》,分别献给博尔赫斯和叶芝。假如翻开西川、王家新、孙文波等人的诗集,我们会发现这类作品屡见不鲜。我还发现白鹤林对一些经典的诗意有过化用,“另外一个孩子弯腰捡起一块硬币”(《布林的天桥》)、“我遇见自己独自穿过一座昏暗的森林”、“我准备写下全部的诗篇/直到年老发白的你在炉旁睡去/翻开的书页合拢 灰烬中的光熄灭”(《献给赛•西的十四行》),从中不难看到顾城、但丁和叶芝的影子。这些影子在白鹤林的扶掖之下,已快站立起来了。另一首诗《是我的》,通篇采用“帽子是我的 头发不是我的”这种悖谬句式,为塞萨尔•巴列霍《相信眼镜,不相信眼睛》一诗增添了汉语版。此外,白鹤林还坦陈他诗中的梦幻色彩与狄金森大有干系。而长句的使用,例如《四个短途旅行》,则来自于雨田。《让花朵回归无尽的黑暗》、《这些人》、《在寒风中跑》、《可耻的》等诗对节奏和瀑布式排比句群的迷恋,则有可能与青年诗人范倍有关。有迹象显示,陈东东和米兰•昆德拉也是白鹤林所喜爱的。一切都有迹可寻。白鹤林似乎与当代最为标准的学院派诗人的口味和胃口并无二致,包括他对意体十四行诗写作的短暂兴趣。学院派诗人被口语写作者们称为知识份子诗人,在世纪末曾一度成为刻板、僵硬和奴媚的代名词。问题恰好出在这里。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白鹤林的写作中,同时包含有一些为学院派诗人们所轻视而为口语写作者们津津乐道的因素:回到语言基层,关注形而下。我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作品为证:《阳光里的孩子》、《信用卡》、《在至兰州的列车上》、《文庙街》、《阿凡提》、《爱情小说》、《<登幽州台歌>藏头版》、《赤城湖》、《新“雨巷”》、《大观园》。我认为,《大观园》一诗渗透着一种金斯伯格式的反学院气息,“这是老百姓的大观园 人民的大观园/这是赵大的大观园钱二的大观园孙三和李四的大观园/这是弹力丝袜 油炸里脊 悄建胸 飞利浦 步步高的大观园/这里步行街商业街下岗夜市一条街/这是一楼当街装修了的音像店和厕所/我掏出了五毛钱就赶上了没有味道的文明/我花了五元钱就打捞起沉没已久的《铁达尼号》/席琳•狄翁的歌声真像是从大海里冒出来的一般/夹带着一个世纪泥沙俱下的混响和回音”。有意思的是,金斯伯格被中国当代众多的口语写作者例如伊沙、唐欣奉为诗歌教父。白鹤林的另一首诗《新“雨巷”》也值得追踪调查,“想象 你一定要想象/我带着很多油纸伞 台湾或江浙货/无业或刚辞职下岗/走在一条新城市的雨巷/希望碰到几位/没有带伞 但带了钱的姑娘”,用贫困者沿街卖伞的现实力量粉碎了戴望舒经典之作中的浪漫情调,就像伊沙的《法拉奇如是说》之于意大利已故记者法拉奇的某段名言、马非的《寻隐者不遇》之于贾岛的一首五绝、宋小贤的《主席与总统》之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沈浩波的《一个人老了》之于西川的同题诗。白鹤林曾坦言他的这类作品写得轻松、舒畅、过瘾。看得出来,这种“无遮拦”的写作方式对他那种字斟句酌、苦心经营的做法构成了一种解放,就像一个平素严守纪律的学生尽情享受某个家长不在家的星期天。综上所述,白鹤林乃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多妻主义者,他不断地尝试着各种技艺,喜新厌旧,寻欢作乐。他这种“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 戏为六绝句》其六)的艺术精神对世纪末诗坛大论争的双方都构成了一种冷讽。当然,白鹤林风格的并时性摇摆而非历时性嬗递说明他还处于一个学习或者说整合阶段,犹如一个旅行者,要把万水千山踏遍。但我希望他的“短途旅行”尽快结束,早日达到他在《写作的空白》一诗中所向往的境界:“直到最后 我从年轻的学徒成为经验本身/了解自己思与想里的每一次障碍和事故/把一支破旧的笔置诸脑后/单凭心灵/听出词语下面微小的颤动和运行”。
至于白鹤林“写什么”的问题,我仅作简要说明,首先得引用他的夫子自道,“童年记忆中悲剧式的残缺与呈现,恰恰给了我最原始的幻想和创造力,给我以奇特的引诱和折磨”(《灵魂的碎片》),“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现实人,同时也作为一个生活在诗歌边缘的说梦人,多年来我的语言和目光仍然穿越着现实的‘白光’,回到生命最初的境地──一种非宗教意义上的前方。这或许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诗歌的中心和方向:梦境”(《三堆:上升的梦境》)。不错,正是童年记忆和梦境构成了白鹤林诗歌之河的源与流。认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明白白鹤林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写到鸟,而且总是将鸟与自己合二为一,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写到河流,而且总是矢志不渝地向源头而非彼岸行进。白鹤林《与一条河流相遇》非常具有代表性,与他的很多作品可谓血肉相连,“很多次 我顺河而上想找回一只鞋子/因为已经没有人懂得与河交谈/一只孤独的白鹤在水面进退两难”。鸟和河与白鹤林的童年和梦境密不可分,也与他的故乡密不可分。“白鹤林”,也许是“白鹤岭”,正是他故乡的一个地名。白鹤林犹如一个一直在那林中或岭上逗留歌唱的精灵。城市对于他而言,是干涸而又荒芜的,“在城市街角的下水道口/我是一条腐烂的鱼”(《鱼是怎样逐渐消失的》)。
白鹤林未足而立之年,他还没有亮出致命的锋刃。但是古龙所谓“七种武器”他已掌握四种:霸王枪、碧玉刀、孔雀翎和离别钩,──我是指他的信心、勇气、诚意和敢于割弃的艺术精神。这些水和粮食,会伴随白鹤林完成令人惊羡的远足和长征。对此,我确信不疑。
白鹤林曾说,面对博尔赫斯,如果我们没能洗尽头脑中的尘埃,就会在那些绝美的诗篇上留下旅行者盲目而无知的痕迹。面对白鹤林我不知道是否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我所能担保的,就是我所写下的都出自内心而且自以为是。如果确有一些瞎话,那绝对不是我睁着眼说的。
二〇〇二年七月改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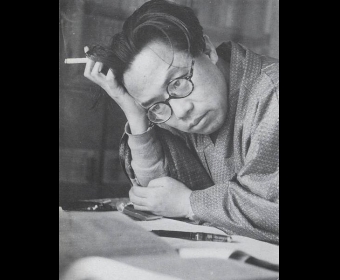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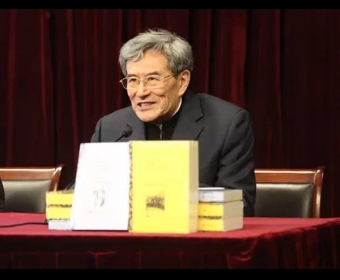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