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华
《活着》
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而非别人的看法
一九九二年初的时候,我在北京十平方米左右的家里睡午觉醒来,脑子里出现了“活着”这两个字,觉得这是一部我一直想写的小说的题目。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题目,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我想写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关系,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愿望,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写,直到《活着》这个题目出来以后,我开始写了。
……
我开始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叙述的,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写福贵的一生, 语言也是《在细雨中呼喊》语言风格的延续,结果写不下去,写了一万多字之后就感觉不对。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经验了,知道自己感觉不对的话肯定是出问题了,虽然是什么问题并不知道。后来尝试用第一人称来写,让福贵自己来讲述,很顺利写完了。
小说里的福贵是一个农民,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念过三年私塾,毕竟是地主的儿子。但是三年的私塾是不够的, 可以说他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所以他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应该是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不可能用大学教授的语言来讲述。我一直在寻找最简单的语言,刚开始比较谨慎,不确定这样的语言行不行,慢慢地找到叙述语调以后,就很顺利了,一切都顺利了,就知道他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述。
我一直以为《活着》是很容易翻译的,因为它的叙述语言是最简单的中文,后来我的日文译者饭塚容教授告诉我,《活着》很难翻译,他说《活着》的语言确实简单,可是很有味道,要把这样的味道翻译出来很难。
我在写《活着》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用简单的语言叙述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这部小说的语言越出了我此前熟练掌握的语言系统,时常会因为一句简单的话耽搁几天,因为找不到准确的表述语言。
举个例子, 有庆死后的那个段落,福贵把有庆背回家,埋在屋后的树下后,站起来看到月光下的那条小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写下那条小路在那一刻给了福贵什么感受。小说前面几次写有庆跑步去县城,有庆要割羊草, 经常要迟到了才急忙往学校的方向跑, 把鞋跑坏了, 福贵骂他, 说你这个鞋是吃的还是穿的。后来有庆每次跑向学校的时候就把鞋脱下来拿在手上, 赤脚跑到学校去, 由于他每天都要跑着去学校, 后来在学校举行的长跑比赛里拿了冠军。因为前面有这样的描写, 而且福贵又一次次看着他这样跑去,所以当福贵把孩子埋在树下,再站起来看到那条月光下的小路的时候,是不能不写福贵的感受的,必须要写,这是不能回避的。
可怎么写呢?我记得自己以前用各种方式描写过月光下的小路, 有些是纯粹的景物描写, 有些是抒情的描写, 也用过偷梁换柱的比喻, 比如我曾经这样描写过月光下的道路, 说它像是一条苍白的河流。但是这次不一样, 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 刚刚埋下, 极其悲痛, 他看着那条月光下的小路, 我知道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多了没有意义。
那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写一句到两句话把福贵悲痛的情绪表达出来就够了, 好比是格斗里的最后一刀, 如果写一千个字, 那就是对格斗的铺垫了, 不是最后一刀。福贵是一个农民, 他对那条小路的感受应该是一个农民的感受,我写不下去,耽搁了几天, 找到了“ 盐” 的意象, 盐对农民来说是很熟悉的, 然后我写福贵看到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路, 月光照在路上, 像是撒满了盐。想想那是怎样的一条月光下的小路, 撒满了盐,这个意象表达的是悲痛在无尽地延伸, 因为盐和伤口的关系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到的, 所以当一个作家用朴素的语言写作时, 其实比用花哨复杂的语言更困难, 因为前者没有地方可以掩饰,后者随处可以掩饰。
……
这部小说发表好几年以后,我有时会想,当时怎么就把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了?可能就是一条路走不通了, 换另一条路。我曾经觉得这只是写作技巧的调整, 后来意识到其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调整。像福贵这样的一生,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除了苦难就没有别的了, 但是让福贵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苦难的生活里充满了欢乐, 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 他们的家庭曾经是那么的美好,虽然一个个先他而去。《活着》告诉我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节选自《纵论人生,纵论自我》
《许三观卖血记》
一部通篇用对话完成的长篇小说
我年轻时读过詹姆斯· 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通篇用对话完成的一部小说, 当时就有一个愿望, 将来要是有机会, 我也要写一部通篇用对话完成的长篇小说, 用对话来完成一个短篇小说不算困难, 但是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就不容易了, 如果能够做到,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 对不同风格的小说都有兴趣, 都想去尝试一下, 有的当时就尝试了, 有的作为一个愿望留在心里, 将来有机会时再去尝试, 这是我年轻时的抱负。
一九九五年我开始写《许三观卖血记》, 写了一万多字后,突然发现这个小说开头是由对话组成的,机会来了, 我可以用对话的方式来完成这部小说了, 当然中间会有一些叙述的部分, 我可以很简洁很短地去处理。写作《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 我意识到通篇对话的长篇小说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这是当年我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困难, 詹姆斯· 乔伊斯的困难。
当一部长篇小说是以对话来完成时, 这样的对话和其他以叙述为主的小说的对话是不一样的, 区别在于这样的对话有双重功能, 一个是人物在发言, 另一个是叙述在推进。所以写对话的时候一定要有叙述中的节奏感和旋律感, 如何让对话部分和叙述部分融为一体, 简单地说就是如何让对话成为叙述,又让叙述成为对话。
我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过六年, 我对我们地方的越剧比较了解, 我注意到越剧里面的唱词和台词差别不大, 台词是往唱词那边靠的, 唱词是往台词那边靠的, 这样观众不会觉得别扭, 当说和唱有很大差别时, 很容易破坏戏剧的节奏感和旋律感;当说和唱很接近时,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所以我在写对话时经常会写得长一点, 经常会多加几个字, 让人物说话时呈现出节奏和旋律来, 这样就能保持阅读的流畅感, 一方面是人物的对话,另一方面是叙述在推进。
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 对于写对话我不再担心了。
——节选自《我叙述中的障碍物》
《兄弟》
要感谢日本人的“垃圾西装”
(对一个时代的命名)它也是很难的,《兄弟》里面写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在变化, 但它变化的速度让你感觉到像是小河流水一样, 而九十年代你会发现像列火车,“呜”地就过去了。
所以我在想, 八十年代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他们一个标志性的变化, 这是很重要的, 想来想去后觉得是西装, 因为中国人从穿中山装变成穿西装就是在八十年代, 服装的变化, 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人对生活态度的变化,以及他们思想的变化。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那些做西装的裁缝原来是做中山装的, 尤其在我们小县城, 小青年结婚时开始穿西装了, 做中山装的那些裁缝就改成做西装,做得不是那么好。大量日本的二手西装和韩国的二手西装——我们叫“ 垃圾西装”——涌进中国, 我买过一套, 欧阳江河也穿过。那个西装质量非常好, 跟新的一样, 穿在身上确实非常好。为什么我没有在小说里边写韩国的“ 垃圾西装”, 而写的是日本的?因为韩国的“ 垃圾西装” 胸口没有名字, 日本的“ 垃圾西装” 内的口袋上面都有他的姓, 都绣在上面。
当时我的日本翻译饭塚容来北京, 他穿着西装, 我说让我看看你西装里面的口袋, 他给我看, 上面绣着“饭塚”。如果你决定写西装, 你要有生动的东西来表现, 可以用一种荒诞的, 也可以用一种夸张的, 所以有了这个名字以后, 我能够写的就有很多, 刘镇的男人们穿上日本的“ 垃圾西装” 以后, 得意洋洋, 在街上互相问你是谁家的, 我是松下家的, 是吧?你是本田家的, 丰田家的, 汽车大王什么的。然后刘作家和赵诗人一个是拿了三岛家的, 一个拿了川端家的, 互相还问, 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最近想写的叫“天宁寺”,哦,跟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只差两个字。然后另外一个说你在写什么, 我在写“ 我在美丽的刘镇”,跟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也差两个字。
假如日本的“ 垃圾西装” 没有绣着的姓氏能够让我在小说里发挥的话, 我也不可能去写, 虽然我觉得西装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表现方式, 我还是会放弃。如何去处理小说叙述里的命名不是容易的事,能否以很好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毕竟不是学术论文, 它是小说, 你要用生动的、有意思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因为日本人西装的口袋上绣了一个姓氏——谢谢日本人——才让我能够把这个章节写完。
九十年代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去命名?然后我就回想, 那个时候我看电视换台的时候, 九十年代张旭东已经来美国了, 电视里边全是选美。比如一个内蒙古电视台, 有两个俄罗斯人来参加就是国际选美比赛了, 只要有外国人来就是国际了。斯洛伐克语版《兄弟》的翻译, 他们夫妻俩当年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去昆明旅游, 结果昆明刚好在进行马拉松比赛, 组织方看到两个老外非把他们拉进来,说你们进来以后我们就成国际比赛了。
——节选自《给你一个烟灰缸,然后告诉你禁止吸烟》
《第七天》
创作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支点
小说开始的时候, 一个名叫杨飞的人死了, 他接到殡仪馆的一个电话,说他火化迟到了,杨飞心里有些别扭,心想怎么火化还有迟到这种事?他出门走向殡仪馆,路上发现还没有净身, 又回到家里用水清洗自己破损的身体, 殡仪馆的电话又来催促了, 问他还想不想烧?他说想烧。那个电话说想烧就快点过来。
然后杨飞来到了殡仪馆, 当然路上发生了一些事, 他来到殡仪馆的候烧大厅, 这是死者们等待自己被火化的地方,他从取号机上取下的号是“A64”,上面显示前面等候的有五十四位。候烧大厅分为普通区域和贵宾区域, 贵宾号是 V 字头, 杨飞的 A 字头是普通号, 他坐在拥挤的塑料椅子里,听着身边的死者感叹墓地太贵, 七年涨了十倍, 而且只有二十五年产权, 如果二十五年后子女无钱续费, 他们的骨灰不知道会去何处。他们谈论自己身上的寿衣, 都是一千元左右, 而他们的骨灰盒也就是几百元。
贵宾区域摆着的是沙发, 坐着六个富人, 他们也在谈论自己的墓地, 都在一亩地以上, 坐在普通区域死者的墓地只有一平方米, 一个贵宾死者高声说一平方米的墓地怎么住?这六个贵宾死者坐在那里吹嘘各自豪华的墓地、昂贵奢华的寿衣和骨灰盒,骨灰盒用的木材比黄金还要贵。
我虚构的这个候烧大厅, 灵感的来源一目了然, 就是从候机楼和候车室那里来的。至于进入候烧大厅取号, 然后 A 字头的号坐在塑料椅子区域,V 字头的号坐在有沙发的贵宾区域, 这个灵感来自在中国的银行里办事的经验。中国人口众多, 进入银行先要取号, 存钱少的是普通号, 得坐在塑料椅子里耐心等待, 有很多人排在前面;存钱多的是 VIP 客户, 能进入贵宾室, 里面是沙发, 有茶有咖啡有饮料,排在前面的人不多,很快会轮到。
来自现实生活的支点可以让我在叙述里尽情发挥, 有关候烧大厅的描写, 我数了一下, 在中文版里有十页。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双向作用,一方面无论是现实的写作还是超现实的写作, 是事实的还是变形的, 都应该在现实生活里有着扎实的支点, 如同飞机从地上起飞,飞上万米高空,飞了很久之后还是要回到地上;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给予了文学创作重塑的无限可能, 文学可以让现实生活真实呈现, 也可以变形呈现, 甚至可以脱胎换骨地呈现。当然前提是面对不同题材不同文本所做出的不同塑造和呈现, 这时候叙述分寸的把握十分重要, 对于写实的作品, 最起码应该做到张冠张戴李冠李戴;对于超现实的和荒诞的作品, 做到张冠张戴李冠李戴也是最起码的。
这里我说明一下,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格里高尔· 萨姆沙变成甲虫以后仍然保持着人的情感和思想, 如果将他的情感和思想写成甲虫的情感和思想, 这就是叙述的张冠李戴;他翻身的时候翻不过去, 因为已经是甲虫的身体, 如果他还是人的身体而轻松翻过去,也是叙述的张冠李戴。
——节选自《两个牙医》
来源:长江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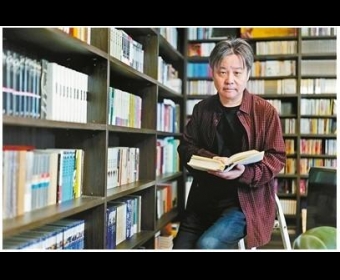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