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的高亢的叫声让人落泪”
王家新
鹅的高亢的叫声让人落泪。
它比我更懂得一个季节,
或许,也是这尘世的孤独。
泉子的这首三行短诗使我很受感动。中国的孩子们从小都会背“鹅鹅鹅,屈项向天歌”,在江南的池塘河汊,人们也可以随时看到这种笨拙而高傲的造物,但是有谁注意到它那“高亢的叫声”并为之落泪呢。
这样的诗让人惊异于一个诗人的“发现”和“揭示”。这不是一般的触物感怀,它体现了一种如布罗茨基所说的“摆脱先验的诗性,使常识得以显现”的能力。进一步讲,它写的是鹅,道出的却是“人心”。这就是它的感人力量之所在。
我本人早就注意到泉子的诗,在他那里有一种“决绝”的东西,使他的诗和那些甜腻、雕琢、俗套的“江南诗歌”有了区别。而在他这部题为《湖山集》的近作中,时间更多地进入到诗中,诗所触及到的东西更为本质,语言透出一种化繁为简的功力,诗的音调也更为直接、亲密和迫切了。
山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湖山集》中的绝大部分篇章,仍不脱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西湖山水的怀抱。但是正因为进入中年,诗人更多了些对时间的触及,在他抓住的那些瞬间中,他一次次真切地道出了某种“物是人非”的惊诧之感(见《中年人》、《惊诧》等诗)。而诗人的“辨认”,也就成了在时间中的更艰辛、更细致的辨认。像以上那首《鹅》,没有对生命和岁月的足够体验,是不可能写出的。
随时间而来的,还有一种对自身创作的更高的要求。诗人笔下的山水,不仅限于现实感触,还被置于一种更深远、更具有意味的时间和空间中,或者说,被置于了千古文脉中,以容纳“千年之间那些曾经的仰望与俯视”(《保俶塔》)。这一切,正如诗人自己在《诗之思》中宣称:“诗必须是一种同情,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一种启示,一种同时向未知与往昔之深处的敞开与发明。”
穿行在这一片山水之间,诗人所做的,正是辨认、敞开和他所说的“成全”——“诗是一次自我完善的契机,是又一次地成全”(《诗之思》)。在经过多年的摸索之后,诗人已有了自己更明确的诗学意识和对自身职责的领悟。他不会满足于一点现实的书写。他要通过这一次次的契机,去“成全”那一片诗的山水,使它重获其神话般的意义。或者说,他要使自己卑微的写作,能够加入到“世世代代的吟咏”之中,从而“有别于此刻嘈杂鼎沸的市声。”(《对话》)
泉子就是这样一个有其精神“向度”的诗人,或者干脆说,一个使徒般的诗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湖山集”和我们常见到的隐逸诗、观光诗、休闲诗都很不一样。他视诗歌为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修行。他寄期望于自我的完善。在一篇短文中诗人称他的山水诗“已无关山水,而是看山水的那个人,那双眼睛在对自我的逼视中,最终能否获得那将之洞穿的力……”而那双在其间浮动的眼睛,是诗人自己的,但又是超越了自己的,它用来“逼视”自我,从事一种生命的审视和辨认。而我们也往往从他的诗中感到了这种“逼视”之力:
你是龌龊的,
你是卑贱的,
你是丑陋的,
你同样是喜悦的,
当你如蝉般脱下自己,
当山水落向大地。
——《山水落向大地》
对自我富有勇气的揭露与一种重生般的喜悦同时到来。诗的最后两句,在生命之蜕变与“山水落向大地”之间,也获得了一种富有张力的澄清。
“语言的本质是一种质询”,法国哲学家埃·列维纳斯曾如是说。诗的本质也如此。如果我们不能获得这种质询的力量,又怎能抵及到事物和自我的内里?
说到底,和人们所想像的“江南才子”不同,泉子是一位“追求真,追求信仰”的诗人,因而他一次次迎向了这种对自我的“逼视”。我认同于他的诗,首先也就在于这种深切的发自生命内里的认知的诉求。
因而泉子笔下的山水不仅是悦人的,虽然它与“世俗”有一种相区别和对应的意味,但它折射出诗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当诗人带着他的“羞耻心”、疼痛感和生命的欢喜奔向这片山水,他从中寻求的,也不单是安慰:“直到你终于理解,山水自有伟大的教诲,/而时间的往复仿佛雀鸟在丛林深处的啼鸣。”(《山水之教诲》)
说到底,泉子的山水是某种“神启的山水”,是一片与灵魂有关的风景。他要努力接近的,也正是古人所说的“山水即道”、“山水即心”的境界。“在一座山的起伏与水光的皱褶间”,他不仅投出了最隐秘的凝视,他也相信,有一种生命正是在这一次次“契机”中生成和认出的。他的诗要全力写出的,正是“生命在这一刻的发生与到来”(《诗之思》)。以下他的这首《雾中划桨》,我读了数遍仍感到惊异:
在雾中划桨的人,他们并没能撕开浓雾。
他们一次次把手臂伸出身体之外。
他们不断地划,不断地划。
他们满载着雾,
他们的身体也是雾做的。
他们的脸是雾,他们的眼睛是雾,
他们的心何曾不是白茫茫的。
他们不断地划,不断地划,
他们一次次将白色的枯骨举过头顶,
又一次次探向水之深处。
诗的节奏艰辛有力而又利落,每一下都“划”得恰到好处,而到了“他们一次次将白色的枯骨举过头顶”,令人惊异的东西出现了。这种对生与死的洞观,使语言获得了一种闪电般的照彻和揭示的力量。我想,这也是一种“成全”:以死亡的白骨来成全生命的不屈,或者说,来显现宇宙中那种万古不灭的“人心”的力量。
还需要看到的是,像同时代很多诗人一样,泉子的写作广泛吸收了东西方的资源,而在近些年来,他则明显受到佛家思想的吸引。好在他并没有以诗来演绎佛理,也从不轻易地言说“解脱”或“四大皆空”。我们会感到,在他的近作中,他依然保持了质疑和追问的力量。他的生命依然充满了疼痛感(这成为他写作的内在依据)。而他追求的,也不会是那些廉价的纯净和不堪一击的完美,而是“必须在剧痛中才得以完整保存的皎洁。”(《在西泠桥》)
这使我对他一意孤行的“偏执”有了信心。更深刻地看,他仍一直保有了他所说的为人的“羞愧感”,这成为他的良知的来源。他甚至这样深信:“每一个人生命深处的羞愧成就了这伟大的尘世。”(《诗之思》)
的确,这是一位已接近于“知天命”的潜行者,谦卑而又坚定。在只有两行的《相信》中,他这样自问自答:
有人问,五百年后的读者,你信吗?
而我相信他们,胜于我自己。
我惊异于他在茫茫时空中这样发问,虽然我知道,一个能这样问和回答的诗人,说明他已形成了某种洞穿古今的视力。他已不再“拘泥于尘世”。他找到了一个永恒的对话者(因而也就有了一个“五百年后的读者”),或者说,他已从当下把握住了某种未来。
2014,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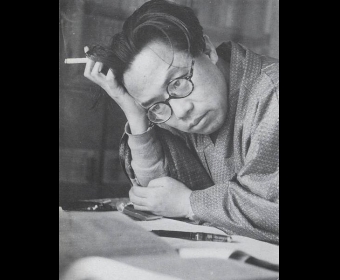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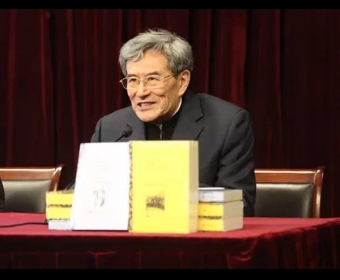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