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浩有些粗糙的、有时是一种容易形成的诗意化语言里,我看到这种非常清晰的,对于不被帮助的乡村基础面的认识,这首诗的意义,和酒鬼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它并不是什么寻求“客观对应物”的努力,它是被伤害的“客观对应物”本身,是对我们的一次打断。
然后,我想提到,具有鲜明的宗教写作诉求的诗人李浩,他的这首长诗,仍然在一个当下的现实时空发生,刚才,我和李浩在门口抽烟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如果按照信仰的角度看,它的时间是现世的时间,不是一种有待救赎和永恒化的时间——我们知道,即使贝克特也抵达了这种时间。提到“时间”,是因为,我想提请大家注意李浩作为有明确宗教意图的诗人,其写作在“时间”中的立足点。奥古斯丁设计了一个“永恒的当下”,排除现实感,而人,被“永恒时间”所排除的堕落的人,通过他禁锢于某个现实时刻的理智所进行的认知,是没有任何终极重要性的,于是这样,特殊事物以及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时间,就被认为不重要而被打发掉了——英国学者波考克称此为“令人难忘,甚至是庄严的谋略”。
我愿意把李浩诗中的时间,理解为一种艾略特在《小吉丁》中所称的“难以确定的时刻”,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共同时刻,在另一行诗中,艾略特称其为“交叉时刻”。
我们都知道,《四个四重奏》的核心,也是《小吉丁》的核心部分,来自但丁。但丁依然是关于“永恒的当下”最重要的诗人。《天堂篇》里的耶路撒冷,平衡了《地狱篇》里的雅典和罗马。这种双重性非常重要,涉及到轴心结构,如果在座各位以及主持人准许,我将在稍后,占用各位大人的时间,向元老院报告有关内容。
最后我想提到语言。因为之前,李浩在一次与我的交流中,非常急切地说他“不关心优异的语言”,因为他想表达的东西的强烈性,更加激励他的激情意志。我能理解他的写作意志的急切。但是,意志不能表达出语言所表达出的东西,这是诗人和意志论者的重要区别。也是茨维塔耶娃在《劳动英雄》这篇辛辣的散文里,通过批评勃留索夫所揭示的东西。对于诗人,意志核心化蕴藏着危险。我们要小心写作的扩张意志是一种蒙昧主义的变体,是现世的蒙昧主义以及我们都不陌生的中国特色蒙昧主义在语言中的变体。或者说,扩张了的意志需要更优异的语言。只有优异的语言才能够不符合惯例和预期,产生与蒙昧的区别,生成为一个美学事实。而不管不顾的“直接”的诗意性可能是一种重复,一种我们所反对的东西在语言中得到延续的表现。
不仅是让基础面说话,而且是让对立面说话,这也是通过优异的语言能够做到的。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宗教诗人,R·S·托马斯让对立面说话的能力,而这正是通过优异的语言做到的。信仰的对象、要求和条件都是并不和蔼的,与之相呼应的自然力——大自然和基础面——也不是一个舒舒服服的梭罗式的田园,它是严酷的,有时让我们不舒服,有时是一种尖刻的对立面,并且随时可能向我们关闭。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询问、专注和诚实,才可以对它稍作敞开。R·S·托马斯通过一系列精确独特的比喻、通过优异的语言,让对立面暂时与我们保持和平关系,和我们谈话。我想,R·S·托马斯的写作艺术也许会对李浩,也对我们的写作实践、对我们与当代基础面对象的关系、乃至对我们的政治学,构成有用的参照。
张杭:我接着王炜说的“优异的语言”这个话题作一个发言。到今天,李浩的诗集《风暴》我也不能说全部看完了,因此就简要讲一下。我们现在总是觉得当代文学还不够好,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从现代到当代,我们的文学还没有成熟,我以为主要是有两个向度的问题。一个是如何找到和表达精神性,另一个让我们始终不满的是,我们的作家似乎很难涉及到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核心矛盾冲突。政治和时代方面的原因我就不详细说了。实际上我们要写作,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从李浩的诗集《风暴》来看,精神性是非常强的。李浩的诗富有精神强度,他的很多短诗里面几乎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意志,甚至可以把它们界定为一种当代中国的荷尔德林式的诗。我想这是在座很多朋友们都公认的,李浩的诗和我们同代人的诗的最大区别。另一点,我们来看他诗歌中现实性的部分,那些比较叙事性的诗作,比如《哀歌》和《还乡》。我在阅读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疑问:李浩在处理这两类诗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种分离的状况。似乎他要写短诗,就是纯精神性的,几乎没有现实生活中那些具体的意象,没有那些我们当下校园诗人、从校园出来的诗人特别沉迷的即时、即景的事物(从现代到当代,在诗人的个性越来越减弱的情况下,一个诗人怎么能够有个性,实际上很多诗人是依靠事物,把属于自己生活的事物写得越具体,就好像越拥有了一种与别人的区分度,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个性)。然而在他的现实性诗作中,我们又看了另一种状况:非常叙事,非常具体,甚至可以说是传统叙事诗中那种非综合性的叙事。实际上我觉得这两点并不是矛盾的,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表面看上去那样是分离的。这两类作品有一个共性:李浩的诗是非常简单的。刚才王炜提到“优异的语言”,而我则想提到“方法”。我认为李浩的诗的简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作缺少方法。
我想简略地提及现代诗歌的方法。我们知道现代诗歌始于波德莱尔,而从波德莱尔发展出象征主义,其后无论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新批评,都跟象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在象征主义开始的这一现代诗歌的进程中。与之相应,我发现,我们85前后这一代诗人,很多人的阅读和写作都是从象征主义开始的。有时,我看同代人的诗歌,会有这样一种区分:这个诗人有没有经历过一种自觉的象征主义训练。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提到这样一个看法?在当下很多关于诗歌的谈论中,我觉得我们过度强调了语言,而在语言背后还有一个结构和方法的问题,却是被忽视的。为什么我要谈到从象征主义开始的这些种种现代诗歌的方法。西方诗人并不是为了现代而现代,为了方法而方法,实际上,他们发展出这些现代诗歌的方法是为了解决现代问题。当我们面临一个浓缩了的现代历程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需要这些方法来处理这些现代问题?当然有些问题是不同的,我们需要新的方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80后、90后诗人,是学了一个现代诗歌的样子,当他们有了更多社会性的经历,会发现他们所学习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潮流的样貌,那时他们也许会用这些方法表达现代生活中的问题。
李浩是非常早熟的诗人,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和面貌,我觉得这没有问题。整本阅读《风暴》,也许你会在一个时段感到,一些诗有同质化的倾向,仔细看,李浩在诗的形式上有过不少尝试,有很多变化。然而大多数的变化,还是停留在语句、诗行、诗节这一层面的。我注意到,李浩非常重视整饬的诗节,然而在他的长诗中,有时会突然出现散文化的情形,不管不顾一大串语句倾泻而下。我感到他在面对这样一个超出日常的问题,比如死亡,有没有办法去处理,有没有一种可以取得与事实本身同等强度的方法?我曾在《我的同代人的诗歌批评》一文中谈到了诗的道德性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处理我们的成长、我们社会中最核心的那些问题,而是一首接一首地写很多即兴的诗,我想也是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难处理的。我们越是面对重要的经验、道德性问题,我们越难以用一般的诗歌方式去完成。比如《哀歌》,虽然极尽表现主义的修辞和描写,然而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情形下,修辞有没有用,能不能承担这个事件的道德重负?我就简单谈到这里。
刘奎:张杭的感受力我很认可,我觉得他的质疑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修辞到底还有没有效果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八十年代末期就被提出了,当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王蒙的一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当文学边缘化以后,当代文学一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文学如何回应现实的问题。文学被边缘化以后,使得文学能够回到文学自身,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同时也有可能使它跟历史离得越来越远;而90年代以来的写作,也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倾向。我平时与诗人来往不多,今天听到王炜、张杭等人的一些批评,他们的一些说法,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此前我没有预料到,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居然有这么大的共性。这就是试图重新激活文学跟历史之间的关联性,我觉得这些思考是非常珍贵的,同时也击中了当下诗歌写作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觉得,文学要回应历史、现实,还是要通过一个文学形式的中介,或者说通过美学的角度,因为毕竟是写诗的,或者说是搞文学创作的。那么,大家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学形式的问题,或者说是美学如何回应现实的问题。
基于这种考量,我就先从审美的角度,对《风暴》稍作解读。问题的出发点是,如果纯粹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对李浩的创作作一个美学的提升,然后,对形式本身也做一些反思。其实,我对李浩诗作有种整体印象,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个自然诗人,如果更精确一些的话,前面可以加个定语,就是“都市里的自然诗人”。李浩这些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无论武汉,还是北京,都是如此。但是,我在《风暴》这本诗集里面,读到的有关都市的东西,非常非常少。他主要处理的是一些自然层面的东西。在古典文学中,自然是常见的主题,但在现代派之后则有所改观,而它对于李浩来说更有一种风格化的意义。它的美学具体性,包括这些方面:首先是自然的时序或时间。他诗作中的时间,大多是前工业化时代的自然时间,而不是现在的机械时间或者说钟表时间,他遵循的是春、夏、秋、冬,这种非常原初的一面,跟传统的农耕文明,有着极深的渊源。他的这本诗集里面,就存在大量诸如黄昏、秋天等,这种非常不确定、不具体的一些时间意象。自然的另一个美学主题是空间。他很少涉及现代的都市生活、工作状态,虽然他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都市,但他诗歌想象的资源,却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时刻,这就是乡土。
我觉得有一首诗,可以作为这种都市-乡村的镜像关系。这就是《天桥下的歌手》这首诗:
天桥下的隧洞里。“城市和人群,
疑问和猜忌,吃人的噪音,
和你的歌声一同,从你的身边
奔涌开来,封堵地下
通道的出口。”你的歌,你的嗓音,
在你的喉咙里,割开你的皮。
你看不到你好像越长越小的楝树,
和树上的苦苓子——闪着光。
你对行人唱,“梭椤树盛开的
蓓蕾。白杨的微光。”你在观众身后,
剥开玉米,细声吞吃髌骨。
你的嘴坚定地朝向摇晃的太阳。
你走近爱人的大房子,挖开多石的山丘,
坟墓,指向 你的额头。
——《天桥下的歌手》
这首诗,开始是城市的一个场景,就是天桥下的流浪歌手,是非常都市化的,而且是很艺术化的,这容易产生诗意的美,与当下青年人的漂泊感、放逐感等是很契合的。但是,就像歌手唱的歌一样——歌词是:“梭椤树盛开的/蓓蕾。白杨的微光”,无论是梭椤树,还是白杨,它们都是一些自然意象;而诗歌的末尾——“你的嘴坚定地朝向摇晃的太阳。/你走近爱人的大房子,挖开多石的山丘,/坟墓,指向 你的额头。”其中,“挖开多石的山丘”这种想象就很有意思,还有“坟墓,指向 你的额头”,也是如此,他最终是走向一种非常自然化的东西。其实,我们在其他诗作中也能读到,像“月光”,以及“土地”、“柳絮”等这一类的,都是非常自然化的意象。
当然,称其为一个自然诗人,并不仅仅在于他所处理的乡土议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诗学谱系,以及文化层面的归属。自然诗人,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海子所处理的乡土经验,李浩与海子这一代诗人是有精神联系的。不过,李浩也有他的独特处,海子诗中所处理的自然,是非常具体的农耕文明;但李浩的处理不同,他把农耕文明抽象化了,他更多的是用了一个“普范式”的自然,是与村庄的整体命运相关的,这可能是因为他是在于都市的对照中来处理的。
他对自然的依赖,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跟年青写作有关系,青年写作的资源往往来自过去的成长经历;第二种可能是与他的宗教信仰背景有关,读他的东西,我很容易想到《雅歌》。《雅歌》的美学风格,大都是借助自然意象,来作带有预言性的书写,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像的。另外,张杭刚才把现代诗歌追溯到象征主义,但从谱系上来看,浪漫主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这方面我们读李浩的诗,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但是我说自然诗人,其实不光是想对他的写作作一个美学的判断,同时我是带着反思性的。这种反思是指什么呢?就是说自然对历史的回应能力在哪里?相对来说,自然其实对历史,尤其是对历史事件,我觉得它回应的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比较重视李浩的《还乡》与《哀歌》这两首诗,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们可能打破了他之前对自然意象,或者自然想象方式的依赖。这两首诗突破了他之前的写作,显示出了他回应历史问题的能力,而且是以诗歌的形式、美学的形式去回应的。T.S.艾略特有句话是,25岁以后的人,如果再缺乏历史意识的话,是比较可悲的。这个历史意识,不仅仅是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基于文学史脉络中的,对于经典影响的焦虑;同时,它也具体地指向现实历史,即时代的问题。我们都从李浩后期的一些诗作中,看到了这种新的可能性,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珍贵的。
苏琦:我的发言是具体从《哀歌——悼工友》和《还乡》这两首诗入手,我为此写过一篇解读文章。李浩最近写的作品,让我对他过去的作品有一个重新的看法。我看了《还乡》与《哀歌》,所以我就必然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去看他过去的作品,这至少能帮助我对他过去的作品做一个理解:李浩想要表达什么?
《哀歌》是他在之前打零工时,遭遇的一个悲剧事件,这是非常精彩的书写。李浩自己也说,从高中时发生了这个事情但酝酿了十年才完成了这个作品。我觉得感情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以后,重新对这件事进行一个反思,的确带着那种力量,那种沉淀。
《还乡》这首长诗,李浩回到了他的乡村经验之中。我对这首诗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它有一个像是但丁的《神曲》那样的结构——分三章,前两章通过“我”给一个鬼带路把乡村记忆,比如说大嫂抢水,乡村村长、支书、文书这些乡村官员,以及一些土豪的腐败行为(涉及收受贿赂、南水北调的拆迁补偿的腐败),还包括一些对李浩个人来说比较痛的地方——计划生育,把这些记忆都勾连出来了,也确实是把中国的一些现实面(如王炜所分析的理解基础面),这三十年以来,或者说49年以来一部分重要的事件,艺术化、内省化、连缀式地勾连出来。第三节,是一个爱情故事,通过追忆一个少女,然后在致幻中完成了与少女情人的“结合”。为什么说它跟但丁的《神曲》结构非常像呢?因为这首诗的第一、第二节,也有一个如同从《地狱》到《炼狱》的引导关系,而第三节诗里的这个引导者变换了,变成了一个贝雅特丽齐式的完美恋人形象。当然,第三节并没有写得那么简单,乡村社会中的复杂,主要是从人性之恶角度切入的……我觉得,李浩通过这样一种带有史诗性的写作,把他对于乡村的一些记忆、情结、情怀和盘托出,别有匠心,具有很好的完成度。
我是看了这个两个作品后感到可以借助《风暴》的出版写一篇批评文章。在《“我深知智慧在我们脚下的经纬上”——读李浩诗集<风暴>》一文中,我将诗集《风暴》打散成两个部分进行分析(李浩自己将《风暴》分成三辑,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李浩是从2005年正式接触天主教,在2008年之后,对于天主的信仰成为他生命和写作中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这本诗集是他正式接触天主教后的第一本诗集——充满了上帝的“光照”,但是我还是准备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突出他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另一部分他直接面对上帝,如赞美诗、祈祷诗。
通过这种分析,我大体把握住了他在两个方向上的努力。一方面是乡村经验或乡村记忆、城市生活经验等现实层面的关切,这些材质透视出他个人乃至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困境,指向生存环境恶化的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是自身的精神救赎,如何在被给定的残缺的生活中活得更加完善、更加尊严、更具有神性(一方面是自身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恰好是一种我们这片土地上长久阙如的事物)。我改用了诗人杨炼先生的一句诗来总结李浩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一座向上和向下同时开建的塔。我这样龙骨般地把握李浩的诗写当然显得有些简单化,即不那么细致,就像是一张草图,还没有涂上油料。对于他的文本细读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限于我的能力和时间关系,只能如此。李浩说他的写作来源是生活、传统、神话,而我只是结合他的文本指出这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这几个方面究竟如何转化成他的作品本身。对于批评来说,那是一项细致的爬梳工作(难免“误读”),但我更建议有心的读者直接去阅读他的诗歌:因为作品本身已完全显示诗之为诗的东西。
我需要再补充几句,我写过一篇关于现实感和历史感的文章,对它们做了一些分析,这是当时陈家坪在倡议搞一个个人诗学的交流活动,我是响应这个倡议而写的,带着自己偏狭的,或者说很基础性的理解。这篇文章受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很深的启发。我在读李浩的诗歌时,一方面我能看到,他的诗歌,在我的那篇个人诗学的文章中能够得到一部分解释,基础面还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我也遇到了相对比较陌生的一部分,信仰经验在他的诗歌语言中建立的灵界空间、精神区域,这是我比较陌生的。而这陌生化的东西对我自身也是一种补充和完善。关于《哀歌》这首,其实这并不是描绘,这是情感喷薄出来的。我觉得不管他写基督教信仰的诗也好,还是写其他的诗也好。他的语言跟他的心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把他的语言也靠近他的形式。我读出的是生命与死者的对话关系。一种静观,很神圣。
秦晓宇:刚才大家所谈的李浩的那两首长诗《哀歌》、《还乡》,这应该是在有宗教背景的诗人那里,比较喜欢去处理的诗歌题材。西方有哀歌传统,哀歌跟悼亡诗有点区别,它处理的其实是重大现实问题与精神命题的悲剧,而不是像悼亡诗那样去书写一个人的死亡。而李浩扎扎实实地写了一个工友死于惨烈的工伤事故,似乎更像一首悼亡诗。但是确实在这首诗当中,渗透着某种富于宗教感的怜悯,尤其最后还出现了一个“父”的形象。张杭刚才谈到如何对灾难进行修辞的问题。我理解,真正的苦难有个不可言说的核心,但诗歌仍有责任对其进行言说,诗歌这一微妙的言说艺术也可以赋予苦难一种尊严,这就是抱怨、诉苦、呻吟与一首出色的哀歌或悼亡诗之间的区别。
张杭:我不是说他处理的内容,而是指方法问题,指简单的叙事。
秦晓宇:再有,李浩在《还乡》里面给出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家园,这还不是荷尔德林式的还乡,后者那个家园本身其实是非常甜美的,还带有乌托邦意味,能够带给你最深刻的慰藉。
我们读到的一些还乡诗,情感上一般都是比较单纯的,还乡就是慰藉,心灵终于得到了安顿,整个生涯都在回乡那一刻得到了和解。但是李浩这首诗没有,这首诗的紧张感其实一直保持到最后。哪怕是真正到达了地理意义上的家乡之后,作者心灵最深处涌上来的情感,恰恰是无乡之感,就是身在故乡仍然在漂泊。
《还乡》与《哀歌》,这里面有着非常充沛的个人经验,他不再是一种在书斋里,从书本到文本这样一个路径——我称为泛象牙塔写作,李浩的诗里有当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那首《哀歌》。我最近看了大量工人写的诗歌作品,许多工人诗人把自己宝贵的生活经验题材化了,结果就是你会觉得许多作品特别雷同。但是李浩的《哀歌》不太一样。这首诗,应当说在我看到的涉及工伤、死亡的这类诗中,几乎是最优秀的一首。这里有伦理问题,甚至修辞伦理问题,李浩把握得都比较好,而且这个事件中的复杂性也表现出来了。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归功于他没有贸然动笔,而是经过了大概10年的酝酿。而且在这首死亡之诗中,我恰恰看到一种元气淋漓的生命的力量。
总之我觉得,像李浩,他既有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既趋向于圣徒人格,又有着一种偏激的性格。就是说,他基本上不走寻常路,一开始在工地上打工,上大学又主动辍学,后来又组织一些人在汶川地震期间去救援等等。和一些文学青年的生活不太一样。基于现实的诗学极为重要,否则大家谈来谈去,其实就是一个诗意的问题,就是如何写的问题,这其实是把诗歌的问题谈小了。
刘奎:写底层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底层如何发声的问题,其实大家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底层的人,他们有生存的经验,但不一定有写作的能力。
秦晓宇:刚才王炜提到过“弱者的武器”。底层的发声,非常重要。底层能否以及如何发声的命题事关社会正义与历史真相。但这发声何其艰难?他们总是处于沉默的境地,仅仅在一些极端的时刻,才不得已用暴烈的形式表达其主体意志、遭遇和情感。因此,如工人诗人的创作意义重大,哪怕仅仅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也是在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在这里,诗歌古老的见证功能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总的来说,社会愈来愈重视底层的发声。媒体会去采访他们,倾听他们的讲述,征求他们的意见,却是针对具体的事件、政策、议题;学者会去做田野调查、口述史的收集整理,也都是带着特定的课题。诸如此类的“发声”当然很有价值,却是被动的、被编辑过的;非但如此,这些“发声”还都是直白即兴的口语,这种大白话是一种毫无表达难度的表达,往往把生活世界和心灵深处那些勾连错综、难言之隐、暧昧幽微、莫可名状的东西省略了,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于是被大大简化,像这样的“发声”有时未必不是一种遮蔽。像工人诗人自觉运用微妙的诗歌语言,去含纳深闳纤细的记忆与经验,感受与愿景,无疑更具有现实揭示力、精神深度与思想启示价值。
刘奎:我觉得你所强调的这种历史的现实感,或者说真实性,对于诗人的写作很重要。但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知识分子面对底层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无能为力,或者说没有资格发言的,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很多事可以做,只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要说是为他们,或代他们立言,而是在关注他们的同时,要保持自己(诗人)的自觉,要带有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意识。
秦晓宇: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其实也带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你的优越感也只不过是知识的优越感。但是你说到经验的时候,其实你还不如他们。
刘奎:这当然不是说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而是说知识分子在面对底层问题时,也是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思考,而这种思考也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对自己的身份有所自觉,尤其是在处理底层问题时,一定要避免把它题材化、消费化。
陈家坪(主持人):大家的发言和讨论非常深入,对话题本身又有所拓展,很精彩。下面有请江汀、万冲和陈迟恩发言!
江汀:首先感谢家坪兄,邀请我们齐聚在他自己家中,为李浩的诗集提供了这样一个轻松、热烈的讨论氛围。我想起柏拉图的《会饮篇》,一群友人聚集在一起谈论文学,这种情境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是某种永恒之梦,“血样从一只玻璃杯倒进另一只”。
我会接着张杭没有讲完的一个问题来谈,就是他说到李浩诗歌中的修辞问题,在某种难以承受巨大的经验之下,修辞是否还能行之有效?在这里,我遇到一个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写作者的创作状态,尼采曾用“日神与酒神”的二分法来描述它们。在此我提及一下自己的创作状态,写作时,我会处于“酒神”状态,词语会不由自主地从天上落在自己身边,然后我再来做拣选。我不知道李浩写作时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要写小说,我会进入“日神”状态。或者说,进入刚才大家在讨论的那种公共性话题的时候,你需要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主题,你需要精确的逻辑。
大家都在谈李浩诗歌的公共性,但是我要提醒大家,首先要注意李浩是一位谣曲写作者。看这本诗集里面,百分之七十的内容里,他都是作为一个歌手在行使抒情。……即便李浩不以这种方式呈现的话,他也会以那种形式,来显露他的抒情灵魂。修辞或此或彼,但他的本质始终是稳固的,我们不难找到它。
前面的讨论中,大家重点谈论他的乡村经验。但他首先是一个城市里的居民和写作者,这是他现在的处境和坐标。童年和乡村经验已经封存在他的经验里面,现在它们被挖掘出来。
他诗中的一些意象,让我想起荷兰画家博斯,他的画布上充满丰富、奇异的众多意象。
在他另一些诗中,文字非常宁静,内蕴则充满动荡,可称之为宁静的讽喻。
张杭说李浩的不同作品中有同质性的东西,这一点也是显见的,我们难免会重复自我。我自己也在注意这个问题,在一个写作者形象的最终确定之过程中,“自我重复”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刚才听完王炜兄的发言后,我对他提到的“什么是中国人”非常感兴趣。李浩的诗歌是一个样本;而不光是李浩,我们所有人的文本,都可以被这样一个终极的问题所容纳。
万冲: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李浩《风暴》中经验时间和写作时间的关系。第一辑《引入记忆》,里面大部分诗歌是写他过去的经历,写作时间和经验发生时间的距离比较长。第二辑《你和我》,主要写他的一些宗教体验,依据我的认知和体验来看,宗教体验更多是即兴和瞬间,李浩将这种宗教体验表达出来,其写作时间和经验发生时间的距离是非常相近的。
李浩在《风暴》的序言《个人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唯独真实的行动和言语能辨别作为物存在的痕迹”。李浩对词与物的关系,真实存在等有独到的体悟。不管是处理过去的经验还是处理当下的经验,他的诗歌中词与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他语言的力度是非常强大的,能够直接召唤出物。这种优异的诗歌语言力度在当代诗歌中并不多见!
陈迟恩:我发言,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浩。因为第一次听到这首《哀歌》的时候,是他在今年的北大未名诗歌节上的朗诵。当时,他朗读的时候,他的情感是特别充沛、有力,给我的感觉是他亲历了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通过情感的积压,他写出了这么一首诗。他朗读的时候,这种感情是自然而然地带出来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年前,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经过了十年的洗涤、经验的处理。十年之后,他重新把它拿出来写,这十年是他写过,还是说不停地修改过?
李浩:在写《哀歌》的时候,这首诗中的事件,在我的大脑里,与我的生命共同经历的这段漫长旅程,它好像是活在我生命里的一个黑洞。在这十一年里,我经常梦见这个故事的始发现场,有时候我经常在梦里看见我的被子上沾满了死者的血——那个死在工地上的工友,他的血在我的梦里,从工地的钢筋头上一直流到我的被子上。
二零一三年,我回到河南工作,那种工地里的气息又回来了。河南郑州空气中的那种气味,那里的人说话的声音与腔调,那些人对待弱者的思维,待人接物的方式,一下子把我抓住了:将二零零二年夏天的那个悲惨事件,从我的身体里、记忆里、情感里、经验里、血液里召唤出来了。那时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我记得我当时在椅子上,好像被椅子捆绑住了一样无法动弹;我感受着房间里的阴暗光线刺穿肉身,而被一点点地悬空起来,我一直抽烟,不敢动笔。
当我胆战心惊地把第一个句子写下之后,我只记得我从垃圾桶里翻出的纸上哗啦啦的声音,过不久这首诗便一气呵成了。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存留在我身体里十一年了,如同身体里的一个肿瘤一样,时时刻刻都在你身上搅动着你。写完之后,我就将这首诗,输入电脑,放在那里,也不敢看。过了两天,我打开电脑读时,我非常后悔和心痛,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写出我想象中的那个诗的样子,我心里很纠结,我更没有想着去修改,因为那种状态中的写作跟复活一样,是不可以改动的。
刘奎:我再补充一点,我刚才说李浩是个自然诗人,前面是加了一个定语的,是都市里的自然诗人。其实,都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发明的过程,如果你在乡村的话,你很难来审视这个乡村,你很难写作;而到了都市之后,住在都市的公寓里面,在都市的书斋里面,你才能召唤出一个乡村的图景出来。然后你才能将过去的经验挖掘出来,我觉得乡村对都市本身的呈现,起着很大的作用,也是一个很必要的经历。联系到李浩的一些生活经历,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他在武汉的时候是住在风光村,这个地方就是城中村,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地方。它在城市之中,但是,它又是一个独立的小村子,那里面五脏俱全,什么都有,是一个较为自足的社区形态。我觉得这个都市的形态,让他不仅召唤了乡土经验,同时它可能保存、并且丰富他的乡村经验。都市与乡村的这种复杂面向,也是需要带进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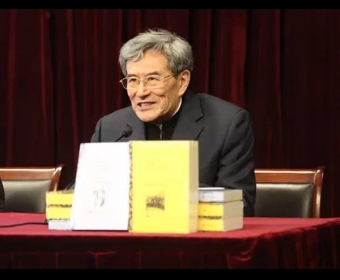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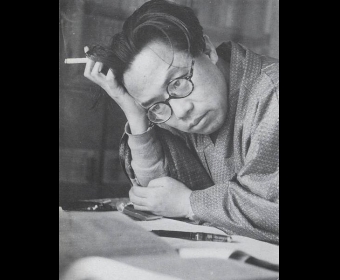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