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宏:找寻消失着的路途
——柳宗宣访谈

柳宗宣像
2004年6月19日晨,北京通州,独自在地铁入通线的梨园站等待着。
10年前的一个上午,卡车行驶在江汉平原的田野,他的家乡。我们迎风站在卡车上,他突然对湖边割草的人叫喊着,他对说我们说,“在草丛里,发现了我的妹妹”。
10年里,一些人和诗歌消失了,被年轮、琐屑生活的轨道包裹进未名角落。早年的朋友中,至今好像只有他时而让我在分行的铅字间看到名字。
现在,他从通州的家里走来接我。他带我坐公共汽车到市内供职的杂志社,让我计算他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
2004年6月19日——26日。谈话在柳宗宣书房和客厅断续进行。由本人根椐录音归类整理编辑。
母 亲
(夏宏)比较你早期和晚近的诗歌,感到你有一种重要的转向:开始你是为了诗歌而去寻找生活,或者说为了诗而生活;后来是生活本身让你感到了诗意,而且越是到后来发现你是在用诗在记录个人的重大事件。
这种转向是怎样发生的?
■(柳宗宣)早期的写作总是在捕捉着诗歌,现在好像是在你要遗忘它的时候,它突然抓住了你,真正把整个身体、灵肉都感动了,这成为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写作瞬间的到来是个人无法把握的。
所以你晚近的诗歌在写生活的常态,从情感出发,然后显现出某种命运感的东西。
■在写作中好像听到了岁月的回声,这种回声震憾了你,在这种状态里完成一首首诗是精神的一次次解放,体会到空虚生存的充实和巨大安慰。
从你的诗歌里常能感受到对脆弱性的表达,对柔软的甚至是软弱无力的东西的敏感。是否因为经历了生活的磨砺,感觉到精神资源的匮乏,然后把内心最柔弱的那一块拿出来,让它成为一种力量或精神的支撑?
■没想那么多。我有一种怪癖,老是想让自己的诗歌朴实一点,和自己的灵肉经历相吻合。
诗人自己首先会感动,但感动所抵达的地方不一样,有人被景色感动而去赞美自然,有人被生活感动而去对生活感恩,还有人被自我感动,强烈地要塑造自我。我体味到你的感动触及到你自己最柔软的地方,你的感动抵达哪里?
■我的内心非常柔软。或者说写作让我抵达自己存在最能触动我的地方。在写《为母亲送行》中,很多感情潜伏“我看见……我看见……”的叙述之中,我克制着不去说,不去表达,遵从诗艺的内在要求,发现一说出来就伤害了许多东西。那情绪的暗流隐藏在看去平静的叙说之中,这样更有力量,它彰显的东西更多。而我从北京回潜江老家处理母亲的丧事,在整个过程中我克制着没有流泪。在肃穆、紧张繁杂之中完成了一生中的重要事情。在生死的交界点,人特别脆弱。对存在的各种体悟在一个个瞬间契入你的内心,它们在我心里存活很长时间,没去触动它。
非常温暖的一块突然消失了,人在脆弱的时候不能直面?
■事件中有很多琐碎事情要处理,特别牵动人,但我很冷静。几个月后,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同诗友向隽谈到各自内心的生活,说到凌晨五点钟,我说到我母亲之死,我说我看不见我母亲了,那时泪水就流在脸上了。
在写的时候,多年前的经验和记忆出现了,整个身体在颤动,但我克制着,泪水也流出过,写到最后,“天忽然又晴了当我们回到城里/我感觉一身轻松我把母亲送回故乡/我看见我站在十里长安街上观望/大街上的车辆和行人/我看见路旁的建筑,我视而不见/我又看见火光中母亲的衣物升腾的青烟/我看见我的泪水终于流出来了”,这个时候现实里的悲痛已经完全消解了。母亲成为本源,你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已经丧失了它,已经回不去了,只有无可奈何地告别。
可诗歌让消失的东西突然又回来了。
■在回忆中重返,返回到我们的语言之中。“非典”期间我在家里闷着,翻读着艾伦金斯堡的书,忽然某种东西牵动我,要我把它写出来。
一首诗当你完成后,你发觉其中呈现的意象、场景和情感是你经过多年的积累,你以为它们被遗忘了,但它们隐伏在你的身体里,在呼吸在生长,最后寻找着时机,它们要显形。
在现实生活中,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但是在情感方面很脆弱。
这种脆弱性开始肯定指向情感,但现在我想问你是否感到过精神资源的匮乏?如果是,这种脆弱的、柔软的东西反而能支撑起你的精神?
■我们的母亲死了,一切本源的东西在流逝,只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流浪着,寻找着,被自己内心柔软的东西感动着……
孤 单
你常谈到流浪,而在你的诗歌中经常呈现出"家感"(我不想用"家园"这个词,它已经被滥用到失去了本初的意义),比如你几次写燕子在你的居所筑巢。
■像写《棉花的香气》,我是想回到我的老家,回到我回不去了的过去的生活里,这也是对整个乡村文明的哀悼。现在我感觉自己开始老了,回不去了,所以对自己过去的生活要祭悼。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你的诗歌在时空感上总是处于回望的状态,回望中的两种距离:时间上的距离,很多年的内心存积在某一时刻被触动,然后你就回望从前,想回到从前某个带给你震动、安慰、温暖或痛苦时刻的情愫里。空间上的距离,你说你在哀悼乡村文明的流逝,你是在哪里哀悼的?你是在北京来回望潜江?
■这距离确实很远。假如我不离开家乡,不和我的出生地构成一种距离的话,我无法回望。除了心理上的时空感,还需要地理上的距离。可我觉得这两种距离还不能完全概括……
时间的流逝在起作用,地理位置的改变在起作用,还有什么在起作用?
■还有什么?我的精神找不到路途了,现在只有回到过去。为什么说自己老了呢?现在前行的路都找不到了,就想回到从前寄放自己的内心的地方,但是又回不去。
你是否讨厌漂泊?
■我太希望安定。我很反感现在的工作、目前的生存方式。特别向往安静,甚至想找一个院子安静地独自生活,回到自己所愿意的写作中来。我经常在梦中回到过去的场景。目前我过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愈来愈觉得自己回不去了,又想去复原它,那种个人的孤独的隐秘的同早年相似的生活,复制它就是想重建它。在北京不可能复制在故乡的生活,那是精神上的一种虚拟。
那是诗歌带来的安慰,你在寻找安慰?
■我的写作是来自身的感动,存在对我的感动,现在这种感动太少了。
有自恋式的诗,夸张自我的脆弱性,情感纤细到一触就要断的地步;有逃避的诗,诗人似乎对脆弱、柔软的东西感到羞耻;还有的诗歌,根本就不能让人感到柔软的情愫。
■我对存在充满了柔情。我一直将自己定义为存在主义诗人。真正能感动人的艺术家很少,我理解在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死后,刘小枫说他"感到了在世的孤单"。
带给我们温暖存在的本源一个个在丧失,这对我们个人来说是重要的精神事件。
父 亲
■我在诗中这样写到:"当我们回到城里/我感觉一身轻松我把母亲送回故乡"。我好像特别理性,知道必须告别。有一种感觉特别奇怪,安葬母亲回到北京后感到身体轻松,死亡对我们的负累太重。我有相互冲突的想法,一方面想挽留母亲,另一方面又想把她送走,服从命运,想自己轻松一点,摆脱一些负累。我一直想回到母亲的身边,又想摆脱她。
而你在写父亲的这一首里却有强烈的欠负感。
■歉疚感。父亲的死让我感受到对死的无可奈何,感到自己特别卑弱,不能帮他什么。而且父亲在生活中也无可奈何,找不到任何依靠,我这个远走他乡的儿子不能帮他什么的时候,他无望了,选择了死。晚年他靠我哥生活,嫂子和他的关系很紧张。母亲晚年跟着我这个小儿子,还是享了福。
你父亲是不是病了很长时间?
■肺气肿,他很痛苦,无以安慰。
有一位年长的人告诉我,现在农村不少老人不是自然死亡的。
■对父亲我感到特别内疚,特别内疚……我感觉自己活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要写父亲?那是我正在重新选择生活的时候。我的状态契入父亲当年的无路可走的境遇,自身的境遇与父亲当年的境况重叠了,如果没有和父亲同感的东西,没有那种对存在的痛心,我是不会完成这首诗的。
"自我"在你诗歌中的出场十分鲜明,除了这一首,有一首《当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最后一句给我深刻印象。你写到:"我想,我离你越来越远",为什么不简洁地表述为"我离你越来越远"?
■这样写好象是在对自己进行着打量。
自己在这个时候必须出场。你写父亲的那首里,在写自己作出选择的时候这个"自我"出场:"发信的路上,我决定离开这里:/单位快倒闭了;院子里死气沉沉,/还有几个人在那里。/你是不堪忍受才用一根麻绳/把你与我们隔离。"
■写的时候我是将父亲的死和我的存在境遇混杂在一起来呈现。
父亲的死是无可奈何的,没有办法,他对自己的困境只有用死这种方式解决,而我是通过离走。我是在父亲的死中获得出走的力量,以前对父亲之死有些害怕,在诗中我这样写过:几年前你是我的对立面\现在,你在我的身体里。”
"父亲"这个形象在你多首诗中出现过。
■写这首的时候很多场景和记忆是多年前的,而且在另外的诗歌里作为意象出现过,后来又转移到这里。比如在梦中梦到他,他和我女儿莲子在一块。表面上他活着的时候和我没有沟通,实际上父亲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母亲,在骨子里。我好像在重复着他的某些生活。"想见你/你去贵阳做牛马交易。一双近视眼/是怎样在走南闯北……"有一次在石家庄火车站,他突然站立在我面前。我总是在生的奔走中与父亲相遇。甚至在他死后,我代替他去看望过姑妈,"你死前总是惦着你大姐,/我远方的小脚姑妈,你死后,/我去看望过她,同你一起。"这一句太柔软了,写到这里我流泪了,我现在不大喜欢这几句,虽然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
为什么现在不喜欢了?
■觉得应该更深入地开掘我内心的忏悔、人性中那种阴暗的东西,我用柔情掩盖了人存在中的黑暗的部分。这首诗前四十三行处理的我很满意,但之后没有深入下去,用对父亲的颂词掩盖了更真实的东西,我准备改写的,但改写需要勇气。
我是一个虚荣无知的人。在教书的时候,有一天他到学校来看我,走到了教学楼前,我很害怕:父亲是麻子(他早年得过天花)!我没留他吃饭……我想把自己的虚弱、阴暗写出来。
写父亲这一首比写母亲这首,我觉得更好。
■写父亲这首好象更内在。它们表现形式很不一样。
在你的个人性上,写父亲的这首更重大,更尖锐,深入到长期困惑你和让你感到无能为力的层面中。父亲这个形象一出现,你好像就在表达一种负罪感。
■确实有负罪感,而且我还不敢面对,不敢忏悔,即使忏悔,也不敢在诗中呈现出来。那年写它的时候没有这种力量,一个诗人面对自我需要时间。
是否担心一旦忏悔了就美化了?
■不是担心美化,是写诗写"滑"了,很多东西还没完成。
"父亲"是你诗歌的一个源头,特别是你后期的较成熟诗歌中,他是你回到自身的一个源头,你通过写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来面对自我。
■我感到人性中虚弱、假的、阴暗的一面。这让我感到一个诗人面对自我的难度和修炼所要达到的层面。
特别是在人意识到这一面后,会痛苦,而且这一面在人的一生中还会延续下去,无法摆脱。
■那时我逃避父亲,怕他死。现在我越活越朴实了,能面对父亲之死和隐藏的自我了。
用柔情掩盖了黑暗的部分,能这样说也是一种勇气。
■这种柔情是真实的,但它遮蔽了我最需要面对的、更残酷的东西。我被柔情感动了,让表面的真实遮蔽了更内在的。这个事件对我个人来说很重大,不能就这样让它过去。有一次我对哥哥说:我们两个为父亲都做了什么?他那个时候也害怕父亲的死。父亲死后,我去看我的姑妈,人真的需要感到自己有罪。难道那时我真的经济上很穷吗?人总是逃避生活中的"重"。
可你的诗歌动人之处恰恰在你感到无能为力的地方,就像经过一场搏斗之后又认命了。
■父亲是用死来解脱,我从中获得了生的力量,我要离开。我们都是在生存中寻找着出路,外在的和内在的出路,漂泊多年后我还在在寻找。现在我不放弃写作,好像这是家园一样,在自己的语言中获得一点安宁。
诗路
谈一下你的诗歌经历吧。
■ 1989年,我27岁开始写诗,已经很晚了。这之前也接触过诗歌,大多是语文课本上的……
那个时候为什么想到要写诗?
■ 对自己的一生要有一个安排,想找一件事去做。当自己有了工作有了家室这时候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了。
除了写诗,有很多事可做,比如继续谈吉它,玩乐器。
■那时在潜江有几个诗友,在诗歌报上发些东西,他们办民刊,很热闹的。他们寻访我来到我所在的校园里,我受到了些感染。开始写诗后我喜欢上了假期旅行,一个人漫游。这样经过了五六年的学习期,一旦开始写诗我就很投入,放弃了所有学历的进修,但是通过诗歌函授来接触我喜欢的诗人,同他们书信来往。在《诗歌报》的函授中,韩东修改过我的诗歌。后来诗友推荐我参加《星星》的,和孙文波联系过,到现在我还叫他老师。同于坚有过书信往来,他给我写了几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信。同这几位接触后,我开始系统阅读,比如巴尔特的《零度的写作》,于坚曾谈到过:逃避读者,回到语言。我用了几年时间才理解。于坚的诗歌对我有亲和力。对于坚一直心存感激,三四封谈诗歌的来信,一下把我从小城阅读的孤陋状态里提升出来,从传统的那种直白的抒情进入到90年代的冷抒情。孙文波也帮助我打开了阅读的视野,在语词的运用上开始革命性的改造。我学的是中文,以后发现这对新诗写作有众多负面影响。
通过几年的阅读、反思、朋友间的交流,诗歌观念在改造,从极其传统的写作慢慢进入到相对现代的写作中。另外,我对美国诗史是特别清晰的,那阶段几乎所有的美国诗歌的中文译本我都翻到了,喜欢美国诗歌的开放性,现场感,诗歌对当下生活处理的能力。还有美术界的刘向东的绘画对我们新诗写作的走向也构成了某种呼应,诗画在那些年都开始直面当下并对个人的经验进行处理,转移到诗画中来。
除了于坚、孙文波的诗歌,在阅读中什么诗人对你产生了影响?
■ 还有米沃什,他诗中的不可妥协的敏锐的洞察力,他在集权统治下的自我放逐,他对语言复杂性的了解对我一直产生着阅读兴趣。
英国的后运动派诗人汤姆-冈,看了他的诗后很投胃口:诗歌还能这样写?后来我写了一首《与诗人在小镇度过的夜晚》,在我以前的观念里这不叫诗歌。表达方式完全变了。
这一首是你在对诗意的体验、表达上转型的标志吗?
■这首诗应该说是在表达上更即时开放,在我创作中最更重要的标志是完成长诗——《一个摄影师冬日的漫游》,这是1995年我从西部几省旅游回来后写的,是多年的诗艺积累后达到的一次飞跃。就像翻越了一座高山,将自己过去摆脱了,这首诗出来后在诗友中获得了好评。
可那首中,某些残留的痕迹还看得出来。
■它是我从"学徒期"的模仿转向独自劳动的一次重要过渡,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东西,写出了《小镇的黄昏》、《给小丝的叙事曲》等,没有模仿了,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述方式,感到特别踏实。
"学徒期"之后有什么人和诗对你产生了影响?
■死去的宇龙对我的帮助比较大,和他的交往让我加强思考诗的技艺,对诗歌的形式特别关注。张曙光的写作对我直接产生了影响,我的《小镇的黄昏》和他的一些诗产生了呼应。九六、九七年后,明显加强了诗歌中的叙事,我特别亲睐这一点。诗友们也在默默做着这个工作。张桃洲说我发展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宣叙调因素,我承认这一点。
我亲睐的于坚、张曙光、孙文波,他们的创作对我的写作影响慢慢弱化,于坚过去的口语诗显得简单了。叙事应该是给诗歌增加了难度,宇龙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和他在形式问题上做了很多具体的交流,给我的写作在文本上带来了自觉。
美国诗人唐纳德-霍尔的东西让我印象很深,他的长诗《踢着树叶》让我想到诗歌的构成,诗歌容纳其它文体形式的可能性。喜欢的美国诗人我可以说出一大串。像弗洛斯特,惠特曼、艾伦 金斯堡 ,罗伯特 克里利等
北京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第一次是1999年3月,到北京来看一看。觉得好像在潜江的生活已经过完了,想换一种生活。
来北京是为了诗歌吗?
■想在诗歌中发展下去,突破一下,在小城呼吸很困难了,用兰波的话说,人们在他自己的故乡被流放。潜江当时没有沟通对话的人,买不到好书,太闭塞的环境对写作是一种伤害。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就像弗罗斯特离开美国到英国去一样,为诗歌寻找好的环境。
九九年你返回潜江,呆了半年。
■那次离开北京是迫于生存压力。来北京没有给诗歌写作带来期盼中的效果,只是感觉到谋生对写作的伤害。
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里谈过这种伤害。许多捷克作家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工作后,为了谋生很多活都干过,西方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对写作是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常说的增加了生活体验。克里玛说,如果一个作家20年的精力都花在为生存而奋斗,那是对精神的折磨,甚至是摧残。那些评论家可能是美化了那种他们没有体验的生存经历。
■捷克作家和中国作家的境遇特别相似。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作为一个诗人对自己的命运很清晰,对附加在诗歌之外的东西是抗拒的。
仅仅只是为了写作而到北京来?
■我在湖北的生活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还安定,但是从精神生活从写作上考虑,想换一种生活了,当时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出走,40岁以前再不出来,生活就完了,看不到任何希望,生活没有奔头。长期在潜江生活,感到精神的孤单,整个人文环境恶劣,如果在省城,我不会出走。但现在对在哪里生活都无所谓了.
小时候我就渴望出门,见识外面的世界。在小城看到浙江人到学校里推销教学用品,我就激动,他们带来异地的空气,还有我们不理解的方言。来到北京后,没想到这么多哥们漂在这里,就在北京停下来了,没有物质上的准备,没有考虑生存的严峻;长安居不易,京城米贵,那时我忽略了,生存是第一要义。如陶潜说的:“人生归大道,衣食固其端。”
99年3月来北京前,我没有辞职。住了一段时间后,压力大了,感觉不对劲,房租、吃喝、交通费用交出去,衣袋就所剩无几了,后来在地坛附近找了份工作,但是也很无聊,编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稿,人成了机器。精神一高蹈人就容易踏空。
你比较恐惧这种踏空状态?
■在地坛那个公司上班,没有遭遇到生存的威胁,但是我渴望过自己的写作生活,就离开了地坛,租房子写作。原来我想象外面世界的时候精神性成分很浓,其实外部世界是很日常性的,不带有任何理想光环,首先要活下来,然后才可能从事想做的事情。原来我对异地生活总是抱有幻觉。其实我们在哪里都是过日子,能活下来了写作就行了。在北京租的房子里,读兰波全集,他的生活感动了我,他到巴黎去,后来为什么住不下去离开了呢?最后身不由己离开,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干了很多苦活,包括做采石工,去淘金,几乎放弃了诗歌写作,让我感到漂泊的痛苦。他到巴黎后没有人帮他,他感到整个城市对他的拒绝,诗写得再好有什么用?他面对的首先是活下去的问题,最后他只有离开。回去是不可能的,他一直走在远离故乡的异国他乡。当我读他与家人的书信,心里酸透了,他的生活和我当时的境遇太相近了。你不活下去还能写什么诗歌?我很孤单,在异地没有谁来帮你。后来我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返回潜江,精神萎靡了一段时间。
那些漂在北京的诗友、朋友们呢?
■都是孤立无援的,他们也在艰难地谋生。你会感到整个生活对你的排斥,没有多少温暖的东西。布罗茨基到美国去,奥登帮助了他,提供了衣食之助。
享受了一个诗人的“待遇”。
■回去后呆了半年,但是难以甘心,我斗争了很长时间,决定第二次去北京。2000年过了春节我又来了,首先解决生存问题,找份工作,稳定下来。我做过图书发行员,为的是想以后过自己的写作生活……在北京看到很多人在为生存挣扎,不少人抱着美好的愿望来北京,一些画家在北京的生存一团糟,这样的生存是对他们艺术是一种伤害,没有出路,回去也没有希望,就死守在北京。我从城里搬到郊县,在画家村住过,住农民的院子,把生活降在最底线,守下来再寻求发展。最后钱也快用光了。有个星期我写报告文学,赚了四千块钱,我决心死都不回去了。撰稿已经进入状态了,但那是非文学写作,成了枪手。那时还在找工作单位,受了不少欺骗,北京骗术太多了。后来还是文学救了我。
来北京后一直在为解决生存奋斗,写作受到了伤害,但是某种程度上又成全了我,人的身份变得复杂了。我不再是一个单面向的人,多重身份出现了:诗歌编辑,期刊发行主管,某公司顾问,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土乐迷和京郊居民。在漂泊最艰难的时候10块钱的盒饭我分两餐吃,特别苛刻自己。有一次饿着肚子去地安门去领稿费,路过一家涮羊肉的饭馆,通过落地窗户看进去的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有钱了把老婆孩子带来吃一顿。当时手上不是完全没钱,是特别紧张,放着不敢用。
你在潜江的时候我去过你家,生活不错。在北京你是因为尊严而不愿向朋友要帮助?
■都很苦,孤绝的状态,都在寻找出路,我对漂在北京的人蛮有感情。现在很多人混得不好,我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平台,才能表现自己的能力。我在文学圈子呆这么长时间,对所谓文学上的名声看得清楚,对文学还能保持一份纯洁的感情,做编辑也很敬业,对外在的荣誉越来越淡泊了,包括发表作品。
我觉得自己在北京的整个生活都不真实,很无聊,我一直想着去过个人生活。
这里面应该有很真实的东西。
■现在还有生存压力,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有时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还不满足呢?那么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我在慢慢调整,要解决精神问题。外在生活的繁杂与混乱,必须用内在的秩序来平衡它。有时连书都难以看进去,偶尔看看也很飘,不细致深入,事务太多了,我烦自己这种状态。
阅读像镇痛剂。有时在非常烦躁的时候,拿起书来看进去就感到安静,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有种撕裂感啊,被外在的事务牵扯着,又想钻进精神世界里。在三联书店,每次去都能感受到精神和身体被撕裂的痛苦。人有看不完的书和急于要做的事,但为了挣钱为了尽各种责任,你不得不流离失所在城市的街头。
原来经济上的压迫总会留下阴影,即使你境遇好了,阴影还在起作用。
■现在我把钱看得很重,可能是漂泊生活培养出来的,我理解兰波在他流浪的时候将8斤重的法郎绑在腰间以至让他得了痢疾,那时金钱成了他流浪生活惟一的帮助。现在我有时看看自己的存折才获得某种安慰,有了一点储蓄你就不怕下岗不怕别人岐视,你就会无所畏惧。------这都是漂泊生活带来的病态,凡在他乡生活多年的人都会养成一些怪癖。
但我也把钱看得很淡很虚幻。有时报复性的对待它,另外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会去帮助。过了艰难的漂泊生活,你会培养出悲悯之心。
感觉到了你的悲悯感和同情心。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很少有人像你昨天那样指着路边躺着的人对我说:你看看这是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些人像蚂蚁一样在城市里活着,没有任何尊严,随时都可能被踢上一脚……有时我会问自己的悲悯感是否真实,有些人对别人的悲悯和同情是伪善的。
■居高临下的。
还有就是籍此来感动自己,美化自己,从而获得纯洁感。
■北京生活对我的写作有伤害,又丰富了我,打开了我的世界,这也给我的写作带来了难度。它让我看清了文学场上的虚名浮利。我现在慢慢恢复着对生活的诗意感受,精神力量也在恢复,想慢慢再进入。外在的很多幻觉丧失掉了,内在的东西就更坚定。
写作的浪漫性被剥离了?
■不,原来附加在写作上的功名幻觉、价值感和规则消失了,然后建立起自己对写作的新的信念和价值体认,而且这种热情来得更彻骨。在北京的漂泊,使我对这个时代、国家、文学制度看得很清楚,更加坚定地回复到艺术本身上来。剔除了个人文学理想中的杂质,回到个人内心的对艺术的尽情,我所有的生活都是为了能够写下去。原来写作可能是为了一些花哨的东西,现在是为了能安慰自已和个人的一份文学理想。
有时在生存的奔走中忘记了文学,突然又听到它的呼唤,想接受文学的抚慰。我依旧看轻外在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的要求看得比什么都重。
这几年来,在武汉的几次见面中,我总在掂量你在谈话中显露出来的精神状态,包括你只是谈到生活的时候。我感觉到你的饥渴感、躁动感,那种精神状态是这个写作者必须经历的。
■你看这次我是不是比较安静。
潜江
谈谈你的家乡潜江吧。
■我生在那里,就是被抛在那里了。
曹禺是潜江人。
■唯一被潜江引为自豪的……实际上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潜江人,祖籍是那里,但他不在潜江出生,对那个地方可能没有感情。
假如我不写诗,潜江也不会牵动我那么深厚的感情。潜江的很多风物,像燕子、栀子花、雨水、莲蓬、道路、村落、那里的风俗,都进入了我的诗歌。
写得最集中的一首是《为母亲送行》。
■我没意识到。
除了景物,你写的那些人是潜江的,他们的感情是潜江的。当你在其它的诗中写潜江的景物的时候,有没有感到相对要缥缈一些?而这一首中有复活感。
■我没有刻意去写,它们自然地就在场景里头了。不过在写作的时候我有意将出席母亲葬礼的人:我的亲戚的名字过去的学生和同事朋友的都列在了诗中。当我写下那些名字,还有那些地名,我充满了感情。
正是因为你关注的是为母亲送葬这个事件,而不是潜江,反而让你对潜江的情愫、体验都自然出场了。
你的诗歌里有两个潜江:一个是你完全融合其中的潜江,比如早期你平静地在那里生活的潜江;第二个是你在异地回忆中的和你从异地回来后打量的潜江。
■从异地返回后的潜江,这个在诗歌中表现得不多。你看《下雨》和《栀子花香》这两首,是我在潜江对早年生活的记忆,在诗中直接呈现。我说过我是个存在主义诗人,诗中的意象自然来自我日常所见,它与我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和记忆是契合的,在诗中我不会将艾菲尔铁塔写进来,我写到的是湖中的莲蓬,乌驳船头的伯父,从小随我们长大的桅子花,就像弗洛斯特的诗中只有他农场的土豆、河水和开岔的小路以及他劳动的场景,比如夜间提水。
在抒情比较单纯的时候,对于那些景象、意象来说,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由另外一个诗人来写,也是诗意充沛的。
■在那里从出生、求学到工作,我生活了39年。在那里我呈现了早年的记忆,特别重要的是我还写了我在那片土地上的游走,在故乡流浪的状态。
在故乡流浪?
■对。你看《小镇的黄昏》,感到故乡在流逝,自己在流离。离开潜江也是诗歌的需要,诗歌的外部和内在空间都太窄小,想通过漂泊来增加它的意象,拓展诗歌的空间,那时,对我来说,故乡已经在诗里写尽了。热爱着故乡,但是又感到一种隔离,自己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散文里写到童年到火车站去抚摸铁轨,一直想离开故乡。只有在离开后归来,一个人才能打量故乡。我上学、工作都在那片土地上,外部世界对我的诱惑很大,总想出远门。
在荆州师专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家,再重新看故乡,感觉神奇得很,路变小了,整个村庄收缩成一副风景画了。
后来我经常旅游。我在青海戈壁滩上给潜江的家人打电话,在异地打量或想念故乡的时候觉得特别遥远,听到家人的声音变得很远很远,微弱,甚至陌生。我一直想同故乡构成某种距离感。
想从故乡出走再回望?
■这种愿望很强烈,人总是置身其中,是永远无法打量的。有时我设想过在潜江住在旅馆里,从旅馆里打量自己生活的地方。
卡夫卡随笔中说,没有目标,离开,出门就是目的。
在散文中我曾写过夜归,有一天晚上我从异地回来听见同事们的鼻息声。在静夜里,一个人扛着旅行包,望着下弦月,回到宿舍楼的院子……
你原来是在寻求一种流浪的感觉,但那只是暂时的感受,不是真正的漂泊,没有现实的谋生内容在里面,所以比较超越。
■99年离开潜江,曾以用多种方式回去,在异地的梦中,在感觉自己特别疲惫的时候——故乡就在身体里。今天中午我回想起童年的记忆,想到故乡。但是回去后又无可奈何,连再住下去都很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
■再回去感觉同故乡的环境隔离很远了,成了一个陌生人。一首诗中我写过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故乡不是在过去/就是在天堂/要不就是在天涯某处/或者故乡隐在你的身体里”。
来北京后你好像很少写故乡。
■故乡是我的一个遥远的存在,一个背景,我更关注个人游走的生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但现在你的故乡更多是精神性的存在。是否来北京之后,你的精神性的需求转移了?故乡是否被尘灰遮住了,某一天或许你要擦拭这层尘灰,唤醒记忆?
■我写《棉花的香气》,就是一瞬间回到故乡。但是我处于游走状态,回不去了,这一点我很清醒。有时我想回潜江去建一栋小房子,回到那里居住……看我老了能否回去,现在肯定时候没到。
沈从文的墓地旁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他的话: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
■有时很想念潜江,想回到我的出生地,发自内心。
是感情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要求?
■可能是感情上的东西,有时我想在潜江盖房子,兄弟秭妹都住在一起。
对出生、成长之地的强烈留念?
■有个词是要跟随我一生的:返还。人的一生就是在回返,返回自身,回到我们自己。你离开故乡我才体会到,人的身体、精神是被故乡塑造的,潜江流塘口,那个地方真正塑造了我。
最初的东西是被她塑造的。
■现在依然在影响着我,持续地影响。我觉得我老了,不愿意在异地漂泊,越来越想寻找我本源的生活,可能我所远离的恰好是我所要寻找的。但那些在故乡也流失掉了,我只能在诗中复活它们,在《棉花的香气》里我试着复活了一些。
有了距离你对故乡的感受更丰富一些。
■我对她更宽容了。你发现被她塑造了,你的饮食习惯、脾性、欲望和要求,包括你的方言,所有的都是被她塑造了。有一次和李师东在西安凤翔东湖内见到水埠头,我们就留了影,因为我们都是在水乡长大的。
其实目前的生活里,你也没和故乡断开,你看你身边的人都是潜江的。
■某一天我可能还是要回到潜江,不是回到县城,要回到我的出生地那个村子,我一直想当个农场主。这还是想象,不知能否兑现。
和故乡的关系像一场一生的恋爱。可能用恋爱来比喻还狭隘了,这种情愫应该更宽广。
■像弗罗斯特说的:情人式的争吵。我离开潜江的时候除了为诗歌,还有虚荣心理,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愿望。
是39岁离开故乡的想法?
■不,一直都有,当地的风情文化给人一种暗示。经历了异地的漂泊后我越来越朴实了,回到潜江怀着朴素的心态。故乡,是你带着她在异地迁移漂泊。我想在诗歌中复活对故乡早年的记忆,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想复活过去。
在这个意义上,《为母亲送行》复活了故乡。
■不,在这点上我更愿意说《棉花的香气》。通过珍秀这个女人负载着我对早年故乡的记忆,对她的记忆就是对故乡的记忆。十几年前我曾为她写过一首诗,这是第二首,我写的那些早就消失了,我在用诗歌挽留着故乡。回到故乡特别怅惘,“你也回不去了/乡村文明的破败/连同它树木的毁弃/我倒成了它的遗子”。
在都市文明里,我是一个游走者。我基本没有什么都市生活习惯,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记忆和生活习惯。我一直有一个顽固的观点:没有乡村生活的体验,没有自然神性的体验,一个诗人就缺少了珍贵的东西。乡村文明的濡染对一个诗人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在我们的文明传统中,很多精神性内容来自土地。
■我身上有农民的很多气质。我喜欢弗罗斯特、希尼,因为他们身上有我特别亲和的东西。但是我身上又有某种高贵气质,我写不出所谓的乡土诗。
你体验到了土地上的神性。
■听家人说母亲怀我的时候,我伯父做梦,梦到水中一只甲鱼游走了。就暗示我不可能在故乡生活到死,我是要游走的。
除了土地对你的塑造外,你好像在受暗示影响在生活,寻找暗示对你的诱惑。
■早年的时候,姐姐嫁到异地去了;父亲也一直在外地卖牛……父亲能读古书,伯父能写一手好字,堂兄是花鼓戏团的导演,姐姐演过阿庆嫂。在村上看的电影,老家的月亮、露水.湖泊.父亲耕耘农田时哼的民谣,村子里盖房子夜里灯火中的夯歌,这些被我吸纳了,我的童年就这样被塑造了。在《小镇黄昏》里写过,我经常到小镇浩子口去买书。把黄鼠狼皮卖掉后,买连环画回来看,小时候装了一纸箱的连环画。小时候特别喜欢穿直筒裤,好奇装异服,;爱学武汉知青的风度和听他们唱外国民歌,爱吹笛子,而且喜欢在月雾下水埠头吹笛。
我父亲身上有侠客义气。他死后,有一个曾被他搭救过的范先生来打听他的下落,找到了我,我在散文里写过“父亲死后,还有一个人在寻访他”。我们家有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我姐夫是孤儿,父亲把我姐许给了他,姐夫是个孝顺的人,父亲吊死后,是姐夫给他擦洗身体的。我们家的开放性,影响着我对世界、对人的态度.所以我成家后家里朋友很多,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家的遗风。我吸纳了楚地故乡的地气,那些浪漫的美对我产生着影响。
他们是本然地生活着,而你有超越性。
■你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我是被唤醒的人。
你离开故乡漂泊异地,想回去可又回不去,这里面都是超越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超越性,也许你会感到还是故乡的地气和人情更亲近,就可以回去了。
■我一直怀疑自己能否种地。上高中的时候很刻苦,就是想考出去,最后我终于考上了。
现在的同事有时说我像农民……
你身上有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自己很高贵,可以看清许多人身上毫无诗意的一面。
■我一直庆幸自己从小生活在乡村,是农民的儿子,吸纳了乡村文明的精华。我觉得自己是有根的人,虽然这个根本身在消逝,已经被这个可怕的时代连根拔走了。
这种根,对写作者来说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只要外界撞击你一下,只要你被唤醒,你就马上可以回到自己的身体,而外界的东西只是触媒。我很在意是什么对写作者发生着影响,你说你讨厌从阅读中、从诗中得来的诗,这是重要的警戒。
■我讨厌复制的写作,追寻从身体中生长出来的。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诗歌的根性问题.
正是因为你经历了、体验了,身上有来自自然的质朴东西。
■我在那里生活了39年。
在都市里的生活渐渐安定下来,是否能感受到这种生活里的诗意?
■很矛盾,我也有倾向于都市文明的一面,对特别高雅的、人创造的东西也很亲睐。
因为你觉得那是诗意的、浪漫的东西?在超越性上,这和你在乡村土地上体验到的浪漫性是一致的。
■我对诗歌的形式也很关注。对新生的艺术样式的敏感.
如果某一天你发现都市生活很虚假,和自己隔膜,也许你又会想到回去。
■在城市里有套公寓,还渴望乡村的房子,就像画家村里的房子。我渴望回到和童年生活相近的环境里去。正是因为身上乡村情愫比较多,我比较古典,但又有很强的现代性倾向,内心里渴望接纳新生的东西,但内在的精神上我是被故乡塑造了,那种力量太强大了。所以我的东西古典但不显陈腐,新但看不出怪异。我是一个平和的形式主义者。
我以为要做一个艺术家,在某些方面必须愚钝、固执。什么都能理解,马上就能溶入,也许对艺术创造反倒不利。坚守着回故乡的渴望,这很重要。
■我身上有农民的朴拙。这平衡了我的生活和写作。
只有不丧质朴,才能真正敞开。
女子
你好象很看重《棉花的香气》。
■在《棉花的香气》里,我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和我爱的女子聊天,我们谈到早年的爱,珍秀是我早年喜欢的村子里的一个女性,她启蒙了我的爱,对故乡的记忆所有美的往事集中在她身上。我是通过一个女人回到另一个女人,实际上一生都是在回到内心里的爱,回到最初的爱的愿望。我在家里是老二,一直受到大哥的照顾。因为是老二,在农村没有人跟我介绍女朋友,我一直渴望异性的爱而得不到。我是从一个女人的身体回到另一个女人,回到月下的故乡流塘口,感到自己抓住了某些东西,棉花的香气就在我的写作中自然散发出来。
你是当时就感受到那种美还是后来体味到的?
■都能感受到。而且这种美不断地丧失着,一丧失我就不断去找寻,“你是源头,我在别的女人身上体验你”。
想挽留消逝着的东西。
■对女人的爱中,精神性的内容太多,色情的成分很淡。我在所爱的女人身上加注了精神的愿望。
对异性的渴望和对精神追寻的混合。为什么诗人为女人写了那么多诗歌,在生活里愿和女人亲近,更容易博得女人的亲睐?确实是在寻找、发现和呈现美好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女人身上朴素的一面,所爱的女人都有和我相近的乡村经历。我现在所希望的,和我早年在故乡看到的女人形象是相似的。受到文明的熏陶后,加上了精神沟通的渴望。对话的愿望总是保持在与女人的交往之中。甚至可以说通过爱的女人的深入沟通来达成与所有隐秘存在交流的可能,她们成了一个切入点。
有精神领域的要求,日常生活就得保持距离。比如说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波伏瓦当然是精神性要求很强的女人,如果他们厮守在一起,精神性的东西可能会被日常生活消磨掉。
■以前写的《为小丝而作的送别曲》、《当我们把电话放下》,写到了情感的游动。我想在情感生活里建立一个对话者,后来我不得不放弃了。
在女人的质朴性上,你需要精神的相通,如果单单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女性……
■那我会感到隔膜,必须有超越的诗性东西在里面,对天生的东西的超越。我对女人的追求好象呈现着一种幻象。
你在寻求完全的契合吗?确实有一种幻觉,比如你说渴望写作就是你的生活。
■我渴望自己的空间。
写作带来的生活容易给人踏空感,不真实。
■《棉花的香气》中的女人,她回不来了。我还给珍秀打过电话,这早年的乡村美好女性的形象在时间中消失了。诗中这个少女的出场,是在我经历了情感流浪之后,得到了某种归宿。我呵护着这些经历,忽视了就不真实。
有人曾对我说过:本能是人最强大的动力。如果人失去了本能,那整个文明不将存在。
■我写过一首《抚摸》,抚摸一个女人的身体,非常抒情地,“这是我另外的肚腹/消化着我每日的粮食/还有我对你贴近的想念”;到下面,“这是我身体的另一个空闲/我残缺的一部分”,这时我好像成了女人的一部分了。“这是我另外的一双手/另外的一双眼睛/看见掩藏在事物背后的那一个/代替我观看/死后灵魂的命运”。
你在找寻某一类给你稳固情感的女人形象?
■就像记忆里的乡村一样稳定。
质朴
为什么那么看重质朴?
■作为一个诗人,质朴性能让自己更有勇气抵达真实的存在。我把做人和写诗都慢慢地归于质朴,人还是要老实一点,要勇敢一点!敢于在生活中去爱,去承担,不逃避命定的东西。
你的诗意的质朴性还在于,越到后来越是少用抒情性强烈的词和句子。你触及到漂泊、痛苦、孤独的时候,很少把它们放大和夸张,反而是像说话一样把它们说出来,用反诗的形式进入到诗意中。《棉花的香气》里有一段回忆和描述,简直是叙事文学了,或者说是散文的语言,非常直白,但是从整体上看,有一股强大的情感冲击力。我把这样的诗歌语言看作是倾诉,你面对着遥远的事物说话。
■我给诗中所写的女人打过电话,这个做法……(笑),很好笑吧?她是我真实情感中的切入点,我把对整个乡村的记忆归于她身上。
你自己意识到没有,你在用这种靠近日常生活的叙述语言?
■我不喜欢雕琢,《棉花的香气》像是从身体里流出来的。我曾试着修饰一些句子,后来我放弃了,它们像流水一样不可改变,自然呈现,有着它们的自然流程。
在写作过程中,对伪饰的情感、形式是否非常抗拒?包括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中也有很多伪饰性的东西。
■我不再对语言上做过多的加工,让它回归自由自在的状态。它们在诗中互相呼应,带着我特有的语调,身体和灵魂的气息。
为什么不用那种夸张放大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不是“我看见天空中的父亲”,而是“父亲,你忽然站在了我面前”?
■因为我没有那样的体验,也就无法那样写。另外,觉得那是语言的暴力。
那样的语言很美,为什么说是暴力呢?
■我不喜欢那种美,它和我的身体没有关系。我喜欢用身体性的语言,它应该是从我的身体感受中生长出来的。身体有它的体验,幻觉和记忆,这是语言的根基。
你在抗拒那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抒情?
■不少抒情特别虚妄,和他的身体一点真实关系都没有,假的。为什么我不轻易抒情呢?我写为母亲送行,感情剧烈的,但我很克制,让情感回到它自已的空间,情感它是一个让人感知的客观化的东西,用现象学的观点来说,回到现场回到事实本身。在准客观的陈述中才能传达我的感情。情感不是夸张地喊出来的,有时它甚至是在安静的陈述中彰显;它在诗句的空白处敛藏。
在日常生活里,人也会有剧烈的情感表达,有表演和夸张……
■是有超常的表达。但要提防情感的做假或表演。崔健他提倡真唱运动,那是他看到了众多人的内心的颓废。众多的人在假唱在表演。
你是通过向生活要真实,来达到向诗歌要真实,你想把你的诗歌和你的生活吻合起来?
■我是一个老实人,技艺是很笨拙的,我的写作忠实于自己的体验。我知道诗和生活是有距离的。我看重细节,感受和体验的缓慢生长,写作的时候尽量去复原它。你看黄灿然的《祖母的墓志铭》写得多好,回到存在的原生状态而不去破坏它,诗人要做的只是去呈现它,那里面包容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一个诗人不应该强硬地用语言的暴力去破坏存在,要尽可能回到以物观物的状态为好。
你是怎样理解语言暴力的?
■诗人不能太主观了,把诗意强加给读者。在我看来诗人是观看与描述的人。诗人要做的工作是去观看或发现,让存在自身去彰显。
(夏宏:武汉大学中文系,此文引自2006年第一期《滇池》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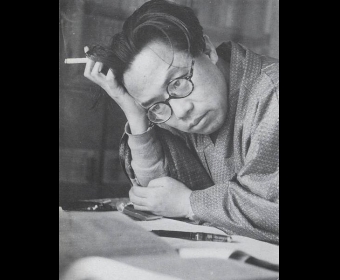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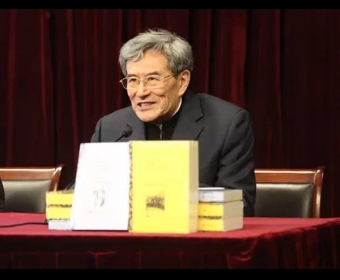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