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书写日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诗歌的一大趋势和重要特征;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是当今世界哲学、美学后现代转向的标志之一。何谓日常,何谓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或艺术的日常生活化,诗人自不必像理论家那样去做清晰的界定和回答。不过,正像所有的诗都来自诗人内心,经过情感过滤,所有的诗也都与诗人的日常经验息息相关。这本是常识,但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一方面常识往往为人忽略,另一方面质疑、打破常识本应是写作者的职责。一旦日常生活进入诗歌,成为文字世界的一部分,它就理应不被再看作“日常”的,而是依据每一位写作者的禀赋、个性、气质、素养、识见的殊异而不同。就像一段好端端的文字被分行以后,它确实不再是“好端端的文字”——诗人需要的是众人口中的“好端端的文字”吗?——分行的形式赋予阅读者以新的心理期待,亦即:分行的文字并不是它看上去的那样意义浅白,它将会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韵外之致,更不必说还有因分行、跨行造成的语言节奏、韵律的改变。因此,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应当以“日常性”的生活名之,它让读者感觉到——藉由文字技巧——对日常的无限贴近,却不是、也不可能是日常本身;诗人的目的是在文本发散的日常性中,揭示某些非日常的元素;抑或,由于太日常而未被觉察、未被表现的“不可思议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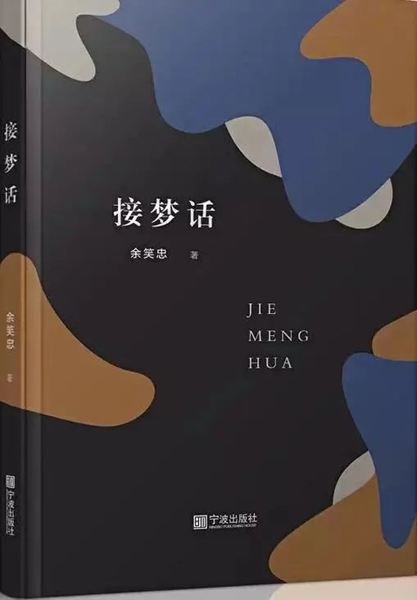
余笑忠诗集《接梦话》
余笑忠诗歌的日常性特征显而易见。三十多年来,他执拗地在每一首诗后标注写作日期——具体到某一天——以至评论家称之为“诗日志”,一个人“诗性的传记”。它们“乃是要让个体平凡的日常生活转换为诗性的生活,如果诗的写作有着意义,就在于面对日常的生活,诗还能够发声,能够确立写作的尊严,就是在这不合时宜与错误的生活中确立诗性的正义”(夏可君,同前)。怎样理解“诗性的生活”是一回事,但诗歌一定存在对日常生活的转换,转换方式的细微差异成就了不同诗人和不同风格的诗。在20世纪80年代于大学校园开始写作的这一代诗人中,余笑忠的殊异之处是对“细小细节”,尤其是对生动鲜活的视觉细节的痴迷:他的凝视在这里,凝神在这里,他的转换也在其中完成,就像他把“我”转换成婴儿,转换成盲女和油菜花,转换成飞鸟和暗中蓄积力量的蜜蜂。正是这些日常性细节,使他的诗晕染上浓厚的写实性,以至给人以“绝对的写实”的印象。但此“写实”非彼“现实”:写实之“实”是诗人的语言技法及其对阅读者产生的接受效果,绝非现实之“实”的简单位移;易言之,现实只有在诗人抓取并定格在词语之中,才成其“实”,并启示阅读者换一种眼光来审视生活现实。余笑忠认为,诗人“对现实的关注不可简化为对日常生活、对浮世万象的记录,而应该在更难以发力的地方去探寻……因此,与其强调关注现实——它在实际上往往是单向度的——不如关注精神的现实性,或者说,在赋予精神以现实性上下功夫。这才是诗人的职责所在”。这并不意味着退回内心,而是藉由内心“打通万物之间的隔膜,进而寻找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我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如何去化解种种障碍,将理智与情感、审美与道德、社会与自然之域相贯连”(同前)。
在上引几首诗中,与其说诗人专注于场景与细节的真实再现,毋宁说,他用心于自我与他人、他人与他人之间复杂的精神场域的构建;细节的点,在场域的网格中被用心安置,并随其中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变化而闪烁不定,充满伦理意味。相对而言,《告诫》(2011年)一诗语义指涉比较复杂,具有强烈的“精神的现实性”:
从泥土里被刨出的蚯蚓,它们
从未见过世面的肉身
暴露出来
以其渺小的弹性
顶撞碎石、阳光
和阳光下它自身的影子
他们推过来一个被反绑着的人
命令他:吃它
他们又推出一个人,一个妇人
他们笑道:要不就割下她的奶子喂你
母亲叮嘱她的孩子:不管什么人盘问你
你都说,我和你们是同一个部分的
……蚯蚓就一直在我们的喉结里涌动
蚯蚓也和我们是同一个部分的
“告诫”的本义是警示劝诫,具有浓厚的人际伦理意味,可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个人对一群人,一群人对一个人,或者,一个“我”对另一个“我”。不过直到第五节,“告诫”才姗姗来迟,我们也才明白它指的是母亲对孩子——抚养者对被抚养者,教育者对被教育者。每个人的人际关系都开始于父母,我们最初的人生知识和经验也莫不来自朝夕相处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教诲、训斥、鼓励、赞美等,将影响、左右我们对世界、对陌生的他人的感受和体验。然而,正如你注意到的,诗行里并未使用“告诫”,改用了“叮嘱”:后者的含义为前者包容,前者的伦理意味又不能被后者完全替换。这种词语游戏似乎在暗示,诗人想以确指的人际关系,来映射更为宽泛的人伦抉择。母子关系只是诗中交错出现的种种人际关系之一;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只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恒定不变,至死不渝,其余种种关系则会依据情境的不同而发生程度不同的裂变。
与《春游》等诗来自诗人对眼前和回忆中场景的观察与截取不同,这首诗建构起来的极为特殊的场景,可看作想象与虚拟的产物,但其中显然有诗人对头脑中积淀的历史资料的“简化”。它既是具体的,焦点在母子,又是抽象的,让人无从确定“他们”和“被反绑着的人”的身份;虽说后两者的人际关系是抽象的,但无疑可划分为邪、正两派。而诗采用的正是虚实相间的手法。此刻,母子俩和其他人置身于特定情境中,母亲郑重其事的“叮嘱”,很可能是因为她感应到了孩子身上滋生、蔓延的恐惧——会传染的恐惧,会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人的恐惧。这正是“他们”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事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以恐惧制服对抗者,以示众警示围观者。这是最原始的,也是最便捷、最有效的对付敌对者和摇摆不定的群众的方法。正如“叮嘱”一词的本义——再三嘱咐——所示,见多识广的母亲意识到这一场景并非绝无仅有,它会“再三”出现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因此,也正遂“他们”所愿,母亲毫不犹豫地把“你”(孩子),推向了“你们”——“盘问”者——那一边。以虐待他人取乐的暴力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被“再三”地使用;它之所以“再三”地、以几乎相同方式上演,因为它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可以被围观者口耳相传。结果,这样的暴力不仅成为历史,也成为当代日常景观中的一部分,只剩下“被刨出”、被抛掷到人世间的蚯蚓不明所以。周围的一切都令蚯蚓深深恐惧:阳光盛大,但不属于它的世界;光明尽显,却不能阻止恶的复苏。蚯蚓顶撞碎石、阳光和自身影子的本能,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母亲“叮嘱”中体现的、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的本能,甜蜜又苦涩的爱的本能,以及所有人躲避恐惧,并希望免于恐惧的本能——我们与蚯蚓确实是“同一个部分的”;蚯蚓堵塞住了我们的喉咙,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世界哑然无语。
余笑忠跳脱了触景生情的写作套路,在诗中预设了日常生活中复杂难解的人伦景象,以表达对人生选择的伦理困惑。这或许不是他写作的本意。我相信他最初写作的意趣集中在蚯蚓的意象上,这个被无辜挖掘出来的生灵身上,晕染着诗人童年的游戏记忆。地面的碎石、阳光令它惊恐万分,与地下暗黑、潮湿和松软土壤给予它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形成反差。此刻,它被强行“卷入”人的世界,充当行恶者的道具,成为人人难掩恶心和呕吐的对象,却被诗人发现它“和我们是同一个部分的”。无辜者的无辜不是毫无来由的,而他们对自己的无辜的确信和申辩,将使他们远离被反绑着的人,那个原本和他们是“同一个部分”的人。“母亲叮嘱她的孩子:不管什么人盘问你/你都说,我和你们是同一个部分的”。这番叮嘱,会让围观的母亲们,更多的为人父母者,感同身受吗?
可以略为展开分析诗中人伦关系的复杂。全诗有四个主要表现对象:蚯蚓、被反绑着的人、“他们”和母子。绑人的“他们”肯定是属于“同一部分的”,其中每个人都怀着至少是暂时的有组织、有依靠的安全感。被反绑着的人是“他们”施暴的目标和敌人。“他们”需要目标和敌人;倘若没有,可以去制造。“他们”正是通过制造一个又一个类似的目标,在同仇敌忾中,形成越来越大的“同一个部分”——另一重观照视域中的“我们”。被母亲叮嘱的孩子必须学会跟“他们”结成“同一个部分”。可以肯定,那滚雪球一般膨胀的“同一个部分”中的每个人,当初也都经历了类似情境中的恐惧,也都接受过母亲——过来人——的叮嘱而默记在心。还可以肯定的是,蚯蚓对于敌对双方、对于默默围观者,永远是异类:收尾句只不过是诗人在反思、内省中的愿景而已。
现在且让我们出离诗歌,反观自身,设想一下倘若我们就在这样的场域之中,将如何进行伦理的抉择。这首诗的阅读者,包括正在看此文的你,当然不会把自己划入“他们”的阵营,进入施暴者行列。那么,第一,假设阅读者觉得,自己不会因“顶撞”而成为被反绑着的人,至多不过是围观者中的一员,有些麻木、冷漠而已。既如此,倘若你就是那个孩子,你将接受还是违抗母亲的叮嘱?设若你已为人父母,又将如何去叮嘱你的孩子?当母亲说“不管什么人盘问你/你都说,我和你们是同一个部分的”,其中的“我”当然不只是指向孩子,也包括她自己:她的母亲当年就是如此叮嘱她的,那也是一个“我”;这个孩子长大后或许也会这样叮嘱自己的孩子,未来的另一个“我”……第二,就算你自居围观者,如果像那个妇人一样被突然从人群——另一个“同一个部分”——中拖拽出来,你将如何反应?你会怎样看待这“被选中”的命运?哭泣,哀求,咒骂,踢打?第三,如果你选择成为被反绑着的人,此刻你将如何决断?吃下蚯蚓以保护无辜的妇人?——你将成为罪犯,和“他们”无异。誓死不从?——你将成为牺牲者。然而,正如你已无数次目睹——如同诗中的母亲——因而可以预知,围观者唏嘘、感叹一番后散去,生活旋即回复常态,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然而“他们”会再次云集,围观者会再度聚拢。但这不是这首诗的抒情重心。诗人告诫我们,“蚯蚓也和我们是同一个部分的”,他希望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蚯蚓,而不是想象成被反绑着的人——如果那样,你看到的将是自己的无辜,你在无辜者中得到庇护并如释重负;如果把自己想象为那条蚯蚓,你就会体悟到,每个人都可能犯下过残酷罪行,不只是“他们”。同样,这个世界不只有被反绑着的人是围观者眼中的不幸者;在被反绑着的人的视域里,包括母亲和她的孩子在内的围观者,蚯蚓,被拖出来的妇人,甚至“他们”,都深陷不幸之中。更迫切地需要我们反省的是,在某一时刻、某一被认为是极其特殊的场景中,“我们”是否就是“他们”的化身?
04
十多年前,我和余笑忠同在商业繁华的汉口上班,两家单位隔着武汉最繁忙的街道之一解放大道。后来单位搬迁新址,我距他也不过三站路。我们各自忙着,很少碰面。偶尔他会叫上我,一同步行去京汉大道一家影碟店挑碟片。更多的时候是外地诗友来汉,朋友们从三镇汇流到一起聚餐。酒桌上的余笑忠豪情万丈,拒绝白酒——可能是怕伤害嗓音,他的职业是电台节目主持——而善饮啤酒。往往不问对方如何,自己先干一大杯为敬。在他仰起脖子之时,早生的华发在灯光下生辉。有一次他突然说,他曾经去染过发。见我们有些不相信,他解释道,那一次是因为父亲要从乡下来看他,他不能让黑发的父亲看到白发的儿子。2013年10月,余笑忠的父亲因意外事故而去世。三年后,他在酒桌上提及染发的故事——我在手机备忘录上记下它,时在2016年12月9日。那时的他是在回忆。他依然平静如水,如同他写下的一行行诗。但很难想象他在经历丧亲之痛时,如何抑制住悲恸和颤抖,而不让泪水将诗稿濡湿,模糊了文字。父亲去世后的第四日,余笑忠写下一首《祭父辞》:
……
你与自己的老迈之躯作对
纵然道路平坦。在格外平坦的路上
你的电动三轮车突然冲下河堤
没有人知道,你那把老骨头撞向何物
闻声赶来的堂弟将你抱在怀里,你说
“这回我死定了,儿”
你为自己的意外之死感到羞愧
你要借自嘲给老迈之躯挽回
最后的颜面
父啊,再也没有令我欣悦的清晨了
我羞于将这些无力的喃喃自语
罗列成诗行。我宁愿
是我把你抱在怀里,哪怕
不得不听你说最后的那句话
“这回我死定了,儿”——你以临终的平静
阻止我们夸大你的不幸
我宁愿是被你捎带着的那个小女孩
她和你一同翻滚落地,但拍拍身上的灰土
一溜小跑就赶到了小学,她会一如往日
拿出纸、笔和橡皮擦。这一天
才刚刚开始
即使迎面遭逢如此巨大的事变和灾难,对诗人来说,对一首诗而言,除了本分的写实,复现改变父亲也改变家人命运的那一刻的场景,以铭记在心,还能做什么呢?这首悼亡诗同样有转换:“我”宁愿转换成那个搭便车的小女孩,一路与父亲说说笑笑。诗人的视线由此转向小女孩,想象她这一天按部就班、平淡无奇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父亲不再有了。
诗人余笑忠是一位生活在城里的儒雅的乡村知识分子。这样称呼他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来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写作具有知识分子气息。与这一代诗人的经历大致相同,余笑忠出生于乡村的一个普通农家,直至考上大学才离开偏僻县城远赴京城。他的出生地和发蒙地湖北黄冈蕲春县,堪称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出诗人、文艺理论家闻一多、废名、胡风,国学大师黄侃、熊十力,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现代新儒学大家徐复观,哲学家汤用彤、汤一介等。诗人、评论家江雪曾撰文详述余笑忠故乡的文脉和地理:一条长约一百二十公里、发源于大别山深处、汇入长江的蕲河贯穿全境,黄侃故居在上游,胡风故居在中游南岸,闻一多故居则在与蕲河平行的蕲水下游。余笑忠的老家傍依蕲河中游,他被江雪称为“蕲河之子”、“蕲河诗人”(《风骨与凝神:当代汉语个体诗学的锻造——余笑忠论》)。这一代人生逢其时,在1980年代自由、开放、宽容的大学校园里学习、成长,受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而开始习诗,毕业后工作在异地。异乡人或浪荡子是这一代诗人的情结,就像同城而居的诗人张执浩为诗人雷平阳写下的诗句,“你还有故乡,而我只剩下故居”。在这些与余笑忠交集密切的诗人纷纷走过人生的中途,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后,在文字的世界里,张执浩重返养育了他的仙女山、岩子河,剑男不知疲倦地书写鄂东南的幕阜山,沉河在江汉平原一砖一石地建设“守界园”。更为年轻的诗人谈骁,则像他诗中的那一颗从恩施高山上滚落下来的土豆,一头扎进都市的灯红酒绿,孤寂难掩。这些诗人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也都有丰富的阅读和写作经验,单把余笑忠称为“知识分子”,不是指他的写作是书斋式的,也不是要把他与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相提并论,尽管他与后者有不少相近之处,而是来自对他的写作方式、文本构成的整体感知,亦即:面对日常生活,他是一位严肃、严正的,有着个人鲜明伦理抉择的诗人;这同时意味着,他有自己的语言伦理操守,正如夏可君使用“写作的尊严”、“诗性的正义”的说法,诗人、翻译家李以亮谈及诗人的悲悯、谦卑与爱,诗人、评论家夏宏、江雪用“沉默诗学”来概括。众多诗人、评论家、读者注意到余笑忠对灾变的关注与书写,如《悼沙兰逝去的孩子们》(2005年)、《中国病人》(2010年)等,并有诸多评论。我们可以举一首他的近作:
没有哪一团火自愿蛰伏
接近瀑布的水流加快了速度
瀑布之下,深潭中
有人向你游来
手上擎着火把
火,要么让人失去藏身之地
要么像一颗失效的药丸
你知道,擎着火把的人
奄奄一息
而你逃离之快像全速接力 (《不安》,2020年)
这里没有“我”而有“你”,但这个“你”却是每一个在逃离之后深感不安的“我”。这里没有“绝对的写实”而宛若梦境,无数个“你”正“从长痛中醒来”——余笑忠一首诗的标题——但并未失去其尖锐的日常性。加缪在谈到写实主义时说,“全世界都是写实派。但没有人真的是。原来重要的不是美感,而是内在的态度”(《加缪手记》)。这种“内在的态度”无法与写作者的伦理立场相剥离。在《不安》中,诗人决不是指责逃离的他人,而是忏悔自己在瀑布雷鸣般的压迫声中的怯懦。“从梦中醒来的人/不得不双手掩面,一如罪人/如此真切……”(余笑忠《梦醒后——仿佩索阿》,2017年)当然,并非只是在书写灾变之时才会让人感知到诗中伦理的存在,灾变只是让习焉不察的日常伦理变得异常严峻。
至于“沉默诗学”,可用加缪手记里的话来解释:“真正的艺术是说得最少的。”在加缪看来,沉默与发声并无矛盾。沉默是对话:“因为沉默总是笼罩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和自己对话,替自己说话;和别人说话,为别人说话。我们不只是在面对沉默时这么做,而且是为了表达那种沉默”(见罗伯特•泽拉塔斯基《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余笑忠的诗自然不是对加缪言论的诗意图解,但它们确实常常在对话中沉默,在沉默中对话:
所有亮着的灯都在制造谎言
但你不会说谎,所有暗自
流下的泪水,不会
所有亮着的灯都是赤裸的
我要你亮着,赤裸着
我也必须赤裸着,赤裸着
我们如此孤独。在隐语和行话中
我们愈加孤独。比如沙漠中的海盗
比如失明者眼中
最后的微光
(《“深邃而普遍的黑暗”》,2011年)
如你所见,当“我”与“你”同时出现在诗中,两者在对话;“我”、“你”与“暗自流下的泪水”也在对话;“我”也在与自己对话(“我也必须赤裸着,赤裸着”);“我们”——孤独者和沉默者(被隐喻和行话排斥在外的人)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也暗含对话。“失明者”则让我们想起诗人观察和书写过的盲女,也很可能指涉的是他所熟悉的诗人、作家博尔赫斯,那个晚年双目逐渐失明的人,那个如痴如醉地与时间、历史对话的睿智老人。
最近几年的写作中,若说余笑忠的变化,是他的诗盘桓于动物与植物,发散出寓言意味。如同他邀请我们乘船顺着蕲河逆流而上,他的写作似乎也在汹涌澎湃的诗歌长河中,逆水行舟,回跃到原点:诗人的童年,诗的童年。在那时在那里,我们的眼睛明亮如炬,我们的耳朵灵敏尖细,葆有对繁复、神秘世界永无止息的惊奇,以及对宇宙这个庞然大物的凝神注视。人生的“最后一课”将会以复习我们最早学会的那些单词而结束:
一位诗人的老母亲,中风后
把她的拐杖叫做针
与其说,她的语言能力
退回到婴儿期,不如说
世界在她眼中
变得很小很小了
所有的逆来顺受
不过是磨成了一根针
而我们轻信的语言
像气球那样被一一戳破
再没有什么
比这更称得上是
一针见血 (《最后一课》,2019年)
原刊于《上海文化》2021年9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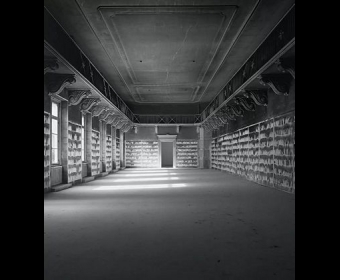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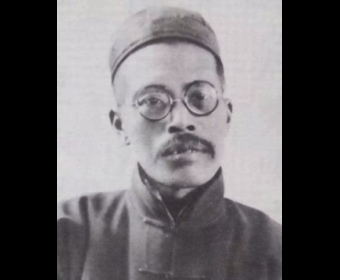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