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锐 1952年生,北京人,艺术家。1979年参与发起“星星美展”,而其被看做中国当代艺术之发端。1984年,黄锐移居日本。2002年,黄锐进驻北京798工厂,主张利用厂房发展艺术空间,他多年来持续策划各种展览及艺术节活动
黄锐 798就是我最大的作品
上一次和黄锐隔桌对坐聊天,还是在2007年。彼时他正与798艺术区的物业对峙,每天爆出各种剑拔弩张的新闻,或是搞一些奇怪的行为艺术,以示抗争。在当时的住所里,黄锐只是疲惫地喝着茶。那年年底,798被列入政府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今天,黄锐搬进另一个空间,同样的长桌、清茶,但黄锐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
不是有钱,是生活方式
为什么现在我会觉得,像798这样的艺术区应该再多来几个?因为按人口比例算,北京有足够的承载量。
老北京人都会记得,解放军刚进城时,城里人口才120多万。后来大量政府机关从外地迁来,人也越来越多,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了400多万人。我记得小时候南城一带有几十家剧场,我家附近有个人民剧场,是梅兰芳的场子,他的剧团有将近100个人。还有其他很多剧团,什么四大小生、四大花旦之类,吃艺术饭的人非常多,再加上卖画的齐白石他们,都是几百万人口就可以养活的。父母带我去看梅兰芳的戏,两块钱一张票,50年代两块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去看戏,不是因为有钱,而是需要这种生活方式。
我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是个做皮具的工人。那时候酒仙桥一带只有几个很大的工厂,厂房里热火朝天,厂房外一片荒凉。而我家住在西城区,对北京东北角的印象不过如此。我不会想到将来搞艺术,更难以预见自己与798会有这样深度的关联。
画画,是我从小就有的兴趣,据说我三岁就能在地上画画了,而且画得不错。比如画《三国》,我特别喜欢赵云,还能画张飞和关云长。对于三岁的小孩子,我的画风已经算是成熟,都可以画出人形了。
我六岁开始正式画画。我没上过任何学校,但是现在回忆历史,我是科班出身——为什么呢?过去只有私塾,我的老师谢天民,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我家和谢天民家大概不到200米的距离,谢天民就教他儿子和我画画,所以我是谢天民儿子的同班同学。在谢家,漫长的时间都是在学写字,这是幼儿教育的必修课,我现在觉得国画挺枯燥,当时只能服从。不可否认,这几年的学习对我的基本功影响很大,小时候在名师门下练过,出来就是不一样。
消解革命,游戏的筹码
我到十岁的时候,学习就中断了。没什么特殊的,那一代人的命运都这样,无法逃避地经历大跃进、“文革”等等所有的政治运动。对于青少年,这是一种理想的破坏和重建过程。我曾经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三好学生,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见过四次毛泽东。
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却是第三次见他了。在广场上,我可能是年龄最小的红卫兵,我只有13岁。当时游行队伍走了几十分钟,最后一个节目叫“拥场”,就是小孩子们从广场上“哗”地一下,拥到城楼底下,很近的距离向城楼上的领袖欢呼。以前“拥场”的孩子们要手持鲜花,但是1966年时没有鲜花,因为不合适,革命热情不能是鲜花象征的那种浪漫。于是大家改成手拿“红宝书”。
所有人拥到城楼底下就哭了,不约而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场面。我浑身冰凉,感到一种恐怖。我不可能问周围的人为什么要哭,人家会说,你为什么不哭啊?
这件事给我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变成了运动中一个脱离出来的角色,精神上脱离了。从那一天起我知道,我不可能和别人一样。哭泣不一定是表达爱,小孩子见到爸爸妈妈也不哭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种群体的感染力从何而来,就像看电影,你突然发现自己也在电影里。
后来我做艺术,就利用了很多革命的符号。这是我游戏的筹码,是必须要消解的人生。
印象派传到上海,未到北京
16岁我插队去内蒙古,劳动了六年多,那是又能适应又不能适应的生活。能适应是指可以吃苦,不能适应是指精神贫乏。
刚开始非常困难,知青们完全不懂得生活,半年没有粮食吃,就吃土豆和胡萝卜,我体重变成82斤。后来学聪明点,我们买了一些小猪和小羊,放到农民家里养,然后给农民钱。这样到了第二年,肉就多得吃不完了。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无法排解,我看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书,这些不可能和农民交流。也有性的苦闷,可最苦闷的时候我也不想去抱农村女孩。也有一批人在那个年代逃避现实或者超越现实,包括一些诗人,郭路生、北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诗歌的进步比较早,当时有内部图书,已经翻译了聂鲁达、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的作品,诗歌的形式感,相对而言更适应革命年代。
任何文化的发生,都需要环境的刺激。我重新捡起画画这个工具,大约是在1969年到1971年的时候,我被派去画革命宣传画。我在1979年,开始接触到西方艺术。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毕加索死掉了,但我不知道毕加索是谁。
印象派已经传到上海,可是传不到北京,因为被徐悲鸿他们挡掉了。后来我还是通过日本传过来的一些画册,才看到塞尚、毕加索。 全国旅行,离不开北京
1979年我们一帮人做了“星星美展”,紧接着1980年又举办了第二届。“星星”是最彻底的艺术运动,也是事实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发端,但是今天的主流声音已经不再提起。其实当年“星星”游行的时候,我在所有投票的人里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但我最后又去参加游行了。因为我是“星星”的召集者,“星星”又是游行事件的理由,是这场博弈中最重要的砝码,我不能不去。我如果不去,其他人的责任就太大了。
我这个人是认准了一件事,就会负责到底,因为我知道做事的底线,知道自己可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我在广场上贴了一首诗叫《人民的悼念》,结果被抓进去,关在工厂里的一间单人牢房。没有进正式的监狱,这算是比较幸运,关了四个月,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给放出来了。
“四人帮”倒台后,我也获得平反。我从此找到了信心:不就是蹲监狱吗,蹲一会儿就出来了,有什么可怕的?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二十来岁,就去全国旅行。我走了二十多个城市,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北京。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味道,但我离不开家乡。
孤独也是一种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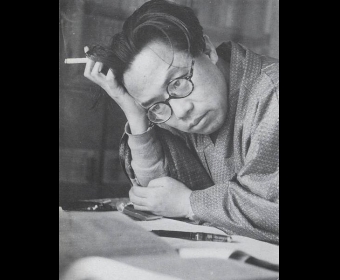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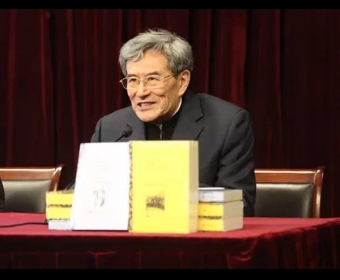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