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脸多么荣耀,和火焰有共同的王冠……”①
——池凌云试论
西渡
1
池凌云是一个孤独的诗人,更准确地说,池凌云是一个具有悲剧气质的诗人。这一气质概而言之就是在一个失爱的世界上和一个失爱的的环境里,坚持对爱和希望的言说。这一言说把她和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女诗人联系在一起,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德格朗、狄金森,还有更遥远的萨福。在一种精神天文学的视野下,她们属于同一明亮的星系。寂静,高贵,遥远地发光……池凌云的写作一直在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中进行。她生活在一个远离诗歌中心的小城,和外界迹近隔绝。这种状态决定了她的写作很少受到关注。她的写作已经持续了二十五年,但除了本地的一两个诗人和评论家曾偶一道及外,她在诗坛至今还是一个道地的外省陌生人。而与她同时开始写作的多数女诗人,早已名动天下,获得了各种真诚或逢场作戏的赞赏。很多诗人的成就落后于他们的名声,而对于池凌云,其名声远远落后于她的成就。对于一个内心不够强大、对诗歌缺乏真正信仰的诗人,持续数十年的这种状态足以扼杀其诗歌热情,并伤害到其诗歌才能的表现,至少也会对所谓诗坛感到心灰意冷。但对于池凌云,这一状态反而成为其诗歌独立性和独特性的保障,使其免受各种流行病毒的感染和侵害。她只管在孤寂中按照其本性指引的方向成长,诗艺和心灵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最近出版的《池凌云诗选》,把这种成长的高度连同其难度一起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惊讶于这本诗集所显示的诗人心灵和诗艺的成熟、丰富,而深感到诗坛的势利、冷漠、自以为是的愚蠢所造成的那种忽视的不可原宥。这个愚蠢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一份。2006年底我和诗人曾有一面之缘,并得诗人以她的诗集《一个人的对话》相赠,但我对这本诗集只在旅途中随便翻了翻,就束之高阁了。我的愚蠢和粗疏差点让我和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永远错过。
池凌云的成长过程与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以及瑞典女诗人安娜·吕德斯泰德有诸多类似之处。把她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她们共同的精湛诗艺以及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而且是一种精神的状态。在她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植物性的坚韧,就像一颗顽强的树的种子,在随便哪一处有泥土的地方扎下根来,然后就不再移动,而不断向着深处汲取营养,供给自己的成长。环境的贫瘠和严酷不单没能阻止她们的成长,相反她们用女性的坚韧、善良和爱改造了她们所置身的环境,把它转化为生命和诗的土壤。在这一过程中,诗的甘美的果实被创造出来——但人们在品尝这一果实的时候,却很少想到诗人成长的艰辛孤独,创造的烦恼焦虑,以及无数个日夜的心无旁骛、殚精竭虑。她们的歌声是从像植物那样倾向于沉默和寂静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而那棵树在悬崖上/琴弦寂静无声,一端在崖壁/一端伸向高耸的天空”(池凌云《醉了的小提琴手》)。她们也许不够广阔,缺少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但她们的自由就体现在她们深深的扎根和沉默的成长中,她们的深邃足以弥补她们在广度上的欠缺,如果非要说这一植物性的生命状态有所欠缺的话。她们的生命体现了真正的树的灵魂:“我们可能在一天之中失去全部果实,/但不会失去更多。/因为要一棵树在一天之内倒下是困难的,/除非那不是一棵真正的树。”(池凌云《真正的树》)这是一种有根的生命状态,相应的,其写作也是一种有根的写作。而充斥诗坛的是另一种广告牌式的诗人——从这种无根的写作中绝不可能结出真正的诗的果实。在她们的诗中,有一种“小人物”的真挚,而完全摒弃了“大人物”的虚伪、做作、自以为是。她们写诗,就像植物的开花、结果一样自然、谦卑,诗作飘溢着真正的花的香味,拥有大自然所奉献的果实的甘甜:“活着的愿望是一朵最小的野菊/爱得深沉,却沉默寡言”(池凌云《一只死去的雏鸟可以再次回来》)。满溢其诗作中的力量,用瑞典诗歌评论家扬·乌拉夫·于连评论安娜·吕德斯泰德的话说,也正是一种植物性的“卑贱的力量”:它具有一种“单纯的美和丰富性”,体现了“坚忍不拔的生命的非凡奇迹”。①
2
池凌云出生在浙江省瑞安县一个贫苦的乡村教师家庭,姐弟四人。因为贫困,她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断学业;也因为贫困,父母在她十五岁那年就为她定了亲(有限的聘金用于清偿家庭积欠的债务),这一婚约在她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抗争之后才得以解除。离开学校后,她当过代课教师、工厂女工,期间开始诗歌写作。池凌云的诗歌就在这一艰苦的生存斗争中,伴随她一同成长。对她而言,诗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的力量,帮助她战胜无所不在的苦难,并使她在黯淡的现实中看见未来。她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投入这一工作,并以同样的姿态欣悦于它的收获。对池凌云来说,为诗歌而工作,也就是为人生而工作;真正使灵魂感到欣悦的是她本身为诗歌所作的奉献,而不是那些不可靠的、短暂的奖赏,名声、地位、不朽的幻觉(而那些忘记这一点的诗人,总是不停地向诗歌榨取,把诗歌变成一架特殊提款机)。
在池凌云的诗歌历程中,2004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她的诗歌写作在这一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爆发。也是直到这一年,她个人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这一年她三十八岁,她的写作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在这个年龄上,许多诗人的写作已经陷入停滞,但是池凌云的诗刚刚开花抽穗——在这个年龄的圪节上开出的花朵自然也就拥有了不同于青春写作的高度和深度。这是一个在地下成长的漫长的故事。写于这一年的85首诗构成了她第二本诗集《一个人的对话》的主体(另外收入前此之作21首)。加上未及收入这本诗集的作品,池凌云这一年的创作量高达近百首。这个数量本身就足够惊人,更重要的是写于这年10月以后的一系列诗作,显示了池凌云诗艺的成熟。在我看来,这些优秀作品至少包括了下列诗作:《分币》、《按摩椅》、《我在傍晚倒退着行走》、《航空杂志》、《阔叶林与针叶林》、《钉子》、《一个人的对话》、《在蛇馆》、《安息日》、《游船》、《赞美》、《留下》(以上五首未见于诗集《一个人的对话》),以及组诗《旧城》(收入《池凌云诗选》时改题《偶然之城》,并增加了诸多新作)的部分作品。在这些诗中,池凌云充分显示了其诗艺的几个突出特点:一是运用想象力对经验加以处理,并赋予其诗意的能力;二是其精微曲折而又亲切动人的语调,这一语调的获得实际上是其心智成熟的表现;三是生动的感受性和精密思维所带来的高超艺术手腕的结合,这个特点在女诗人中并不多见,而为池凌云驰骋诗坛的胜负手。
如何处理经验一直是现代诗人面临的一个难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诗歌如何对时代和当下处境发言。1990年代以来诗歌对叙事性的重视,其目标就在解决这双重的难题。但是在诗歌中引入叙事性,并不意味着经验问题获得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不意味着诗歌就此获得了对当下处境说话的能力,更不意味着经验可以自动地获得“诗意”。1990年代以来,几乎人人都在谈叙事性,谈经验的处理,但真正有能力赋予经验以个人独特性和诗意的诗人仍然寥寥无几。所谓的叙事性诗歌普遍存在两个缺陷:想象力的退化和主体体验的贫乏。池凌云的卓越之处不但在于她所处理的经验总是包含了丰富的感受性和深刻而独特的主体体验,而且在于她总能以生动的想象力对日常经验加以淬炼——想象的自由在她的诗中总是第一位的,某种程度上,经验只是为想象提供了跑道;而当代诗歌中随处可见的却是另一种现象,日常经验纠结的雨林扭断了想象的螺旋桨而导致诗歌机毁人亡——并由此展开对当下处境富于洞察的批评。这方面最早的例子见于2004年10月的《按摩椅》中。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个人关于按摩椅的经验,但却从中写出了富于幻想的人在一个机械时代的悲剧处境,以及诗人对这一处境的尖锐批评——想象力在这一从日常经验过渡到对时代处境洞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一节就写得出手不凡:“是否真的有一双手,从虚无中伸出?/这一次的击打从颈部开始,直抵尾骨/机械的力禁锢了双脚/患有幻想症的人,你想去哪里?”第一行的疑问语气和“虚无”一词,起着化实为虚的作用,为接下来想象力的滑翔搭好了梯子,第三行“机械的力禁锢了双脚”正是从这梯子的顶端纵身一跃,而达到了对当代处境的洞察。第二节首两句承上一节而来:“你想再跑一千米,再爬一个山峰/没有人听到你的恳求”。这两句略显稚嫩,但接下来的三行令人刮目相看:“而关节的缝隙正接受黑暗的研磨/它们互相抵抗,挤压/一些尖锐的东西逐渐平坦。”这里的“黑暗”与第一节的“虚无”形成呼应。第三节继续有惊人之笔:“你已承受加倍击打/就要血脉通畅,心无沟壑/你赞许它一次次涌动,起伏/期待它改变在背后操纵的习惯/走出来,与你面对面。”二、三两节的描写直接基于经验,而又被想象的灵光穿透,妙在虚实之间。最后一节平实而有余味:“它有一个秘密的男性名字/它绵长的指力让我好奇/我抚摸它隐藏的手/它伸出来,抓住我的骨头摇晃。”这首诗是池凌云处理日常经验的能力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正如已经指出的,它在个别地方仍保留了诗艺蜕化前的稚嫩痕迹。此后数年间,池凌云处理经验的能力在《航空杂志》、《钉子》、《在蛇馆》、《这是拖着灰发辫的冬天》、《从一座房子到另一座房子》、《往事》、《麻醉术》、《一个针灸的下午》、《今天,谁来给我们讲故事》、《寄信石家庄》、《傍晚送奔奔去小南门》、《与Z说西藏》、《与母亲同行》、《编织品》、《不曾相识》、《蜡像馆》、《那时候我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过去的一天》、《一颗枣核有一千种智慧》、《迷醉心灵自由的麻醉师》、《那一年七夕》、《病中的父亲》,以及组诗《偶然之城》中一些较晚近的作品等一系列诗中日益精湛,而尤以《从一座房子到另一座房子》、《麻醉术》、《一个针灸的下午》、《迷醉心灵自由的麻醉师》等诗为出色,可以说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这些诗的另外一个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们所提供的经验本身的独特性。池凌云在从一个乡村代课教师成长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历程中所获的体验,她的观察的范围,她的心灵的敏感点和敏感度,和一般生活在大都市的诗人相比,本身有其独特的一面,她的人生和她的诗歌的一致性,更张显了池凌云诗歌经验对于当代诗坛的异质性,而扩大了当代诗歌处理经验的范围和深度。这是池凌云对当代诗歌的一个贡献。
相对于处理经验的能力,诗歌声音问题也许是一个考验诗人才能的更为根本的问题。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是诗歌魅力最直接的来源。诗人的独特性、风格的魅力,最终都须以声音的形式呈现出来。就诗的表现而言,韵律就是意义,声音就是思想。语调的丰富而随物赋形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思想和感性的丰富。在池凌云那些最好的诗里,思想总是直接以美妙的声音向我们现身。池凌云诗歌语调的独特、精微、机敏变化在上述处理经验的诗作中已有充分展露,而当它被用于揭示事物秘密的时候,显得尤为动人。事实上,池凌云是少数有能力道及事物秘密的诗人,或者说,她是那种有秘密要告诉而且也有能力告诉我们的诗人。《游船》、《谈论银河让我们变得晦暗》、《到一棵树中去》、《辜负》、《我无语时受到的灼烧比说出来的还多》、《它或她》、《真正的树》、《赞美》、《阔叶林与针叶林》、《流水没有带走光芒》、《谁也不敢在黑暗中独自说话》、《石头比从前更是石头》、《盲》、《在雾中》、《春天的所有安排》、《一无所知》、《卵球,一种态度》、《无尽塔》、《地狱图》、《你日食》、《肃静的门廊》、《灯的皇冠》、《秋天将月亮抹去》、《别的事物》……这是一个众多杰作的系列。在这些令人爱不释手的诗作中,诗人的声音一点点退出,最后留下的是诗歌的声音,亲切地诉说着爱情、生命、大地和宇宙的秘密。在那首写给希姆博尔斯卡的《游船》中,这一声音的魅力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按照巴赫金的说法,语调总是关系到叙述者、叙述对象和听众三个互相联系的因素。在《游船》中,叙述者和听者都是了解生命秘密的诗人,而叙述的对象就是生命和诗歌的秘密。这首诗是在深知事物秘密的知情者之间的对话,声音的节制、微妙而曲尽其妙的变化,加强了这一对话的严肃性、心灵性和神秘性。下面是这首诗的第一节:
如果你事先与整条河流约好
如果斯提克斯河的水通向每一条河流
你坐的船只很小,就像你看见的事物
仅能运载你一人。你停下来
像一个心怀歉意的女神
让水从身边安静地流走
开始两行的虚拟语气,显示了对话的内在性;“河流”由于“斯提克斯”河水的汇入而象征化了,成为生命的表征。诗人是生命的摆渡者,洞悉生命的秘密,但这一秘密属于特殊的、不能公开传授的知识,所以它“仅能运载你一人”。这大概也是诗人“心怀歉意”的原因。但是知悉这一秘密本身足以使生命变得高贵而不可战胜,“像一个女神”。“让水从身边安静地流走”,则是洞悉命运秘密之后的从容态度。“安静”某种程度上正是生命的一个关键词。博尔赫斯说写作的是为了“让时光的流逝使我感到心安”。这话常被视为作家的自谦,其实正是道出了写作的秘密。让时光的流逝使我们感到心安,这是诗的安慰,也是哲学的安慰——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安慰。池凌云说“让水从身边安静地流走”,也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让时光的流逝使我感到心安”,而在语调上更从容,态度上也更为高贵,契合了一个神定气闲的女神的光荣。
要是河流能变得更宽些
你亲近的人在不远处的堤岸上
为你照顾好柔软的外套
没有人能分享你的权利
孤独的亡魂将倾听你
飘在空气中的美妙的告诫。
第二节延续了上一节的虚拟语气。诗人的出场使生命的河道变得广阔而满溢爱的温馨。“你亲近的人”也许是指读者——他是另一个知情者,守护着诗人和诗歌的秘密。诗人和读者总是彼此创造,彼此发现,因而也彼此依赖。没有诗人,固然没有读者;没有读者,也不会有诗人。在共同守护诗歌秘密这一点上,诗人和读者的“亲近”超越了任何血缘和情缘。他们同被诗歌所选择,对诗歌负担着共同的义务和责任。“你的权利”就是诗人的权利,就是诉说和歌唱的权利,也就是把秘密以秘密的方式传授他人的权利。“孤独的亡魂”则是我们大家——在知悉生命的秘密之前,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亡魂,苦于渡不过斯提克斯河去。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当埃涅阿斯在西比尔陪同下来到斯提克斯河边,看到如秋天落叶之数的亡魂拥集在河边等待渡河。西比尔向卡隆出示了金枝,埃涅阿斯以未死之身得以渡到对岸。诗人对亡魂的告诫也许就是关于这金枝的秘密:
告诉他们广阔的前景值得惊奇
多么合适,你所做的一切令人欣喜
我喜欢你白色V领上衣,暗色的短裙
我听到整条河流都在说——
这个女人来到这条河流上,她是多么可爱
两只手握着两片薄薄的船桨
令所有见到的人高兴。
女诗人某种程度上就是手持金枝的西比尔,对于其秘密的知悉使生命的前景变得广阔。“惊奇”是生命的另一个关键词。歌德说,惊奇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它也是诗的境界。生命和世界由此而令人欣喜。“这个女人来到这条河流上,她是多么可爱/两只手握着两片薄薄的船桨/令所有见到的人高兴”——这微妙的言辞,除了加以复述,我想不出其他赞美的方式。这是河流在说话,也是生命本身在说话。这声音之精微已非人间所有,而只能来自一个洞晓人世秘密的“女神”。此诗原来的副题为“题希姆博尔斯卡的一帧照片”,那么诗中写到的种种场景,皆出于诗人的想象,由此更见诗人心灵的穿透力和处理题材的老道。这委实令人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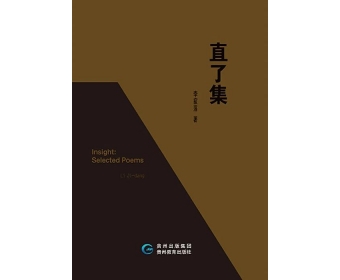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