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政变的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编印了中国第一本非官方的铅印的诗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这个主要是万夏的功劳。万夏是一个超级行动派,从计划夺权开始,他就想好了要编印刊物,一开始叫《现代主义同盟》,这个刊名太吓人了,没有通过,只好委屈成《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尽管是如此低调的一个名字,但它一定是八十年代前半段中国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首先它是铅印的,铅印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出身正派高贵的标志,在正式出版的期刊以外非常稀罕少见;第二,它的编辑眼光是全国的,现代的,它的作者不限于四川,而是全国各地,一半以上是当时中国最有名最活跃的诗人,包括北岛那一拨。在编排上,第一辑名“亚洲铜”,主要是一部分史诗概念的作品,海子打头;第二辑名“结束与开始”,这部分主要是朦胧诗那拨人,这个名字也是北岛的一首诗的名字;第三辑就是“第三代人”,主要是我们这一拨,也包括在其他地方的同路人。这个编排可以看出万夏的眼光、抱负和谋略,他一下子就把“第三代人”提到了中国诗歌的最前沿,让这个名词堂堂皇皇的进入了中国当代诗歌史。1985年春夏之交,《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印出来后,万夏立即带着它们北上南下,周游全国,相当于作了最大程度的推广和传播。可以说,八十年代的现代诗歌运动,就这样发端于成都,并极大的影响到了全国。
到此时为止,早期的,或者说我称之为原教旨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有四个节点:1982年10月重庆西师的聚会,首次有了“第三代人”这个提法;一个月后的南充聚会,这次聚会的成果没有落地,什么也没留下;1983年春夏成立的“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结果是编印了中国第一本“第三代人”诗刊;最后就是1985年春夏出来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让“第三代人”这个名词传播到全国,并得到了诗歌界广泛的认同。机缘巧合,我是唯一一个这四个节点都在场的人,但我都不是主导者,而只是主要参与者。到此时为止,“第三代人“都还只是一个代际概念,没有任何诗歌观念或诗歌美学的东西。传说中的郭绍才那份宣言,我至今没有看到,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力。北望到是在我们那本《第三代人》开篇,写了一个”第三代人“宣言,但他是从政治和社会意义上来阐释这个名词的,和诗歌没有任何关系。《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里“第三代人”专辑,有几句话,也是一个代际概念。现在大家熟知的,关于“第三代人”反诗歌、反文化和反理性的诗歌观念和先锋姿态,都是1986年以后才贴上去的标签。今天的诗歌史已经完全认同和接受了这个概念,用“第三代人”或“第三代诗人”,来泛指朦胧诗以后的一代诗人。而这一代诗人,天才辈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中坚力量。我个人认为,现代汉语诗歌也是在我们这一代诗人手里,才真正成熟起来,已经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文本,形成了强大的诗歌传统。
三,四川五君
放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度,“四川五君”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现象。五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天才,都是那种一个人就可以开出一种方向或者改变一种局面的强力诗人,现在都是汉语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五个人,按年龄来排,是钟鸣、翟永明、柏桦、欧阳江河、张枣。“四川五君”其实只是一种说法,既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个流派,五个人的诗歌风格和美学观念也完全不一样,甚至都不一定有共同的友谊,所以我只能说它是一种现象,一个诗歌智力和品味的共同体。我和他们五个都比较熟悉,先后也有不少交集,对他们每个人专门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今天我就谈一点纯粹是个人的记忆,一些直觉、印象和往事。
四川五君里,我最早见到的是欧阳江河。1982年,我认识了我们川大经济系78级的游小苏,他当时写很纯正的抒情诗,一首《金钟》风靡成都,被称为他们那一拨的“第一小提琴手”。游小苏那儿是一个中心,欧阳江河、以及刚回成都的钟鸣,那时都很推崇他。一次,在游小苏的宿舍里见到了欧阳江河,那时他还叫江河,江河是他的本名,但朦胧诗里有一个更有名的江河,大家就把北京那个叫成大江河,把成都这个叫成小江河。小江河估计后来不能忍受这个“小”字,就把母亲的姓拿过来,叫欧阳江河,所以,欧阳江河是一个笔名。那次和小江河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口才好极,滔滔不绝,很有激情,他走后我问游小苏那是谁,游小苏就说是江河,一个当兵的。我后来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成都诗歌圈的工农兵,工是指孙文波,工人出身;农是指萧开愚,他当过赤脚医生;兵就是欧阳江河,当时是四川省军区的宣传干事。这三人后来都很厉害,孙文波和萧开愚也是成都八十年代诗歌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但不在这些帮派里,属于比较早的个人写作。
钟鸣1982年从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成都的四川师范学院,唐亚平带着我去川师见过他。钟鸣是53年的,和我们年龄差距有点大,但人很热情,不装,有亲和力。钟鸣也是一个行动力和执行力很强的人,他那时正在编一本诗歌民刊《次生林》,作者以游小苏为首,一批五零后出生的诗人,包括江河、柏桦、翟永明、彭逸林等。82年底,唐亚平给我说她和我的诗也会被选进去,我还很是期待。但《次生林》出来后,她和我都不在里面,想来钟鸣还是觉得我们太年轻,和他们有差距。
1983年九月,我们那本《第三代人》出来后,我收到了重庆彭逸林热情洋溢的来信,盛赞我在集子里的长诗《随想》。彭逸林是五零后诗人,我们并不认识,那么,他当时肯定是真喜欢我那首诗,他在信中又热情洋溢的说到柏桦,说我们应该找机会见面。大概是在84年下半年,彭逸林和柏桦来了一次成都,我应该是在江河那儿和他们一起见了。他们那一拨年龄相当,是一个朋友圈,我比他们小很多,在这种聚会里就很边缘。但我那时在学校里风头正盛,心气也很高,倒也没有落寞之感。那一次,柏桦热情洋溢的说到了张枣,还带来了《镜中》的手稿。柏桦是一开始就认定《镜中》是一首了不起的诗,那次聚会里,我记得别的人也觉得《镜中》很好,但应该没有柏桦那种感觉。在今天,《镜中》已经成了一个诗歌神话。那次见面后,我成了柏桦诗歌的热爱者,他有一首《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是汉语诗歌里最温情最动人的作品,几年前,音乐人小柯让我推荐一些诗给他朗读,我首先就想起了这首。柏桦还有两句诗:“我迎接过无数夏天/随后全融入悲伤的河流”,我当时也是喜欢得不得了,还把它用作我的一首诗的题记。
1984年,欧阳江河写出了《悬棺》,这是一首了不起的作品,在成都诗歌圈很轰动,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分水岭。之前他的诗歌,很精致,也很雕作,像一个精美的玻璃器皿,没有人的温度,了无生气。《悬棺》一下子到了一个炫目的高度,很文化,很哲学,很多人可能会不喜欢,其实我个人也不喜欢,但它很重要,是一个大诗人的写作。喜欢与否,只关乎一个人的趣味和心性,而不关乎作品的价值。江河后来也没有继续写《悬棺》那样的东西,但《悬棺》以后,他就完全打开了,一泻千里,开创出一种欧阳江河式的语言风格和诗歌美学,这需要极高的才智和能力,想模仿都模仿不了。欧阳江河的诗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他是一个语言的炼金士,词语在他手上熠熠生辉,把每个句子武装起来,剑光扑面,王气逼人。欧阳江河九十年代中期去美国,在纽约呆了几年,获得了当代世界最前沿的视野和感受力,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对音乐、电影和当代艺术,也是真正的内行。我总觉得,他干什么都能干得最好。很多诗人都很健谈,但欧阳江河的口才,是太好了,他有一种罕见的能力,像爱尔兰诗人希尼说布罗茨基一样,“谈话总是立即获得一种垂直起飞,并且减速是不可能的。”哪怕一些夸张怪诞的说法,都充满灵感和机智,他的敏捷、夸夸其谈和连珠妙语,如果任他发挥,会像雪崩一样覆盖你。我在这方面正好相反,无可奈何的认同库切的说法:“真实是和沉默、反思、写作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讲话并不是真实的源泉,而只是写作的一个苍白的、临时的版本”。2000年开始,我和他都住在北京的望京,相距一千米左右,就经常在一起玩,主要是听音乐和打扑克牌。之前十多年,我们也很熟悉,却没有任何交往。钟鸣和欧阳江河很多年来都不太和谐,但钟鸣是我开车的师傅,他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教会了我开车,而欧阳江河把我带进了古典音乐,特别是硬件。我现在的两套音响器材,一套是直接从他那儿接手的,一套是在他的影响下买的。
我觉得江河是一个真正先锋的诗人,他的写作,完全摒弃了汉语诗学里所有的范畴和观念,比如意象、情景、言志、境界等等。江河的句法,和汉语的传统毫无关系,但也不是翻译过来的西方诗歌的句法,好像是他自己生生创造出来的欧阳江河的句法,你甚至都看不出他的来处和方法。最近听他说到鸠摩罗什,说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完全是一个奇异的存在。《金刚经》的语言完全成立,而且影响巨大,一直流传到今天,但它既不同于六朝当时盛行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样式后来也没有得到仿效和发展,在汉语的历史上只此一家。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至少在我的视野里,他是第一个这么说出来的。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江河的诗歌语言。
1985年春天,我写出了小组诗《河》,当时觉得是一种最高级的诗歌美学,有半年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往下写了。秋天,杨黎说有机会出一套诗歌丛书,约我来编一本我这个趣味的。那时,成都整体的诗歌运动已告一个段落,莽汉和整体已经成派了,每个诗人的个体风格已出现。我和杨黎在诗歌方面,一开始就在两个轨道上,不过彼此都还保持了对对方的尊重。杨黎他们肯定不像我,对钟鸣柏桦他们如此看重。出诗歌丛书这个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我却是因为这个缘由,专门去了一次重庆约稿,就住在张枣的宿舍里,他当时在四川外语学院读研究生,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诗歌就是一个江湖,比较活跃的诗人彼此都知道并会引为同道,到了就可以直接拜访,蹲吃蹲住。那几天里,我也专门去了一次北碚,去柏桦在西师的家里拜访他,吃饭,散步,愉快的交流了大半天。
我去张枣那儿时,心气还是很高的。张枣,还有柏桦,都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就是会让一个人特别舒服的,就对他们无比佩服。他们说话都很舒缓,耐心,娓娓而谈那种,都有一种强大的气场,这个气场不会排斥你,反而是把你带进去,让你和他们马上就亲近起来。他们会首先肯定你,说你的好,然后会让你觉得他们更好,自己都觉得有了差距。柏桦常常会有一些尖锐的出奇的表达,你会觉得无比精彩,张枣则像一个漩涡,充满魅力,不知不觉就把你吸进去。钟鸣和欧阳江河就不一样,两人都是铁嘴,雄辩滔滔,但你听完后,当然觉得他们说得很好,甚至也很受启发,但最后他还是他,你还是你。那一次,我和张枣谈到诗歌,谈到了他的《镜中》和《何人斯》,《镜中》当时已经在圈子里很有名了,张枣主要谈《何人斯》,谈这首诗好在哪儿。我现在还记得,张枣对我说,他已经可以写得和叶芝一样好了,但是还写不过艾略特,他说他写不出《四个四重奏》那种诗歌。这一下就把我搞翻了,我们虽然心中都在向大师看齐,却还没敢想和叶芝写得一样好了。关键是张枣这样说的时候,那种诚恳和笃定会让你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你一点都不会有他狂妄自大的感觉,我后来觉得,张枣语言中那种甜的感觉,应该受惠于叶芝那句“把甜美的声音发出来”。也就在那几天里,一个下午,张枣说他晚上就不管我了,他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如果结果是如其所愿,那会改变他的命运。晚上很晚他才回来,满脸喜悦,他说搞定了,一切OK。然后我知道,张枣是和他的一个德国老师约会,谈恋爱,那个晚上可能就决定了未来,他们会结婚,然后一起去德国。不像现在,那个时候能够去欧洲和美国,都是了不得的大好事,似乎一步就踏入了天堂。
我带着对张枣的满心佩服回到成都,当然也成了张枣诗歌的热爱者。我也看到了差距,他的见识、博学、对诗歌的理解和对语言的掌控、以及词与物的融会贯通,都远远在我之上。那年里一次和胡冬聊到,他说比起柏桦,张枣的诗歌不够清晰。这是一种微妙的感觉,只有写诗的人才会有。柏桦和张枣是那时我们最喜欢的汉语诗人,所以会经常谈起。张枣86年一毕业,就结婚出国了,88年回了一次成都,可能是他一生最高光的时候。那一阵我不在,是听钟鸣说的。张枣那时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又有着在德国获得的新视野和新感觉,在成都走路都自带风声,钟鸣和柏桦他们都无比宠着他,陪着他各种疯玩,颓废而高级。
1992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成都那拨先锋诗人,个个都能与时俱进,一头扎进生活中,如鱼得水,过上了一种八十年代时想都想不出来的生活。张枣远在德国,一个叫图宾根的小城,异乡人,生活寂寞,寡淡如水。而张枣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他喜欢热闹,喜欢享乐,喜欢名气和地位,喜欢站在C位,这一切德国都给不了他。诗歌的抱负和成就,在现实生活面前一文不值。张枣是一个天才,但不是圣徒,如果他还留在中国,以他的能量和魅力,他不会比任何人差。九十年代以后,他在德国是非常不开心的,邓翔去德国开会,专门去图宾根看望过他。邓翔回来对我说,他感觉张枣在那边太孤独,整天一个人喝啤酒。我1999年在北京再次见到张枣时,当年的英俊少年已经完全走样了,胖得不成样子。张枣说过,德国害了他。他回国时,有过一天几次进出洗脚城的传说,完全是报复性的享乐,然后又会嘟囔着说,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记得当时我问他,你现在还做白日梦吗?他说当然要做了,要不人怎么能活下去。我们都理解,我说的白日梦是什么意思,就是少年时无边无际的美好的幻想,在这种梦里,一个人可以成为王子,英雄或者神仙,可以邂逅最美的姑娘,可以和自己的梦中情人终成眷属,可以梦想成真。而当时,我们已经人到中年了。我和张枣还有一个间接的交集,1989年我写了一首诗《春秋来信》,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题目,“春秋”既是时间又是空间,既是季节又是朝代,打算将来出诗集时,就用作书名。钟鸣也非常喜欢这个题目,后来就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很棒的随笔。我想,张枣应该没有看到我这首诗,但他一定读过钟鸣的随笔,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题目,后来也写了一首《春秋来信》,他199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时,书名就是《春秋来信》。到我2003年出第一本诗集时,我就向钟鸣抱怨,说他把我的一个好书名搞没了,让他帮我取书名。当时我们正好在一条河的堤岸上,钟鸣遂指着河水说,有了,就叫“逝者如斯”。
诗歌不能拯救生活,生活也摧毁不了诗歌。在德国不开心的张枣,却没有辜负他的天才,写出了现代汉语里最出色的诗歌。张枣的语言天赋,也许是一百年才能出一个的那种,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就说过,中国新诗一百年,前五十年有一个卞之琳,后五十年有一个张枣。他的英年早逝,可以说是当代汉语诗歌最大的损失。
那么多年过去了,柏桦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写的哪批诗歌,还是我的最爱。很多次有人问我,当代中国诗人你最喜欢谁,我都会说是柏桦。最近我知道了柏桦的《表达》写于1981年,那么,他才是当代汉语诗歌最先驱的人物,朦胧诗以后,《表达》应该算是整个第三代诗人的处女作,有独特的语感,文本完全成立,我喜欢的邓翔,也要在82年才写出那些美妙的诗歌,而现在公认的第三代人处女作,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写于1983年。顺便说一下,我们的第三代人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时候,至少钟鸣、柏桦和欧阳江河,是不认可他们是第三代人的,可能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瞎折腾,毕竟年龄也差了一大截,他们当时在诗歌上,肯定是不屑与我们为伍。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戏称他们是二点五代。不过在今天,我想他们都会乐于认领“第三代代表性诗人”这一冠冕。
柏桦身上有很多迷人的怪癖,我们以前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柏桦又在搞怪癖了。我想,柏桦很清楚他的这些怪癖,也知道它们的迷人之处,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能搞倒好多人。当柏桦把他的这种怪癖有节制的用在诗歌上时,他的诗歌就有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品质,那些看似随意,漫不经心的句子,却总是那么锐利,出其不意,直击人心。柏桦在广州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巧的是我86年毕业也分配到同一个单位,不过之前他就调走了,那一年九月,他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去了成都。可能重庆那几年家庭生活的束缚,柏桦到成都就完全放飞了,脑子里各种奇思异想,万念奔腾,过着一种激情、任性、虚幻、颓废的生活。柏桦的英雄是波德莱尔,他把成都当作在巴黎了,游荡在大街小巷,目空一切,只是看云,挥霍词语,梦想着贵妇。受欧洲文学生活的影响,柏桦有一种很深的贵妇情结,那些年他的白日梦里,一定有很多热爱诗歌的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转世到当下。现实生活中,他身边也围着一帮人,像郑单衣、孙文波、潘家柱、付维等,和他一起发疯和任性。我觉得那一年其实是柏桦身心最为舒展的时期,他的怪癖和个性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代价是一年后,他就被川大劝退了,然后流落到美丽的南京,用他的疯狂和怪癖,又搞倒了好多江南的诗人。就在那几年里,有一次,柏桦很认真的对我说,我们邀约几个诗人,去一个美丽的乡村做小学教师,过另外一种生活。他大概是想到晏阳初的乡村教育了,我也还很认真的想了一阵子,觉得桃花源似乎可期,不过他那儿就没下文了。他当时要是真走出这一步,我多半会跟进,我们年轻时对生活和社会毫无认识,也无所畏惧,觉得怎么都可以,只要能任性自由就行。
我喜欢的柏桦的诗歌,基本上都是他那几年里写的。那些诗歌,自行构建了一个疏朗清澈的世界,天高地远,又有此世的温度和呼吸,它会把你带进去,让你感觉到语言的奇妙、美和危险,好的诗歌都应该有这样的品质。柏桦被称为中国最好的抒情诗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诗歌里,看不到文化反思,看不到当下批判,看不到复杂人性,甚至也看不到一种悲悯心和精神性,但就是好,一种肉身、心灵、感觉的直接抒发,一种词语的魔术,呈现了汉语纤细极端的质地,以前没有那样的抒情诗,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柏桦只会有一个。柏桦近十几年的诗歌,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我有点看不明白。这绝不仅仅是求新,我觉得他还是刻意在玩一种怪癖:老子就这样写,随你怎么看。这样做其实需要一种很深的底气,一种满不在乎,一种大无畏,直接与绝对精神连接,也是一种英雄气概。他和张枣有真正的惺惺相惜,彼此视作俊友,他觉得张枣才是他真正的知音,那么张枣故去后,他怎么写,我们怎么看,都无所谓了。诗歌以外,柏桦写了一本出色的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有点自传性。这本书要当成诗一样读,不要在乎他的观点和结论,只看心灵和词语的过程,看它的语感,会让你获得美好的阅读经验。一本书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了不起了。“左边”也是柏桦的怪癖之一,他多次说过,他少年时的梦想是做毛泽东的秘书,这个也同他的贵妇情结一样,属于他的白日梦。柏桦的“左边”,是诗学的而不是政治的,是激情、浪漫、先锋、叛逆、飞翔、狂想,是一种身姿和做派,词语的狂欢,口腔的快感。如果真关乎政治,我记得西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年轻时不是左派,说明他没良知,一个人成年后还是左派,说明他没头脑。我深以为然。
九十年代中期,柏桦再次回到成都,一直在天上飞的鸟儿,终于落到地上。他当时没有工作,却要承担生活,负起责任,必须开始学习卑微和辛劳了。当时,成都那拨诗人,像万夏、李亚伟、马松等,好多都做了书商,而且很成功。柏桦就为他们做稿子,主要是为马松做,拿固定稿酬。这些书都是畅销书,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毫无价值。一般人如为生计计,可以去做,但绝不会署自己的名字。但柏桦不一样,他至少做了上百种这种垃圾书,都署名“柏桦”,这其实有点惊世骇俗的,现在看来也是英雄做派,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怪癖的结果。柏桦最终没有在体制外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付不起自由的代价,2000年以后,他去西南交通大学做老师,重新进入体制内,现在成了“柏桦教授”,还入了作协,在成都市作协做副主席。他的诗歌还一如既往的怪癖,但在生活中应该是完全正常了,正常得和每个人一样。他重新进入大学时,我还很心疼地想过,一个绝世天才,在九十年代被生活胁迫,现在又要被大学的体制胁迫,看来是我想多了。其实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胁迫我们,这就是命运,生活也终于把他从左边,生生拽回到了右边。
我和钟鸣很早就认识,但深交却要到1988年了,那时,我从重庆离职回到成都,在成都漂着。钟鸣有大哥风范,热情包容,行动力强,乐于助人,生活有品味和要求。八十年代末期,我的生活一片迷茫和绝望,钟鸣常常在他的房子里,搞一些小聚会,他有一个一套二的宿舍,应该是单位——四川工人日报——分给他的。每次当然会约上几个姑娘,在物质主义还没起来时,成都的美女很喜欢同诗人和艺术家一起玩。钟鸣每次都会去锦江宾馆,当时成都唯一的五星级酒店,买一些西式糕点,还有鲜花和红酒,音乐当然是有的,这种聚会都是温情脉脉,恍惚迷离的。也是在那一阵,我们提出了“在颓废中反颓废,在腐朽中反腐朽”的口号,让这种生活有了高大上的精神性。
钟鸣在八十年代初就编过一本诗刊《次生林》,虽然也是打印的,但制作得很精致,板式、装订都很考究,在诗歌圈有一定影响力,可惜也是只出了一期,这也是那个时代民刊的命运,基本上第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89年10月,他来找我一起再办诗歌民刊,还有向以鲜和陈子弘。向以鲜贡献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象罔”,典出庄子,大意是皇帝游赤水之北,遗失了玄珠,他先后派最聪慧的人,最明察的人,最善辩的人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派“象罔‘去找,就找到了。“象罔”其实就是无所用心,就是无。后来读《金刚经》,里面一句“无所用而生其心”,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六祖惠能也是听到这句话开悟的。钟鸣觉得我们都应该做象罔,不要耍小聪明,不要呈机智,而要直驱本质。这是大智慧,当然是对的。不过,钟鸣最后自己成了聪慧、明察、善辩的集合体,我对他有一点小腹诽,觉得他太用心了,不够悟空,也就是不够象罔。
那个时候已经有电脑了,钟鸣是技术和机械的高手,视觉美学的行家。他那时狂爱比亚兹莱——十九世纪末英国最伟大的插画艺术家——以及他做美编的《黄皮书》,应该在那儿采了不少气。我们这个《象罔》,钟鸣先用电脑打出来,比铅印还干净和漂亮,钟鸣又会找一些木刻、线描或者图片,做装帧和插图,然后复印出来,再装订。我们看到后都呆了,单形式就是美轮美奂,让人爱不释手。钟鸣自己有电脑,可以随时操作,唯一的问题是,那个时候复印很贵,他的财力每期最多只能印到十几本。但有个好处,只要有钱,随时都可以印制,可以无限的再生。我知道钟鸣的一些朋友,比如画家何多苓,就经常赞助他。两年多的时间里,《象罔》总共出了二十几期,我觉得是诗歌民刊中品质最好,期数也最多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第二期《庞德专辑》,和随后的肖全摄影专辑《我们这一代人啊》。《庞德专辑》是我从庞德的一本画传里编译出来的,应该是之前去北京时,在西川那儿复印的原文。图片经过不断复印,细节都消失了,只剩下苍凉坚实的线条和轮廓,以及粗旷的颗粒感,显得更沧桑、饱满、厚重。我听说有些诗人还把专辑里的庞德照片,单独复印出来装好框,放在自己的书桌上。肖全虽然那时已在有意识的拍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的肖像了——钟鸣说是在他的指导和安排下,这应该是真实的,我回成都不久,钟鸣就能带我去见肖全,让他为我拍照——但他后来坦承,他是看到《庞德专辑》里的一张照片时,如遭电击,遂下决心要记录历史,为一代人存照。那张照片是年迈的庞德在威尼斯,柱着一根手杖,仿佛还在和世界对峙,眼光深邃、坚硬而沧桑。照片下面配了两行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肖全那个专辑,就是他后来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雏形,名字是钟鸣取的。一年后,肖全拿着他这本专辑,赢得了三毛的信任,在一个下午为三毛拍了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批照片。所以说,肖全的事业也是从《象罔》开始的。《象罔》以特别的观念、材质和方式,以每期区区不到二十本的数量,在诗歌圈内外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在制作和传播上,都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很值得专门研究。
钟鸣在他报社宿舍附近,还有一个一室的小公寓,他会无偿给一些有需求的朋友临时住住。1989年底开始,我曾在那儿住了几个月,之前是翟永明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十几年前我在丽江有一个小院,一次麦家过来小住,我们聊起文学,他说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博尔赫斯,而他最早读到的博尔赫斯,是在钟鸣那个小公寓里看到的两三页手稿。这么一交流下来,才知道我搬离钟鸣那个公寓后,麦家又住了进去。他看到的那几页手稿,就是我为第一期《象罔》翻译的,文章很短,也就一千多字,题目是《隐秘的岛屿》,原文还是从西川那儿复印的。西川后来把整本书翻译出版了,就是那本《博尔赫斯八十忆旧》,我译的其实是博尔赫斯的一小段谈话。
四川五君里,张枣最早熟,钟鸣却是大器晚成。除了年轻时人人都有的生活的小颓废,钟鸣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不会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把时间耗在酒桌上和牌桌上,或者无谓的社交上。中国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钟鸣却是把有涯之生,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内心有着坚定的目标,一旦开始一件事,就会倾情投入。从他开始做古物收藏算起,二十多年来,他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用在各种文物的学习、鉴定、研究上,即便这样,他用在文学和诗歌上的时间,还是比我们所有人都多。他因为做收藏而研究上古史,不止一次说过,他以后的大成就是在上古史的研究上,他要改写中国的上古史,至于文学和诗歌,只是小技。文物和上古史我是彻底的外行,也没什么兴趣,无法知道他在里面真正的段位,但在文学上他已经是一座大山了。他这样说时,我就会想起杜尚,杜尚说他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他最大的成就是下国际象棋。我们知道杜尚是西方当代艺术的源头性人物,他把一个小便池在展厅里倒放过来,命名为“泉”,就影响了西方艺术一百年。
不过在整个八十年代,钟鸣在成都诗歌圈,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一直到九十年代,他出版了《畜界,人界》,才横空出世,一举奠定了一个大人物的地位。他把中国的古代笔记与类书,18世纪的英国随笔和西方现代主义大师散文,在叙述方式和文体上作了了不起的整合,发展出一种斑驳、绵密、扎实、复杂、深邃的文体,直接把现代汉语的散文,推到了世界级的水平。我觉得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写起,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结束,如果他愿意,甚至也可以永远不结束。博尔赫斯梦想有一种沙之书,没有开始,没有结束,钟鸣的文章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沙子是一粒粒的,是颗状的,钟鸣的文章却像一条线,可以从天上绕到地下,从远古绕到当今,从万物绕到人心,包容万象,绵绵不绝。不少内行推崇他的随笔是汉语头把,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夸张,因为文学像美人,不能这样排名,你自己喜欢就是。我知道敬文东教授,也是一个目空一切的人物,却独独服膺钟鸣,说他“开创了一种过目不忘的文体,而文体是天才的事业”。不像他的随笔,几乎无人质疑,钟鸣的诗歌争议却比较大。其实,有争议是好的,西方哪个大咖说过,所有人都说不好的作品,不一定不好,所有人都说好的作品,一定有问题,一半人说好,一半人说不好的作品,一定是好的。钟鸣的诗歌太复杂,意象、典故和隐喻的密度大,思虑深,反讽涩,布满了各种机关和暗器,按中国的诗学传统,几乎是反诗歌的,在唐朝诗人那里看,有点近似韩愈。中国诗学的正宗,是空灵俊逸,情景交融,人天相汇,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钟鸣是相反的路数,读起来很困难,也很累,好像存心不让你愉悦,我在好多年里,也没有真正读进去。近些年我意识到,钟鸣的诗歌,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你喜欢或不喜欢,它都在那儿,体量巨大,你可以绕开,却不得不正视。他对诗歌有明确的认识,有自己的诗歌伦理,建立了自己的语感,有足够的数量和成熟的完成度,按奥登的标准,是一个当然的大诗人。很多诗人的思想,可能会很深刻,但一般都不系统,钟鸣有成体系的想法,充满反省和批判,足以建立起一套诗歌理论。整个的钟鸣是一个现象,其厚重和深度一眼是看不透的,泛泛的评说会显得很轻浮。他的写作是诚恳的,包括他的复杂也是诚恳的,而不是炫技。有一种诗歌是深入浅出,这肯定是好的,还有一种诗歌是深入深出,也许更好。当下经验的复杂和荒谬,对诗人有着更高的要求,诗歌要重新赢得尊严,诗人必须要付出比本能和直觉更多的东西。同样,现代诗歌对真正的读者,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壮丽的诗歌宫殿,不是谁都能走进去的。
我和翟永明认识得也很早,大概是1984年秋天。她很快就以两个组诗《女人》和《静安庄》,赢得了中国首席女诗人的位置。唐亚平毕业后有一阵,风头也很强劲,有一点与之争锋的意思,但很快小富即安,享受生活去了。不过,我知道柏桦最推崇的女诗人,是上海的陆忆敏。翟永明一直在一个最高级的朋友圈中,渐渐的就成了中国诗歌的女神,像阿赫玛托娃那样。而女神是无法说道的。
他们五个人,张枣去国很久,当他又回来时,已是另外一个时空,八十年代的辉煌不再,他的英年早逝,才把更多的目光吸引过来,现在成一个小小的神话。钟鸣和柏桦一直在成都,生活低调,不事张扬,实力远远大于名气。欧阳江河和翟永明早早到了北京,声名一直高涨,一切都在阳光下,已是显学,我的个人记忆完全微不足道。中国人喜欢比附,我突然想到,用《射雕英雄传》里的五个高手来比附一下。他们的诗歌,柏桦有点像东邪黄药师,空灵邪性;欧阳江河有点像西毒欧阳锋,招招狠辣;钟鸣有点像北丐黄七公,堂堂正正;张枣有点像南帝段王爷,深不可测;那么,以魅力无限的翟永明居中神通王重阳之位,他们四个都不会不服。
成都的诗人,大都有很深重的大师情结,他们五个无一例外,至少还要加上李亚伟、杨黎、宋炜、孙文波、萧开愚以及周伦佑。我想,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肯定都自命大师,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都不做第二人想,一定认为自己才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我现在认为,大师情结是好东西,起码让一个人志存高远,心比天高,与亡灵对话,向历史看齐。禅宗讲,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想当大师的诗人,一般不会和身边的人比,只追慕那些伟大的作品和灵魂,对一个写作者,这无疑是对的。另一方面,想想看诗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诗歌彰显意义与价值,但在具体而日常的生活中,真是没有一点用处,所以奥登说:诗歌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在古代,比如唐朝,诗歌可以是失意人生的慰藉和退处,我们传统里悠久的狂狷传统,足以支撑我们心灵,狷者可以有所不为。但在当下生活里,狂狷就是失败者和神经病,不会得到任何理解与同情。肉体不需要精神性,心灵才需要,如果再不能抚慰一种不朽的冲动,如果不是相信自己能做得最好,我们凭什么要远离尘世的诱惑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坚持写到底呢。但诗人的王者心态,则有点问题,也许就是中国两千年皇权至上的无意识的结果。其实,一个人的语言意识、诗歌美学以及写作目标明确以后,如果带着善意的理解,你会觉得好多人都写得很好,因为他们有你没有的东西;如果只盯着自己的方向,放大自己的个性,就会觉得其他人的都没法看,因为你有着他们没有的东西。汉语如此广阔,需要也容得下足够多的天才为它拓展边界,我们还未写出我们的天堂之诗,地狱之诗,像史蒂文斯所说的,伟大的尘世之诗也还待完成。至于结果,重要吗?我们能否成为新的被人铭记的亡灵,我们其实是无从所知的。布罗茨基说过:万物皆有定数,包括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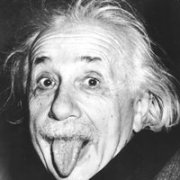 爱因斯坦的绵祆 评论 赵野 | 狂欢与盛筵:1980:值得一读,爽
爱因斯坦的绵祆 评论 赵野 | 狂欢与盛筵:1980:值得一读,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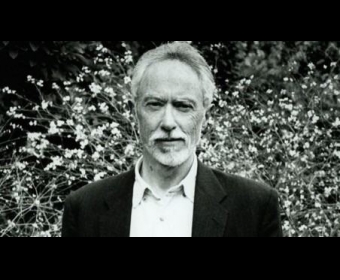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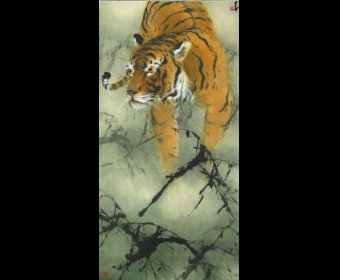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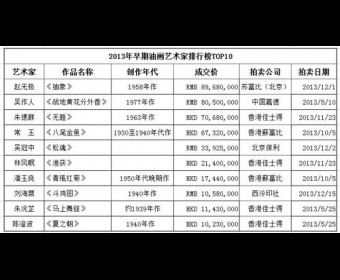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