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莽汉派、整体主义、非非主义
第三代诗人,或者说朦胧诗后的一代诗人中,诗歌成派并且产生大影响的,应该就是“莽汉”、“整体”、“非非”和南京的“他们”,成都四占其三。
1984年春天,胡冬来找我,说他和万夏、李亚伟他们要搞一个“莽汉派”,并给我看了他刚写成的莽汉风格的作品《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我当时是有点不以为然的,觉得不过就是金斯堡《嚎叫》的汉语版。那时,我也正好对青春期的各种疯狂写作感到疲惫了,意识到我应该找一种自己的声音和语感。这个感觉是对的,要早一点这样做更好。因为心性使然,我的方式是回到内心和传统,我太迷恋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了,魏晋风度,唐宋气韵,山水田园,人天合一,我沉浸在古人的心灵和审美里,开始琢磨现代汉语诗歌应该有的句法和气息。年轻意味着勇往直前,也意味着狭隘,认为自己的方向才是方向,别的都是歧途,我要在多年以后才“相信每个方向都能接近真理”。总之,我的狭隘和拘谨让我错失了一首在八十年代堪称伟大的诗歌。1984年,莽汉派一诞生就出了两首神话级的作品,除了胡冬这个,另一个就是李亚伟的《中文系》。《中文系》因其定点打击的摧毁力,流播更为广泛,可能中国所有的中文系里对诗歌略有兴趣的学生都读过。同期马松有一首《灿烂》,尽显柔情,也不断为人称道。万夏和他们一起开创了莽汉派后,很快就转向整体主义,他身上体现的创造力,实在让人惊叹。柏桦说,万夏“整个人的出现就是魔力,风,色彩”,我则一直记得他的两句诗: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这两句诗太好了,有晚明的意味,又很波德莱尔,多年后贾樟柯拍《二十四城》,还用在他的电影里。
莽汉热血豪迈,目空一切,对世界满不在乎,他们用这种态度,消解了青春期的感伤,从而走向成熟。本来年轻诗人最大的问题是伤感和忧郁,但伤感和忧郁恰恰是一个人写诗的理由,写诗的原动力,但是,你只有消解掉你的伤感和忧郁,你才能写出成熟的诗歌。有几种方法:一是天生没有这种东西,如邓翔;一是观念式写作,如杨黎;一是把他们愤怒化,像莽汉这几位;一是建立起自己的语感,这是更多的人走的路。莽汉为中国贡献了四个一流诗人,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在莽汉里坐第五把交椅的二毛,多年后独辟蹊径,以美食诗在一个领域独占鳌头,过了一把老大的瘾。
胡冬八十年代后期去了伦敦,决绝地再也没有回来过。三十多年了,在英语的包围里,他顽强地用汉语写作,其心境和甘苦,难以揣测。2013年我去伦敦,二十多年没见,也没通音讯,胡冬见到我,一个拥抱,就仿佛回到了从前,时间立即消失了。我去他的住处,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屋子里杂乱、随意,还是八十年代成都那种波西米亚调调,他的各种家具,都是从跳蚤市场上买回来的,一个桌子或一把椅子,就一个英镑。他指给我看两百米外的一个小教堂,说当年约翰·多恩在那儿做过十几年的牧师。约翰·多恩是艾略特特别推崇的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那句著名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就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就出自他口。不过,我怎么都觉得胡冬在伦敦就是一座孤岛,唐晓渡一次对我说,胡冬比伦敦人还爱伦敦,比伦敦人还熟悉伦敦,伦敦真的和他有关系吗?我想,胡冬一直是生活在八十年代成都的氛围,和他对伦敦的浪漫主义幻觉中,这种氛围和幻觉已经凝结在时间里,不再与时流动。好在伦敦足够大,足够包容,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在那儿能找到自己的空间。近几年偶尔会看到他的一些新作,已深入到汉语和汉文化的深处,早就不莽汉了。我完全相信,胡冬这三十年的作品如果能集中呈现,一定会让当下汉语诗歌大吃一惊,并自动给他留下一个醒目的位置。
李亚伟是一个才华在头顶上飞着的人,你不经意间抬头就能看到,举手就能触到。他毕业后回老家酉阳做中学老师,我们早就互相知道,却是很晚才见面。大概是1994年,他和万夏到北京做书商,我那时是一个很出风头的杂志《环球青年》的社长,国家级刊物,钟鸣和肖全都是挂名的记者,我就给万夏和李亚伟各办了一个记者证,有钢印那种。从受众这个层面,我觉得李亚伟是成都这拨诗人里影响最大的,很多不那么爱诗歌的人,都会被他的语言折服。有种诗歌是安静的、矜持的,需要你去走近它,李亚伟的诗歌则直接冲进你的身体,带着你狂欢,有音乐般的感染力。他自诩为当代李白,诗歌也有李白的天马行空和狂放不羁,以及一种接地气的人民性。李亚伟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写过好几首格局恢弘,抱负远大的组诗,已经隐隐要开出一种新气象了,然后一头扎进生活,过正常人的日子。他的《中文系》太有名了,也许对他其他作品反而有一些遮盖。差不多十年前,他拿出了一组《河西走廊抒情》,把个人经验融入一种磅礴的历史情感和纵深的地理空间,大气而性感,无疑可列入当代汉语诗歌里最重要的作品。李亚伟诗歌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无论怎么上天入地,都感觉在你周围的生活中,这得力于他独特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李亚伟这两年身体有点小问题,稍显安静。之前听他偶尔说起过,他一直在写一个大东西,能表现中国这三十年的魔幻现实,甚至包括市场经济。我不知道是不是庞德《诗章》那样的作品,但我知道他身体养好后,一定会向中国诗歌扔出一个重磅炸弹。我现在写八十年代,还是李亚伟的一句诗最能表现此时的心境:数来数去,都是想象中的人物。
八十年代成都的诗人,说得上是灿若群星,很难想象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天才一下子涌出来,而在九十年代,应该是92年以后,这些诗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一度中断了写作,义无反顾的投入生活。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命运,生活的重厄压下来时,诗歌首先得退位。诗歌的退位时间和退位程度,每个人不一样,而马松是比较彻底的一个。马松喝酒很莽汉,诗歌却一点都不莽汉,而是写得很优美。很多诗人也写得很优美,但感觉裹得很紧,马松是完全打开的那种优美,像河流流淌一样。马松的语言,自由,自然,和万物亲近,有着一种特别的关系。他诗歌里的比喻,像早晨成熟的果子,还滴着露水,新鲜得让人心动,充满诱惑。周墙在和姑娘谈诗的时候,老用马松作例子。他说马松给一个姑娘讲,我要带你去床上,是色情,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就是诗歌。大多数诗人,一辈子都写不出一个这样的句子。马松只留下几十首短诗,就奠定了一流诗人的地位,进入九十年代后,基本是完全不写作了,对他的诗歌和诗人身份,也毫不在乎,感觉是前世的事。几年前,因为一本书还是一个节目的需要,那一年的每个节气来临前,马松为了宣传或是传播要写一段文字,他用诗的形式,分行写了,大家看了都感觉很惊艳,最后得一组诗,二十四首,对应二十四个节气,朋友们都赞叹说是好诗。也许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不是他写出来的作品,而是他像一个诗人那样思考和活着,像一个诗人那样看待世界和生命。
莽汉是青春的,肉欲的,行动的,当下的,整体主义却是成人的,玄学的,冥想的,古老的。整体主义是84年下半年,由石光华和渠炜发起的。渠炜是两个人,宋渠和宋炜两兄弟,八十年代他们的诗歌只署“渠炜”一个名,九十年代以后,宋渠好像是不写了,宋炜才开始单飞。当年我一直好奇他们的写作方式,一般会认为是共同讨论,分头写作,但宋炜告诉我,他们完全是心意相通,像一个传说。他们往往是一个人开始写完一段或几段后,放在桌上,另外一个人看到了,就继续写下去,如果没写完,第一个又会再继续写下去,那个时候他们喜欢写那种史诗,都比较长。我一直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两兄弟,外貌和性情都大不一样,以后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写出了那些作品。
宋渠宋炜两兄弟是一个奇迹,宋炜同我一样,64年出生,我们两个应该是我们那一拨里年龄最小的,宋渠会大一两岁。两兄弟都没有上大学,却至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写出了洋洋洒洒的史诗,引起诗歌圈的惊叹。首先是北京的大江河,杨炼,倡导写一种史诗,宏大叙事,历史意识,文化民族等等,以一种华丽的词藻铺陈出来,很过瘾,也很炫目,非常引人关注。宋氏兄弟是这个潮流的忠实追随者,我在83年初,也很迷恋这个,我在我们那本《第三代人》里的作品《随想》,就是这种路数,洋洋洒洒两百多行,如水扑来,当时也在大学生诗人里出尽风头。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写法,转向内向的抒情诗,宋氏兄弟则勇往直前,和石光华一起创立了整体主义诗派。
我和宋渠没什么交往,对他一直不了解,这里就只说宋炜。从诗歌上说,宋炜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天才,而且展开得很彻底。我的这段回忆,用了太多次天才这个词,这不是我的问题,实在是成都八十年代的诗人群体太杰出了,仿佛唐朝再现,成都也成了长安,天才扎堆而来,避都避不开,让“天才”这个词都掉价了。宋炜十七八岁时,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们偏居青衣江边一个小县城,远离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城市,诗歌气魄之大,眼界之高,底蕴之深,词语之绚烂,几可以直追历史上任何少年天才诗人。石光华当时也是不可一世的,却在成都留下一句名言:人学万夏,诗学宋炜。宋炜的诗歌,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翻译语体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一点。至少在八十年代后期的诗歌里,宋炜已经有了从容舒缓的气度,混合了书生、乡绅、侠客、酒徒、泼皮、江湖术士、炼丹师、占卜者的形象和气质,因为他懂诗,懂酒,懂易,懂药,懂美食,懂阴阳,懂风水,就后来江湖传言,他那时唯有不懂美人。不懂色,那么,一切都成纸上谈兵,终归是诗人。
石光华是五零后,大宋炜不少,看他如此服膺宋炜,不知道他们是谁影响了谁。整体主义有完整的理论,文章是石光华写的,应该是从易经那儿采的气,构建了一套说法,高屋建瓴,比较玄,就诗学本身来说,谈不上有多少新意,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足以开宗立派,拉起大旗了。整体主义是倡导史诗和回归传统的,史诗都很长,我不知道石光华是否也写史诗,但记得读过他几首短诗,其中一首是《梅花三弄》,我当时觉得太外在了,是用头脑写出来的。84年我也在向传统回归,在往后看,但我认为直接处理古代题材器物,人物事件,都太简单了,传统和古意不是一种符号和标签,我主张传统要化掉——其实就是传统的当下转化,不过当时表达没那么清楚——要深入到你的骨髓,成为你的气息,而好诗,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那时还处于只认为自己的方向才是真理的时期,其实现代诗歌美学,更强调头脑写诗,智力写诗,甚至非如此不足以成为大诗人。
整体主义除了石光华和宋氏兄弟,还有两员大将,在重庆的刘太亨和张渝。刘太亨当时是军人,在第三军医大工作,他为人豪爽幽默,嘴又甜,身边老能拢着很多漂亮的小护士,他的宿舍就成了各路诗人在重庆的据点。我不知道小护士们是否因为他的诗歌,才聚在他身边的,因为他的诗歌都是很长的史诗,甚至是玄学诗,语言深奥,大气磅礴,句子也很长,比宋炜更整体主义,因为宋炜还有很多个人的东西。小护士们应该看不懂他的诗,但也许会因此更崇拜他。我在重庆那一年多的时间,太亨给了我很多关照,我常常往他哪儿跑,但我们从不谈诗。其实,他内心有严格的标准,只有不多的一些诗人能入他的法眼。整体主义当时一定是雄心万丈的,在政治和经济条件都很差的情形下,印出了两期《汉诗——20世纪编年史》,铅印的,装订也很好,看起来像正式出版物,太亨应该对这两本《汉诗》贡献良多。那时办诗歌民刊,除了所有费用要自凑,更重要的是还要担风险,我们叫诗歌民刊,在公安那儿就成了非法出版物,那些主导者,都要被找去喝茶谈话,并在那儿挂上一号,对以后的生活都持续有着不良影响。我迄今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他们都看不懂的诗歌,如此提防这群青草一样无害的诗人。总之当年他们,也可以说是我们,为诗歌的付出真是太多了。刘太亨近年在做一个宏大的诗歌出版工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歌史料》,对八十年代的四川诗歌打个总结。我知道的有“四川五君卷”、“整体主义卷”、“莽汉派卷”、“非非主义卷”、“诸子卷”,最后一卷是那些没有在上述帮派里的诗人,用好听的话来说就是“个人写作”,我、萧开愚、孙文波等,都归在此卷里。还有一本,就是胡亮的《朝霞列传》,八十年代的四川先锋诗歌史。出版这套书,我觉得更多还是太亨的诗歌情结。诗歌尽管无用,但一旦真的进入后,就像吸毒一样,那种美妙完全无法与外人道,布罗茨基也说过同样的意思。我相信不久,就会看到太亨自己新的写作,他也许早就写出来了,什么时候就抛出来,吓我们一跳。
我不知道现在的石光华,诗歌上还有多大的抱负,自从十几年前万夏给他出版了一本《我的川菜生活》,他就一直混美食圈,俨然川菜的主笔秀才和权威,我们要多年后才明白,这是一个多么欢喜的圈子,比诗歌实惠多了。宋炜九十年代下海做了书商,这几乎是八十年代成都那拨诗人的主流出路,万夏、李亚伟、马松、宋炜、刘太亨、石光华、梁乐,都是很成功的书商,我自己在《环球青年》倒闭后,也涉足体验了一把。每次图书订货会,大家在一起都要说,书会开了就开诗会。九十年代做书商,需要脑子话、点子多、想象力丰富,这方面宋炜是高手,一开始他很成功。后来可能是头脑发热,或心志太高,他们全部宋氏四兄弟,在21世纪一开始,就把资金集中起来做了一本《中国美食地理》的杂志。做书与做杂志,用禅宗话来说,似则似,是则不是,表面看差不多,其实完全两回事。这方面我是内行,可惜宋炜当时没有向我咨询。简单说,做书可以是个人行为,做杂志则是一个系统运作。《中国美食地理》这个创意,可以说是超级的好,十年前大火的《舌尖上的中国》,就是这个路数,但宋氏兄弟一则太超前,二则他们是杰出的个人,却玩不转一个系统,艰苦卓绝、惨淡经营几年后,彻底崩盘了。归零的不是别人的投资,而是自己的积累,宋炜却也无所谓,一副纨绔样,喝酒,写诗,谈恋爱,和太亨一起稳坐重庆的诗歌江湖,声色犬马,好像也没缺少什么。其实,古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只要诗歌还在,怎么过都是一生。
几十年来,宋炜罕见地保持了一种独立性和民间性,九十年代后,他远离诗歌圈,不参加诗歌活动,不在杂志上发表,也不出版诗集,像一个古代诗人。一个古代诗人哪儿会有发表和出版呢?马松也是这样,但马松是真的不在乎自己的诗歌和诗人身份,而宋炜的灵魂里,一直住着一个大诗人。我读过他一首短诗,登泰山的,说他在泰山之巅心意涌动,不做第二人想,正是“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在《万物之诗》里,他写道:像我这般,一个天上的人。记得斯大林是这么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住在天上的人。谁如因此嘲笑宋炜自视太高,反而会露出自己的马脚。四川这拨六十年代的诗人,在一起只谈风月,从不谈诗,仿佛一说就俗,然后就是打牌,喝酒,洗脚。好诗人之间当然有认同,但彼此也不怎么读。宋炜的诗我也读得不多,那首《万物之诗》非常好。敬文东特别推崇宋炜的诗歌,认为汉语因之有了不一样的质地。宋炜知道自己的诗歌能力,心中有着诗歌的洁癖,所以不屑与吵吵闹闹,争名夺利的小诗人为伍。我相信他是一个天上的人,就活在汉语里,把自己活成了汉语,活成了诗歌。我不确定人世还需不需要这样的诗歌和诗人,但那是人世的事,不是诗歌的事,也不是诗人的事。宋炜,还有李亚伟们,他们身上的这种豪气,能让诗歌飞起来。他们只要证明,诗是豪杰的事业,小人岂能为之。
莽汉和整体成派折腾的时间都不长,参与的人也不多,就是几个最好的朋友,扯呼一阵后,每个人都转向了个人写作。后起的非非却不一样,他们人数众多,经历过多次内部的裂变,谱系十分复杂,什么前非非,后非非,后后非非等,不深入进去,完全是一头雾水。两个月前在成都,尚仲敏做东约我吃饭,杨黎也在,席上有个很精神的年轻哥们孟原,他们就介绍说他目前在主掌非非。这样看来,非非1986年创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了。一个诗歌流派持续那么久,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一定也有它特别的搞法和道理。
我知道的非非是周伦佑、杨黎和蓝马最早发起的,周伦佑像中军统帅,杨黎是首席诗人,蓝马是首席理论家。蓝马阳刚而儒雅,谦谦君子一个,家在西昌,老在成都活动,在成都诗歌圈也是一个重要人物。86年春天我在西昌实习,他带着十几个兄弟,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接我出去吃饭喝酒,这阵仗把我那些同学吓了一跳。我和周伦佑见面很早,83年秋天,我们那个《第三代人》刚出来。当时周伦佑,廖亦武以及黎正光,正被《星星》诗刊力捧为具有探索精神的青年诗人,有四川诗歌三驾马车的说法,当然这是《星星》的眼光和标准。应该是杨远宏古道热情,居中联络,我们和他们三个聚了一次,我们这边可能还有陈绍陟,以及别的什么人。这次见面其实有点江湖论剑的意思,他们三个都是五零后,年龄名气比我们大,但那时大学生有天然的优势,我们又风头正劲,对他们的官方荣誉也毫不在乎,双方在心态和气势上,是个五五开的局面。记得我谈到了瓦雷里和《海滨墓园》,我应该是特别推崇,说能写出一首《海滨墓园》那样的诗,也算不负此生了。他们三人中不知是谁,可能就是周伦佑,马上接上说,不,不,那远远不够。可见那时他们在诗歌上的野心和抱负,比我大多了。周伦佑有个哥哥叫周伦佐,搞哲学和思想,口才极好,我还请到川大做过演讲。兄弟俩都操普通话,这在成都很另类,是好的那种另类,成都对说普通话的人天然的友好。他们一个诗歌,一个理论,在成都风生水起,很有影响。自万夏杨黎约我发动政变,矛头直指周伦佑后,我已经几十年没和他碰到了,世界很小,江湖却很大。
杨黎也是一个奇迹,一个学商业的中专生,当时好像是在银行工作。记得看他的第一首诗是《冷风景》,客观、冷静,漠然,法国新小说派的路数。《冷风景》写于1984年,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已经出来了,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有点好奇。就是说,我们还在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时期,杨黎一步就踏进后现代主义了,而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得在好几年后才传入中国。我对非非完全不了解,隐隐记得周伦佑有“非崇高”、“非理性”的说法,并把这些标签贴到第三代人身上。但我觉得周伦佑是追求崇高和理性的,所以,他的诗歌应该是非典型的“非非”,杨黎才是典型的“非非”,后来觉得“非非“都跟不上他的先锋脚步了,又发起了极端的废话写作。杨黎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写作,我不知道西方这种写作是什么样子,但西方当代艺术基本上都是这种东西,比如约翰·凯奇的音乐作品《4分33秒》,钢琴家走上舞台,静静坐在一架钢琴前,4分33秒过去后,钢琴家站起来致谢,说已完成演奏。再比如卢西奥·丰塔纳,阿根廷裔的艺术家,他在一块涂满单色油彩的画布上捅上一刀,就完成了一件艺术史上了不起的作品。《4分33秒》被称为一曲绝世经典,丰塔纳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之一,他们的作品,都建立在一个观念上,而这些观念的后面,是哲学。杨黎的写作,走在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前面,他应该在他们那儿找到知音。诗歌一定是有话要说的,杨黎偏偏觉得自己无话可说,遂以一人之力,挑战了整个写作传统,或者说是挑战了诗歌本身,这是他在文学史意义上的最要性。当下中国是一个混杂现代性的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种特点和现象杂糅在一起,很难分得开,所以,仅仅先锋是不够的,一直先锋也不是一种美德。我近年来形成一个观点,面对强大的中国现实,单纯的前现代、现代或后现代,可能都有问题,会流于简单、过气或浅薄,很难形成对等的挑战。最有力量的作品,应该也要具备这种混杂的现代性,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前现代的普世、崇高与启迪,现代的深邃、精神性与形式主义,以及后现代的无所用心与无所顾忌,诗人应该有一种能力,用语言把它们统摄在一起,才能匹配这个现实,表现这个时代。不过,这真的很难,路漫漫其修远兮,等着大家上下求索。
杨黎的废话写作,像杜尚的小便池,让人人都可以做诗人,这让他轻易就收获了大批追随者,自行缔造了一个王国,他也喜欢这种呼风唤雨的感觉,走到那儿都带着一群人。已故的陈超教授生前和我说起,一次杨黎去石家庄约他见面,他到场后看到杨黎身边还有好几个年轻人,一色的黑衣服,整个一个电影里的香港黑社会老大的派头。我有时也戏称杨黎是星宿派教主丁春秋,金庸《天龙八部》里的武林高手。我个人觉得,杨黎的写作当然是成立的,而且非常重要,但观念的东西,只对它的提出者或拥有者才有意义,对追随者和模仿者却不成立,就像你不能再来一个《4分33秒》的音乐,或者,另外一个艺术家拿着刀在画布上怎么捅,都是无效的。所以,非非主义其他几个杰出的诗人,比如吉木朗格、何小竹、小安,就一直很“非非”的写着,没有追随杨黎的废话。近二十年的中国诗歌,其实还有半壁江山是属于“口语写作”的——杨黎的“废话写作”是“口语写作”里最激进的部分——在口语写作里,吉木朗格、何小竹、小安,都是被定义在一流诗人的线上。我和吉木朗格、何小竹都有很好的个人情谊,却秉持着完全不同的诗学价值,我们可能毫不关心彼此的写作,但对彼此的写作都有一份尊重。
八十年代成都这三个诗歌流派,“莽汉”直面当下,“整体”回溯过去,“非非”朝向未来。“莽汉”是感官的,“整体”是文化的,“非非”是观念的。这三个诗歌流派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诗歌的全景。他们的热情是让人感怀的,他们的成就是让人钦佩的,因为他们的努力,汉语诗歌的疆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呈现了多种可能性,一大批诗歌文本被创造出来,正在成为新的经典。他们不经意间,就在历史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的意义,值得我们对这段历史予以更多的关注。
五
这里所谈的,都是我的记忆,也就是说,我个人的八十年代成都诗歌,我经历过的、看到了的或者听说过的人和事,和我都有或深或浅的交集。还有很多我视线之外的东西,我无从谈及。比如两个重量级的诗人萧开愚和孙文波,前者我只是认识,彼此知道,却没有任何交往,而我和后者交往比较多时,他才刚刚开始写作。他们的成就和重要性,要在九十年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托尼·朱特,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完全不信任记忆,他认为记忆始终是碎片的,有选择性的,很有可能讲述的不是事实,甚至可能是谎言。诗人梦亦非不到五十岁,就对我说,他要怀着善意回忆往事,我们都应该如此。我已经尽可能的客观和诚恳了,但所有的观感和看法,都囿于我的视野和见识,并且是顺着一种感觉和个人趣味。当年钟鸣的煌煌大著《旁观者》,曾有非议他把一些个人小事,都当成历史事件来写,但愿我不会受到这样的批评。而所有这一切,按托尼·朱特的看法,都不同于历史。如果有人对这段诗歌历史感兴趣,我会建议他们去看胡亮先生那本专著《朝霞列传: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他应该写的是历史,至少是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进行的写作。
赵野,2021

“借象·红尘”系列
关晶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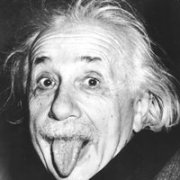 爱因斯坦的绵祆 评论 赵野 | 狂欢与盛筵:1980:值得一读,爽
爱因斯坦的绵祆 评论 赵野 | 狂欢与盛筵:1980:值得一读,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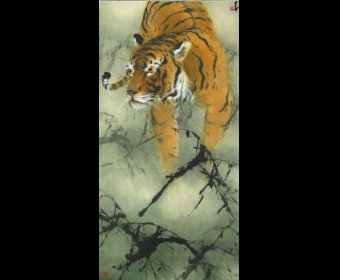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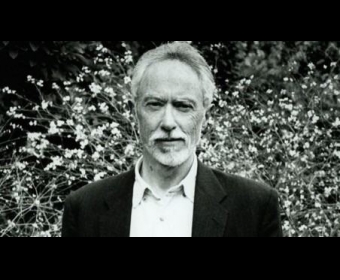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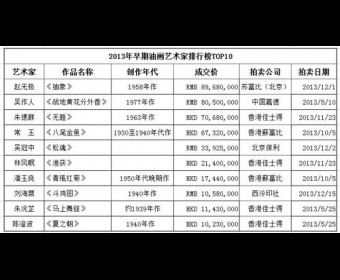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