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说萨义德的意图只是在维护一种(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将把他和其他被殖民的主体祛除到殖民化的经验和遗产外——的同时发泄自己的愤怒,那就太过于简化了。这样的立场,对他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世俗”角色的看法来说是可恶的——在萨义德看来,公共知识分子是要开拓空间和跨越边界,努力“对权力说真话”的。萨义德接过弗朗茨·法农未完成的计划,从一种指责的政治,走向了一种解放的政治。然而,正如他已经指出的那样,尽管他发出了关于在他眼中他的作品将致力于什么——创造一种非强制性、非支配性和非本质主义的知识——的声明,但“更经常的情况却是”《东方学》“被认为是某种对次属地位——大地上受苦的人们回嘴了——的肯定,而不是一种对用知识来促进自己的权力的多元文化的批判”(Said 1995a:336)。
在《东方学》出版之前,“东方学”这个术语本身已经不是流行的用语了,但在1970年代末的时候,它又获得了充满活力的新生。现代东方研究的各门学科,尽管都很复杂,却都不可避免地被灌输了各种传统的对东方(特别是中东)的性质的再现,以及各种支撑东方学话语的假设。尽管萨义德也哀叹,有时人们对《东方学》的挪用过于恣意,但无疑,《东方学》的的确确对普遍而言的社会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1995年的时候,《东方学》已经变成一本出人意料地“废除”了它的作者的“集体的书”了(Said 1995a:300)。你还可以补充说,就对东方学策略的分析在识别帝国文化的各种特定的话语和文化操作上一直是有用的而言,《东方学》也是一本持续成长的书。因为这些分析主要处理的,是再现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权力的再现(尽管它们从性质上说是刻板的印象和夸张的描述)是怎样变成“真实的”和为人们所接受的再现的。
东方学的范围:东方作为附着于欧洲的舞台剧场
萨义德的论证的核心在于知识与权力的关联,1910年首相阿瑟·贝尔福对英国占领埃及的辩护明确地展示了这点。当时,贝尔福宣告:“我们对埃及文明的认识,超过了我们对其他任何国家的认识”(Said 1978a:32)。对贝尔福来说,知识不仅意味着从起源开始全面概述一个文明,也意味着有能力那么做。“有这样程度的对(像埃及)这样的东西的认识,也就是支配它,对它有权威……因为我们知道它,而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存在着”(Said 1978a:32)。贝尔福的言论的前提,清晰地展示了知识和支配是怎样携手并进的:
英国知道埃及;埃及就是英国知道的那个样子;英国知道埃及不可能自治;英国通过占领埃及肯定了这点;对埃及人来说,埃及就是英国已经占领了的、现在治理着的那个样子;因此,外国的占领也就变成了当代埃及文明的“基础本身”。(Said 1978a:34)
但只看到东方学是殖民统治的合理化解释,就是忽视了这个事实,即殖民主义事先就在东方学那里得到了正名(Said 1978a:39)。世界的东西方之分已经酝酿了好几个世纪,它表达了一个根本的两分,而人们就是在这个两分的基础上和东方打交道的。但在这个两分中,只有一方有权力决定东方和西方的现实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关于东方的知识是从这种文化力量中生成出来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及其世界”(Said 1978a:40)。这一论断把我们直接引入了《东方学》的核心,结果,也让我们看到了它引起的大量争论的根源。对萨义德来说,东方和东方人是欧洲人借以认识他们的各色学科直接建构出来的。这看起来一方面把一个极其复杂的欧洲现象缩小为一个简单的、权力与帝国关系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没有为东方的自我再现提供任何空间。
萨义德指出,东方学研究的剧增,在时间上与欧洲空前的扩张的时期契合:从1815年到1914年。他强调,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现代东方学的开端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学的政治性质。而这个开端,不在于威廉·琼斯对语言学正统的扰乱,而在于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这一入侵“从许多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显然更强大的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真正科学的占有的模型本身”(Said 1978a:42)。但关键的事实是,东方学,就其所有的支流而言,开始对关于东方的思想强加限制。甚至像古斯塔夫·福楼拜、热拉尔·德·奈瓦尔或沃尔特·斯科特爵士那样厉害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在关于东方他们能经验到什么、能说什么上也受到了限制。因为“东方学说到底是一种对现实的政治想象,其结构是促进熟悉的(欧洲,西方,‘我们’)和陌生的(东方学的东方,世界的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的”(Said 1978a:43)。它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东方学话语的智识成就服务于帝国权力的巨大的等级网络,并且本身也受制于这个网络。
话语出现的关键,是一个被称为“东方”的东西的想象的存在,这个“东方”是在萨义德所谓的“想象的地理学”中形成的,因为不是说我们可以发展出一门被称为“东方研究”的学科。很简单,东方这个观念存在是为了定义什么是欧洲的。“一个像西方和东方之分那样的大的区分,引出了其他更小的区分”(Said 1978a:58)而从希罗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以降的作家、旅行家、士兵、政治家的经验,则变成了“人们经验西方的透镜,它们塑造了东方与西方遭遇的语言、对此遭遇的认识以及遭遇的形式”(Said 1978a:58)。聚合这些经验的是一种共享的、对某种“他者的”、被命名为“东方”的东西的感觉。这个对东方学的二元性的分析,一直是这本书遭到的许多批评的来源,因为它看起来是在暗示存在一个欧洲或一个西方(一个“我们”),这个一元的欧洲或西方或“我们”建构了东方。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同质化看作东方学话语,至少是含蓄地简化世界的方式,而不把它看作世界真实存在的方式;把它看作一种普遍的态度与形形色色的学科和智识分支关联的方式(尽管这些学科和智识分支的主题和操作模式都各不相同),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种无处不在的思考和所谓的东方学的习惯的话语力量了。
我们可以通过剧场的比喻,来阐明我们理解这种二元的、刻板印象式的认识中的那个被称为“东方”的“他者”的方式。作为一个学识领域的东方学这个观念暗示着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再现这个观念则是剧场式的:东方学的东方是一个舞台,而整个世界的东方就被限制在这个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将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来自某个更大的整体,而他们的作用,正是代表/再现那个整体。因此,东方看起来不是一个在熟悉的欧洲世界之外的、无限的(地理)延伸,而毋宁说是一个封闭的场域,一个附着于欧洲的剧场舞台。(Said 1978a:63)
想象的地理学给了为对东方的理解所特有的一套语汇、一种代表/再现性的话语以合法性,而这套语汇和话语,也就变成了人们认识东方的唯一方式。东方学因此也就变成了“彻底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通过它,东方的一个面向被一个词或短语给固定了,“接着,这个词或短语也就被认为获得了现实,或者更简单地,它本身就是现实”(Said 1978a:72)。
萨义德的分析的焦点,是由他所看到的19世纪东方学的飞速发展和欧洲帝国主义支配的兴起之间的密切关联提供的。通过他赋予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分析的政治导向。尽管不是19世纪初席卷欧洲的东方学的开端,但拿破仑的计划,的确展示了学术知识和政治野心之间的最有意识的联姻。当然,1870年代印度总督瓦伦·黑斯廷斯做出的在梵法基础上组织印度的法院系统的决定,为帮助翻译梵文的威廉·琼斯的发现铺平了道路。这表明,任何种类的知识都是有位置的,其力量也来自它所处的政治现实。但拿破仑的战略——说服埃及人,他是代表伊斯兰而战的,而不是要反对伊斯兰——利用了法国学者所能搜罗的一切可用的、关于古兰与伊斯兰社会的知识,它全面地演示了知识的策略和战略力量。
在离开埃及后,拿破仑给他的副官克雷贝尔严格的指示:永远通过东方学家和他们可以争取到的伊斯兰的宗教领袖来管理埃及(Said 1978a:82)。根据萨义德,这次远征的后果是深刻的。“相当确切地说,占领引出了整个现代的对东方的经验:人们是从拿破仑在埃及建立的话语宇宙内部出发来诠释这种经验的。”(Said 1978a:87)萨义德说,在拿破仑之后,东方学的语言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的描述性的现实主义升级了,在升级后,它不再只是一种再现风格,而变成了一种语言,也变成了一种创造的手段”(Said 1978a:87),其象征是充满雄心的对苏伊士运河的建造。像这样的主张展示了,为什么萨义德的论证如此有说服力,以及为什么在1970年代的时候它能够抓住批评家们的想象。更细致的考察将揭示,最密集的东方学研究大多是在像德国那样几乎没有什么殖民地的国家展开的。更广泛的分析也会揭示,东方学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再现风格。但拿破仑的远征给东方学家的工作指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方向,后者不但在欧洲和中东史上,也在世界史上留下了一笔还在持续传承的遗产。
从根本上说,东方学会有这样的力量和这样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是因为它强调文本性,它倾向于从先前写就的文本获得的知识的框架内介入现实。东方学是密集的多层次写作,这些写作号称要直接介入它们的对象,但事实上却是在回应先前的写作,在先前的写作的基础上建造。这种文本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人的定居和对他们的土地的占领的话,那么,这不过是“伊斯兰的回归”,或者说,就像一个著名的当代东方学家解释的那样,不过是伊斯兰的一个在7世纪时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即伊斯兰对非伊斯兰的人民的反对而已。(Said 1978a:107)
东方学的话语:一种权力/知识的表现
我们最好从福柯的角度,把东方学看作一种话语:一种权力/知识的表现。萨义德说,在不把东方学当作一种话语来考察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理解“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借以在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想象的意义上管理——甚至是生产——东方的那套极为系统的规训”(Said 1978a:3)。
接着我们先前看到的话语概念往后说,殖民话语是一个由关于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关于殖民的列强,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做出的陈述构成的系统。它是关于那个世界——殖民化的行动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的知识和信念的系统。
尽管它是在殖民者的社会和文化中生成的,但它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话语:被殖民者也会在这种话语内看待自己(就像在非洲人接受帝国对他们的看法,认为自己是“直觉的”和“感性的”,并断定自己与“理性的”和“非感性的”欧洲人不同的时候)。至少,它也在被殖民者的意识中创造了一个深刻的冲突,因为它与其他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冲突的。
作为一种话语,东方学被赋予了学院、制度和政府的权威;这个权威,把话语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尊贵的层级上;而话语因此而获得的重要性和特权,又保障了它与“真理”的等同。经过一段时间后,东方学学科创造的知识与现实生产出一种话语——而“真正为从它(东方学)那里生产出来的文本负责的,不是某位既定的作者的原创性,而是它的物质的在场或重量”(Said 1978a:94)。萨义德认为,通过这种话语,西方的文化制度要为那些“他者”、东方人的(被)创造负责,而这些他者和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又帮助建立了欧洲赖以确立自己的认同的那个二元对立。支撑这一界分的,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那条“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不如说是一个人类生产的事实”的界线(Said 1985:2)。处在对像“东方”那样的实体的建构核心的,是地理的想象。它要求维持严格的边界,以区分东方和西方。因此,通过这个过程,它们都获得了使那个区域“东方化”的能力。
当然,东方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即西方)占优势。这个权力和关于东方的知识的建构密切相关。它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关于“臣属种族”或“东方人”的知识使对他们的管理变得容易和有利可图;“知识带来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如此反复——信息与控制之间存在一种越来越有利可图的辩证”(Said 1978a:36)。
东方学话语创造的、内嵌于东方学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起到了建构一个次属于、服从于西方支配的东方和东方人的意象的作用。萨义德说,关于东方的知识,因为是力量生成的,所以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及其世界。
在克罗默和贝尔福的语言中,东方人被描述为某种你可以审判的(就像在法庭上那样)、你可以研究和描绘的(就像在学校的课程里那样)、你可以规训的(就像在学校或监狱里那样)、你可以配图说明的(就像在动物园手册里那样)的东西。要点在于,在每一种情况下,东方都被支配的框架给控制和代表/再现了。(Said 1978a:40)
创造作为“他者”的东方是必要的,这样,西方才可以通过调用这样一个对比项来定义自己,强化自己的认同。
东方学的再现不只得到了像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那样的学术学科的强化,也为“达尔文关于幸存与自然选择的论题”所强化(Said 1978a:227)。因此,从东方学的视角来看,对东方的研究,永远是从一个西方人或西方的视点出发的。根据萨义德,对西方人来说,
东方永远和西方的某一面相像,比如说,对一些德国浪漫主义者来说,印度的宗教本质上是日耳曼·基督教泛神论的东方版。而东方学家,则把这个——他永远在把东方从一个东西转化为另一个东西——当作了自己的工作:他为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文化而做这个工作。(Said 1978a:67)
这种对东方的编码,以及对东方与西方的比较,最终确保了这点:东方的文化和视角被看作一种偏差、一种变态,并因此而获得一个低劣的地位。
东方学话语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东方和东方人的客体化。它们都被当作可被审视和理解的客体来对待,而这个客体化,在“东方”这个术语中就得到了确认——“东方”包含一整个地理区域和一大批人口,比欧洲大许多倍,也比欧洲多样许多倍。这样的客体化引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东方本质上是铁板一块的,它的历史是静止不变的;而实际上,东方却是动态的,它的历史也是活跃的。此外,东方和东方人也被视为被动的、无参与的研究对象。
不过,就西方的知识总会不可避免地引出政治的意义而言,这种建构也有一个独特的政治维度。在东方研究的兴起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崛起那里,这点得到了最好的例示。19世纪印度或埃及的英国人对那些被他们发现的、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发生了兴趣。萨义德指出,这看起来可能“和说所有关于印度和埃及的学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恶心的政治事实的沾染、印刻和侵犯”截然不同,“但这就是我在这本对东方学的研究中要说的事情”(Said 1978a:11)。萨义德之所以能这么说,是因为他坚信,这种话语是在世的:“任何人文科学中的知识生产都不可能忽视或否认其作者作为一个人类主体对他自己的境遇的参与。”(Said 1978a:11)。学术知识被政治和军事力量“沾染”、“印刻”和“侵犯”这个观念不是说,像德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 1983)指出的那样,东方学话语的霸权影响不是通过“同意”来运作的。相反,它说的是,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看起来在道德上持中立态度的对知识的追求,实际上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假设。“知识”永远是一个再现的问题,而再现又是一个给意识形态概念以具体形式,使特定能指表示特定所指的过程。支撑这些再现的权力,与政治力量的运作是分不开的,即便它是一种不同的权力,一种更微妙、更具穿透性,也更不可见的权力。
因此,权力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帝国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存在于它的“野蛮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基本原理”(Said 1978a:12)中,也最为霸权地存在于它的文化话语中。我们可以在文化领域中识别被用来宣传帝国主义目标的支配霸权的东方学研究计划。因此,萨义德的方法论是内嵌于他所谓的“文本主义”的,“文本主义”允许他把东方设想为一个文本的创造。在东方学的话语中,文本的认属迫使它把西方生产为一个区别于作为知识的客体的,以及不可避免地从属的“他者”的权力的场所和中心。东方学文本的隐藏的政治功能,是它的在世性的一个特征,而萨义德的计划,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方作为一个文本建构的建立过程上。他对分析隐藏在东方学文本中的东西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展示东方学家是怎样“使东方说话,描述东方,为西方、对西方说明它的神秘”的(Said 1978a:20-1)。
再现问题是理解话语——知识总是在话语中建构——的关键,因为萨义德说,真实的再现可不可能都是成问题的(Said 1978a:272)。如果所有的再现都内嵌于再现者的语言、文化和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做好接受这个事实的准备,那就是,再现本身(eoiPSo)就是和除‘真理’外的许多其他东西牵连、交缠、嵌套、交织在一起的,所谓的‘真理’本身也是一种再现”(Said 1978a:272)。那种信念——相信像我们在书中发现的那样的再现,是与真实的世界对应的——就是萨义德所谓的“文本的态度”。他指出,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赣第德》和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在《唐吉诃德》中讽刺的,正是这样的假设:“我们可以在书本——文本——说的东西的基础上理解生活中蜂拥而来的、不可预期的、难题性的混乱,而人类就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生活的。”(Said 1978A:93)这确切来说,正是在人们以为东方学的文本意指、再现真理时发生的事情:东方被迫沉默,它的现实被东方学家揭露。因为东方学的文本提供了一种对一个遥远和异域的现实的熟悉甚至是亲近,所以,这些文本本身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并获得了比它们试图描述的客体更大的重要性。萨义德认为“这样的文本不但能够创造知识,还能够创造它们看似在描述的现实”(Said 1978A:94)。结果,考虑到东方人自己是被禁止说话的,所以,创造和描述东方之现实的,就是这些文本。
东方学的最新阶段,与美国取代法国和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相应。尽管权力的中心发生了转移,东方学的策略也随之而发生了变化,但是,东方学的话语,在它的三个一般模型中一直是稳固的。在这个阶段,阿拉伯穆斯林已经占据了美国流行意象中、社会科学中的核心位置。萨义德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行的反闪族(Anti·Semiti C)的敌意从犹太人转移到了阿拉伯人头上……因为这个形象本质上是一样的”(Said 1978a:28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东方学的衣钵传到了社会科学那里。这些社会科学家确保这个区域“在概念上被削弱、简化为各种‘态度’、‘趋势’、数据:简言之,使之非人化”(Said 1978a:291)。因此,东方学,在它的几个不同的阶段,都是一种通过数代学者和作家(这些学者和作家一直享有他们“高人一等”的智慧带来的权力)积累的知识,来建构“东方”的欧洲中心的话语。萨义德的意图不仅是记录东方学的过度(尽管在这方面他做得非常成功),也是强调对一种替代性的、更好的学术的需要。他认识到,也有许多个体的学者在参与这样的知识的生产。但他关心的是东方学的“行会传统”,这个传统有能力腐蚀大多数学者。他敦促人们在与东方学的支配的斗争中持续保持警惕。对萨义德来说,答案是“对再现、研究他者、种族思想、不加思考和批判地接受权威和权威的观念、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角色、怀疑的批判意识的巨大价值涉及的东西保持敏感”(Said 1978a:327)。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最高义务,是抵抗那些隐含在东方学话语传统中的东西的“神学”立场的诱惑,强调对权力说真话、质疑和反对的“世俗”欲望。
原作者 | [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澳]帕尔·阿卢瓦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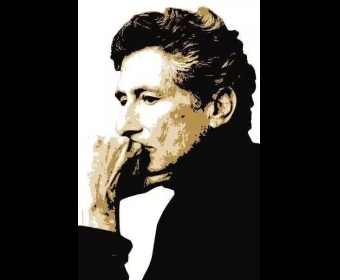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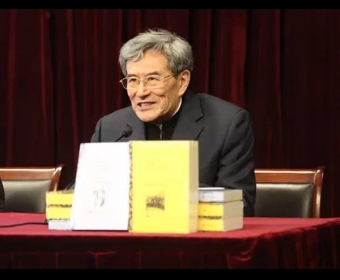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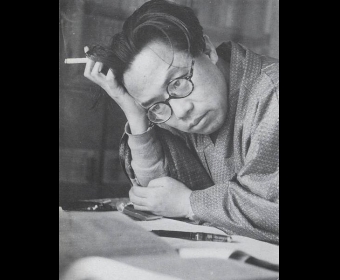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