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房子 男,1968年出生,湖北人。1985年就读于重庆大学电机系,1992年就读于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由工科而文学,心性误我,由文学而新闻,我误人生。“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写作20余年,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现居重庆。
诗歌是这个时代的微言,微小的言说,或者微不足道的言说,这是让我对写作还有勇气和信心的唯一理由。
我们身处的时代具有太多的言说方式,很多阶层都有自已的代言人,他们往往是在繁华的舞台为奇迹而欢呼,为他们搭上了一辆高速的通向未来的磁悬浮列车而庆幸。不同的奇迹因此成为不同的阶层的时代注脚。但我知道,普通人是没有奇迹的,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沉默的前行,即使沉默也并非安全,他们是高速列车之外的人,高速列车带来的大风很有可能刮走他的外套和村庄,他们偶尔的呐喊凄厉,但很快被淹没在时代的喧哗之中,成为布罗茨基所说的一个时代“小于一的余数”。在如此多声部的当下中国,诗歌这种古老的言说方式正在失去它曾经的光荣和梦想,它扮演着遗老遗少的角色,时不时地也会在舞台中央深情并茂地诉说,但那已与诗歌伟大的传统无关。
事实上,诗歌的舞台已经谢幕,或者说它退到了没有观众的隐秘而充满荆棘的沼泽地。因此,写作变得更加艰难,免于自我沉沦的路径不是面向未来,而是深入幽暗的自我和过去,这是一个诗人一生的孤寂旅程,通过和那些不朽灵魂的对话,你可能获得逆流而上的力量,但你必须忍受绝望。汉语的凋零从你开始,曾经奔流不息的汉语,那清澈的河流如今已是沼泽的汪洋。你只是看到了这一真相的人,你的无能为力表现在,你写着,但每个汉字都在沦陷。
写作的处境大抵如此。它给诗人带来很多的困难,但也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让诗人的视线离开宏大叙事,进入细微之物,从而建立一道词语通向万物的秘密走廊,这是个人化的,更是对个人化的颠覆,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曾经的经验在当下失效了,歌唱、痛哭或者无所不在的抒情在现实的掠夺中几乎就是无病呻吟,而现代诗歌中一直诱惑着无数诗歌青年的“游荡者”形象如今已改头换面,成为了网络时代的“犀利哥”。“游荡者”在波德莱尔的笔下成为20世纪现代诗歌的先锋角色,混杂着波希米亚式的古怪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街头流浪汉式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方式,通过本雅明的天才解读,“游荡者”成为了现代诗歌的革命者,它由外及内地重构了诗歌的森林。当现代人的精神日益空心化之后,“游荡者”变成了21世纪网络时代的“犀利哥”,犀利的眼神还在,但没有了方向,时尚依然在混搭,但只是现实的反讽,但没有了开路先锋的雄心。
原来,所有的道路就是没有道路。唯一的可能性,我们还可以无所障碍地观察那些被诗歌所忽略的细小事物,它们的自由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它们还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经验,一群蚂蚁、一朵野花、一把铁钉或者一个陈述句,在汉语中有可能重生,有可能让一物和另一物获得新的联系。这让我心怀感激,也让我明白写作不是与时间赛跑,它缓慢流淌出来的,终究不过是大时代的一滴眼泪。





 南方的南 评论 何房子自述 | 微言无大义:好东东
南方的南 评论 何房子自述 | 微言无大义:好东东 再见重庆 评论 何房子自述 | 微言无大义:写作不是与时间赛跑,它缓慢流淌出来的,终究不过是大时代的一滴眼泪。
再见重庆 评论 何房子自述 | 微言无大义:写作不是与时间赛跑,它缓慢流淌出来的,终究不过是大时代的一滴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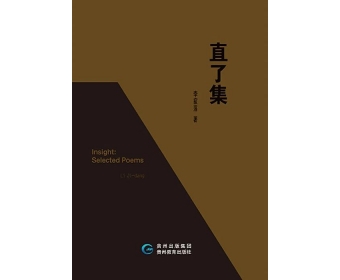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