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你说的可能是重庆和成都的景象吧,我也听人讲过那时那里的狂热,不过“顾城只要说一句话,底下的女同学就晕倒一大片”,那肯定是夸张和演义了。上海没有这么狂热,可能上海给出的眼界,的确能见识得更多一些。在我这儿,有时候甚至是让我略感不安的冷淡。譬如1983年顾城来我们学校演讲,我并没有去听,只是中途路过,在后排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问:印刷术未发明前,手抄本是主流的文化传播方式。后来即使有了印刷出版技术,但大量的个人作品,是用手抄的形式留存的。到了现代,流传最甚的时候是1974年、1975年。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手抄本有300多种。而中国的手抄诗歌,也迎来了“喷涌”,我姑且将这称之为“诗歌的手工时代”,我家里还有我父亲的《天安门诗抄》,再后来,好像油印的居多。从手工到油印的记忆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或人?
答:有啊,1980年代,我自己就参与了用铁笔刻蜡纸和油印地下诗刊的活动,直到1990年代中期,还在主持做一个叫《南方诗志》的地下刊物。几年前我写过一篇东西叫《杂志八十年代》,讲了不少相关的人和事,这篇东西刊于2008年第一期《收获》杂志,可以参看。
问:许多去过上海的朋友都知道,上海马当路上有个以“夜店成群”而著称的景观地——“新天地”。 20年前,这里叫“太平桥”,在太平桥靠近顺昌路处有个报亭,据说80年代中期,每到傍晚时分,这里就会聚集了很多市民,他们手里拿著各种各样的“小册子”,或沽售,或“交换”,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上海风景线。还有“文庙书市”。这些换书淘书的情景您经历过吗?
答:文庙我常去,是淘书的好地方。换书的场合,我从未去过。
问:8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到一个空前的变革过程,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涌动,许多人开始下海经商赚钱。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您对“经商”敏感吗?大学毕业后,您曾经辗转好多岗位,从来没有想过“下海”吗?
答:我曾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史料室上了十三年班,接触很多过去的商人和商业史料,对于“经商”之事,也算有过职业敏感吧。我没有“下海”只是因为我没有“下海”。是我身在“上海”?是命运不要我“下海”,要我去写诗?其实我对自己也还有所了解——我并没有经商的才能。
“我的写作出于内在的需要”
问:自从被“埃利蒂斯”撞击之后,您如光明附体,用色彩斑斓的想象和典雅的词语去呼唤着神秘而庄严的一生,“身体内部语言”也被唤醒,从那一刻起,您已经准备好了为诗歌奉献一切,从主动、坚决地不做教师,到联合会的机构上班,以及后来的种种变动,目的似乎都是为了给您的“高度写作”找一个理由,而您自己甚至在汪洋语词的国度里,扮演了一名英雄色彩浓烈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您在精神上并不输于同时代的海子,您自己怎么看待?
答:我不喜欢“光明附体”“奉献一切”“英雄色彩浓烈的臣民”这种说法,这跟我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我跟海子也很不一样,没有可比性,更无所谓输于和不输于。
问:刚开始诗歌创作时,您把禅引入了诗歌,这可以从您1981年底完成的一个组诗《涉江及其它》里看到。同一年您创作的还有《避居》、《野寺》、《一百单八将》、《短章》等,这些诗更加倾向于小写意,虽说词语吝啬,但深意却是铺开的,像典型的中国画。相比而言,这一年创作的短诗《诗篇》,抒情的味道更炽浓一些,土地、流水、女人,个个炫示着唯美的个性,这几乎成为了您后来一直创作的基调。也就是说,1981年,您花费了12个月的时间决定了一生的诗歌色彩,是这样吗?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年的创作的?
答:1981年是我诗歌写作的出发之年,我写得不少,扔得更多,那一年对我而言是个练习之年,学习之年。我不知道1981年是否能决定我一生的诗歌色彩。我觉得它并不能够,也希望它并不能够。
问:在长诗《断简》中,你再现了个人“众我之中,众我之外”的精神图像。星宿、欲望、虚构以及上升或降落,死亡或诞生,加强了“未日”的成份,也添加了史诗的悲壮;马车、自行车、摩托车、有轨电车、轿车、大客车、柴油机、推土机、轮船、喷气式飞机,这些“重型”组合成为了“漩涡城市”的轴心;黄鼬大小的身形,黄鼬大小的怪兽,黄鼬大小的凶兆之猫,黄鼬大小的星座之异物,复叠、多重、伪装的幻像与魔境的制造,给人窒息的阅读快感……这首诗为什么起名为“断简”,有什么强烈的暗示吗?创作这首长诗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呢?
答:《断简》起草于1996年,开始时题作《炼丹者巷22号》——这个诗题显然跟卡夫卡相关。1999年蔡逍对我的一次访谈里我曾说起这个诗题:“那是卡夫卡曾经在其中写作的一间小书房的地址。在开始写这首长诗的时候,我没有合适的诗题。有一天,我正在琢磨用一个怎样的题目的时候,收到了欧阳江河的一封来信,其中有一帧他游览布拉格时在炼丹者巷22号门前拍的照片。照片上的那条巷子,跟我当时居住的上海七浦路一幢石库门旧楼前的巷子十分相像。这使我决定用那个地址来做诗题。在我的心目中,它变得双关了,正像诗本身要双关于两座城市,两条巷子和两个写作者。”但这个诗题、这首长诗一直让我放心不下,这首诗的写作,就像我其它诗篇的写作,一直处在未完成的状态。后来我又几次改订这首诗。把诗题换作《断简》,因为这是摹拟书信片断写成的诗行。
至于写作《断简》的背景,这个时代的背景,我们都经历过,经历着。我是所谓上海的诗人,那么就还有一重上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当然这首长诗由我来写,必然有我的个人因素和特殊背景。每个写作者的写作,也一定离不开他的国度和语言带给他的背景。所有这些都可以细论,但我不想多谈,我不想用一些谈论去影响读者对一首诗的阅读。我想,应该是每个读者带着自己的个人因素和特殊背景,带着自己的心情,对语言、诗歌、生活和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去读一首诗,而不是让一个诗人,一个作者在读者的阅读前后去画蛇添足地告知诗的写作背景和别的什么背景。诗本身是自足的,诗呈现诗所给出的一切,无需别的阅读作料。
问:马克思曾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这强调了耳朵的主体性,音乐既然是声音的艺术,在您看来“无非是耳朵的产物”,这同样强调了这种主体的功能。那么一个诗人,对声音的敏感主要来源于什么?
答:每个诗人不同,无法一概而论。对我来说,对声音的敏感,或许,因为童年经验,记忆和其实无意识的听力训练。当然,基因,体质,出身,环境,经历,一切的一切,都会是敏感于声音之源。
问:读您的诗,感觉个体角色会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撤离,那个叫陈东东的人,隐藏在他华丽的结构里,每一个显现的词,都迎接着每一种声音的进入,而每个声音的后面,必然有一个发声的体系,这从整体上来看,就造成了“我是我的合唱体”的宏大场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如何分解自己却又是如何统一到一个主旋律中的?
问: 我只是一个词一个词、一行诗一行诗地写,整体虽在我的意愿之中,但更在我的意志之外成形。就是说,一件作品的最终完成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不由自主的偶然,一种不可能的可能,一次不可为之的作为。这的确像做梦,如果你想把梦做完整,那么你就要保证自己不醒。我的意思——我只负责写,至于能写成个什么东西,其实不归我管,归读者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管。我不是一个能够分析自己写作的写作者,很大程度上,我的写作是自然、天然的出产。
问:诗美体验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即灵感之前,是储备,灵感之后,是爆发,您在创作的过程中,对灵感的依赖性有多大?
答:我不知道灵感是什么,因而我认为我从不依赖我不知道的灵感写作。我写作出于内在的需要,出于写作的意愿,那么可否说我是依赖写作的必须而写作的呢?
问:有人认为,对诗来说,最高的技巧是无语言、无痕迹的无技巧。如果要说诗无关技巧,我想一贯以修辞实验为主要手段的您应该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吧?
答:“对诗来说,最高的技巧是无语言、无痕迹的无技巧”,我想这种说法是缺乏真诚和对诗歌写作的切实体会的。我记得桑克有一次做我的访谈,我跟他谈及过相关话题,我当时说:“修辞是必然的,如果你写作,甚至只要你说话。所谓直接怕也不过是一种修辞,特别当直接刻意去避开那么多婉转间接的时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也还是写出来——人工做出来的,其手法只是刚好,恰到好处。自然而然的分寸感我认为就是一种修辞学,它是严格训练出来的,只是终于‘手熟’罢了。”在此,我愿意把“修辞”换成“技巧”来回答你的提问。
问:李笠曾明确表达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困惑,据说一次他将瑞典文诗歌里的玫瑰,翻译、改写成了牡丹或菊花,我想问的是,从一种语言的澄明想要达到另一种语言的澄明,有没有百分百的直通车?
答:我没有翻译的经验,不过也有过一些体验,另外我想我有这方面的常识。我认为你问起的那种情况是没有的。
问:人的一生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抗衡自己。诗人也是如此,尤其有责任的诗人总会将自己杀死在自己的诗中,然后重生,再死,继续重生。最近我发现您的博客里突然多出了许多旧诗,从1981年到1991年(可能还要延续),这些诗都是原汁原味的“过去诗”,还是您在“博客”之前就已经做过“当下”性质的修正与处理呢?您试图从这些诗中获得“重生”吗?为什么不贴新写的诗呢?
答:我的诗歌写作未完成,就是说我一直在写,在改,我想我这辈子并不能完成我的诗歌写作,哪怕我不再写诗了,也并不表明我曾经写下的那些诗已经完成了。我差不多在每首诗后面都标记年份,所标记的是开始写作这首诗的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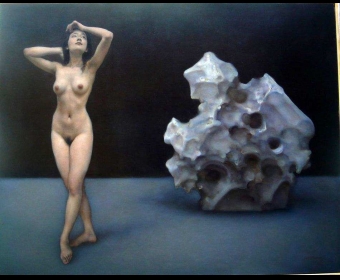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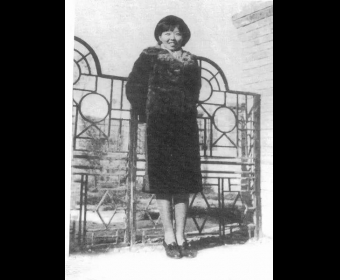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