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历了一个盲目求新的时代。然而有一天,当我重读歌德,无意间接连发现T·S·艾略特的“历史感”和维特根斯坦的“凡是不能说的都应保持沉默”的出处时,我惊讶了。当然,我不会因此而抹平后两者的意义,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发现以前曾占据了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现代主义”的世界再一次地缩小了:它不过是历史的一部分,或是历史的一个变项。
这时再回过头来重读杜甫、李商隐这样的中国古典诗人,我也再一次感到二十世纪的无知、轻狂和野蛮。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沉痛、仁爱和悲怆来感应这样的生命,就如同我们对艺术和语言本身的深入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那样的造化之功一样。我们刻意发展并为之辩护的“现代性”是一种“出了问题”的现代性。我们的那点“发明”或“创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也几乎算不了什么。
在谈论桑克的诗之前说这些,是因为我相信这也构成了这位比我年轻十岁的诗人的写作背景。我们当然应充分关注更年轻的诗人,但我们关注的应是那些优秀、独立的个人,而不是“代”或“派”这类可疑的整体。目前在诗坛流行的以诗人出生年月来划代树派的做法只能让人感到奇怪。如果按照这类可笑而武断的划法,我和桑克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好在我们并不形同陌路,相反,在不同的岛屿之间仍有着一种深刻的连结。我在这里要考察的,也正是那些把我们置于同一的场域和关注点、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写作问题。
桑克最早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那首写于1995年的《公共场所》。这首诗我几乎一下子就记住了,它不动声色地显露了一个诗人的专业性质、风格特点和写作潜力,以及他和同时代诗人的某种差异性。“那人死了。/ 骨结核,或者一把刀子,”而接着却是两个若无其事的护士在“明亮的厨房里”谈论三明治的“嫩”或“老”,这着实让人吃了一惊,而全诗的最后一句“相爱者坐在 / 广场的凉地上,数着裤脚上的烟洞究竟有多少”,更是显示了一种优异的反讽品质。一个数烟洞的细节,在此胜过千言万语。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不仅显示了一种训练有素的专业技艺,而且暗含了更多的耐人寻味的东西,比如诗的第二段“一个女人呆坐在长廊里,回忆着往昔:/ 那时他还是个活人,懂得拥抱的技巧 / 农场的土豆地,我们常挨膝 / 读莫泊桑,紫色的花卉……”这里,“莫泊桑”这个词的运用真是恰到好处(说它是一个“词”,是因为在中国语境里它已由一个人名变为一种文化代码)。它不仅使人感到亲切,重要的是,它使一首诗的修辞顿时具有了某种有血有肉的历史的具体性。这个例子也表明,由于一种历史意识的觉醒,90年代的诗歌修辞已不仅是打比喻了,它还伴随着叙事因素的引入,对细节的关注和选择,词语的转化,文本与语境的相互指涉,等等,从而发展成为一套更复杂的诗艺。“莫泊桑”一词的匠心独运,正显示了一种确立(或还原)诗歌修辞的文化和历史语境的努力。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诗人重新确立其写作的位置的努力。
这就是桑克的《公共场所》,我宁愿把它作为解读一位诗人的起点:专注于修辞和技术,但又不仅于此。这不仅因为修辞本身不可能是空洞的,也因为他——正如我们在其后来更多的诗中所感到的——不能放弃一种关怀。这大概是命运为很多中国诗人所设置的一道难题。在某种意义上,桑克的写作一直就在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展开。
也许正因为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个人性格、气质的因素,桑克的写作一直是不那么冒进、或偏于一端的。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敏感而又稳健,也可以说,他通过写作反复训练的,乃是一种均衡的技艺,是一个诗人的“限度意识”。《一个士兵的回忆》,是诗人近年来写给父亲的一首诗。像许多诗人一样,桑克也进入了一种家族史叙事。理解父亲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进入历史、承载记忆、确认自我的过程。在诗的结尾,当逃兵的父亲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更适合做个农夫 /安静地守着几亩薄田,几间破烂的草房 / 研究种花的手艺,就够我消耗一生的才华。”这里,父亲说出了多年后儿子要说出的话,或者说,父亲在用一个写诗的儿子的头脑思考。显然,通过这样的家族史叙事,桑克不仅要给他的写作带来某种依据和历史的纵深感,还要由此再次确认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限度”何在。
然而问题在于,诗人不可能像一个走钢丝艺人那样来维持平衡,纵然桑克曾以此写过一首挺不错的诗,并以此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隐喻。平衡会被不断打破,因为生活和艺术都会固执地向一个诗人提出要求,灵魂本身也在要求着一种表达。我知道桑克对奥顿颇为倾心(他曾试着译了好几十首奥顿的诗,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奥顿在一次访谈中曾这样声称“我从来都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但接着他又这样回答来访者:“游戏的乐趣是暂时的,你得说出什么才行”。这真是意味深长。在我看来,桑克的写作恰恰一直徘徊在修辞游戏与说出什么之间,而在近年来,据我观察,他更关注的恐怕正是这个“你得说出什么才行”。这不仅是因为诗人自己阅历的增长,也不仅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莫名其妙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感(我甚至听说他在诗生活网上发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写诗声援民工的运动),更是为了诗歌本身,因为同样很显然,只专注于形式和技术的写作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它也会陷入如人们所说的那种“美学的空洞”之中。
桑克近年的诗《雪的教育》,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这是一个出生、长大在多雪的北国的诗人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回赠。在这首诗中,“雪”被赋予了耐人寻味的含义,诗的开头即是一种颇能唤起公众共鸣的抱怨:“在东北这么多年,没见过干净的雪”,这让人不能不沮丧——不是对雪的而是对现实的沮丧;然而接下来,却是一种动情的诗的赞颂,因为展现在诗人面前的,已不是城区上空的雪,而是记忆中的雪、远离人世的雪:有时它“甚至不是白的,而是 / 湛蓝,仿佛墨水瓶打翻 / 在熔炉里锻炼过一样”,“而在山阴,它们 /又比午睡的猫安静……它连一个身 / 也不会翻。而是静静地 / 搂着怀里的草芽 / 或者我们童年时代 / 的记忆……”诗的感人的力量就这样出现了,然而,这却不是一支轻松的谣曲,回忆也不可能代替现实,相反,它把现实更为刺目地暴露在一个人的良知面前。因而诗人会这样写,把雪在国防公路上被挤压时发出的吱嘎声理解成呻吟是“荒谬”的,“它实际上 / 更像是一种对强制的反抗”。这样写有点出乎意料,但一点也不牵强,因为诗的修辞最终触动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积郁,因为诗人在现实中也正是一种受践踏的存在,“而我,嘟嘟囔囔,也 /正有这个意思”,诗人在这里招供了。这个“嘟嘟囔囔”大概是这首诗中一个最独到、最耐人寻味,并带有自嘲意味的词。然而无论如何,一个人内在的舌头开始说话了,纵然它采取了这种“嘟嘟囔囔”的方式。最后,诗人把它归功于“雪仁慈的教育”。
就这样,诗由抱怨和沮丧开始,经由早年的动情回忆、赞颂和现实的屈辱,最后带来了一种觉悟。这种觉悟,不是感悟到一点小哲理,而是以这种方式转瞬间把每一个读到它的人置于一种更为深远的人生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是呵,我们谁不在这种雪的“教育”甚或“目睹”之下?在“雪的教育”这样的“修辞”中,是美学与伦理学的出乎不意而又必然的相遇,是一种更能对我们的人生讲话的艺术语言的诞生。
这样的诗让我感动,它让我再次思忖什么才是“诗的技艺”,什么才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写作。我相信对诗人西穆斯·希内如下的话桑克一定有着深切的同感:“学习技艺即学习在诗的井中转动绞车。通常在初学时你只把水桶降到井深的一半,绞上来一桶空气。你在模仿真实的东西直到有一天绞链出乎意料地拉紧了,你浸入了那将不断引诱你返会的井水中。”(《进入文字的情感》)
这一次,一个诗人手中的绞链“出乎意料地拉紧了”。然而,艺术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并不是一首或几首诗的写作就能解决的,甚至不是一生的写作可以解决的。桑克仍处在他的矛盾之中,或者说处在一个更深刻的临界点上。一方面,他不满足于在修辞的圈子里打转,只“绞上来一桶空气”,他要试图进入真实的人生,写出存在的血肉本质,但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很警觉地把自己限制在专业的“诗”的领域内,如有人所说“坚守在一个在战略上有所限制的世界里”。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处理好了,就会给他的写作带来一种饱满的张力,如果相反,则会带来某种不协调或摇摆不定性,摇摇晃晃的风筝就会一头栽下来,变成一只死鸟。比如《雪的教育》这首诗,整体上不错,以上已引述的一些句子和比喻也都很好,但像“结实像石头,柔美像模特”这样的对雪的比喻就有过度和空洞之嫌。为什么?在某种崇尚修辞和技术的时代氛围中,也许他想因此增加一首诗的“技术含量”,结果却显得有点多余。这表明了单靠平衡的技艺和才能并不能完全化解写作中的矛盾,表明在一个诗人写作的内部还有更深刻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考察。
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对桑克的创作进行一种全面的解读,这里我想说的是:桑克作为一个诗人在艺术上的确已趋于成熟,他的“土豆”可以挖掘了,然而,也恰恰是在一个诗人越过其习艺和早期阶段,逐渐接近其一生的艺术目标的情形下,写作的困境和难度才得以显现出来。这种不到时候就不会深刻显露出来的困境和难度,有时甚至会宿命般地将一个诗人留在那里。这个困境,如我在其它文章中已分析过的,仍是在审美与伦理、自由与关怀、个人与历史的冲突之间反复形成的。对此,请想一想自屈原以来一代代中国诗人的命运吧。只要我们“过了二十五岁后”(这里仍借用T·S·艾略特的说法)仍在写诗,只要我们认定自己是一个诗人而不是诗匠,我们就会多多少少受制于这个基本困境,就会一再感到它的矛与盾的深刻撞击。
而一个置身于这种困境之中的诗人,看来不仅要依靠其“限度意识”和平衡的技艺,还要借助于这种撞击来不断深化和强化其心灵的力量。只有这样,他才有足够的“内功”来整合这人生的和美学的种种矛盾。如有可能,他还要无畏地听从一个人内在良知的召唤。叶芝曾经这样感叹过“人在两个极端之间走过一生”,可是他在《在学童中间》的最后对人生与艺术的至高境界又做出了这样动人的描述:“栗树啊,根子粗壮的花朵开放者,/ 你就是叶子,花朵,或树身?/ 随乐曲晃动的躯体,明亮的眼神,/ 怎叫人把舞者和舞蹈分清?”
对一个终生奉献于诗和艺术的人而言,这是不是一个比走钢丝艺人更让人动心的比喻呢?这里我们只能沉默。这一切,正如桑克自己的诗所启示的:我们是在雪的教育下,而雪,永远是无言的。
20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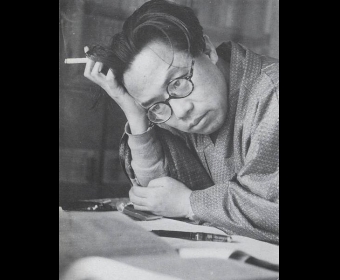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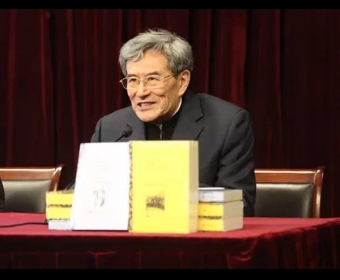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