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肉身,沙磨骨桠
——读泉子《杂事诗》
郭建强
保尔·瓦雷里说 :诗是一种感叹。
遗憾的是,49年之后,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诗歌只剩下对政治图腾的顶礼膜拜,就是有点什么感叹,也不过是一种利用唱歌技艺而吐气扬声的“花腔”——即使发出“花腔”,也少有技惊四座的效果——原因很简单:歌唱需要艺术,但艺术必须回到人间,回到人身,才可能绕梁三日而不绝。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大陆地区)经过地下诗群艰难引领,和世界诗歌破门而入的瀑洗,逐渐肌理形成,恢复肉嗓发声的能力。各种调门的吟诵、呼喊和低语,风起云涌,一时蔚为壮观。接下来是89,一阵巨浪将美轮美奂的文化泰坦尼克掀翻海底,隔岸观潮者、灾难之后的残存者等等,莫不生有“劈开八片天灵骨,一桶雪水浇下来”之感——白日梦式的追写、旧日怀乡病式的吟咏,和狂言式的大话英雄写作,瞬间体无完肤,暴露出弱小的耻部;继续写作的诗人必须停止半空梦游式的高蹈,转而脚踏实地。
以上是70后诗人进入诗歌“坛城”的客观实在。此时,文化和诗歌不无浮浪的黄金盛宴已告结束,但登堂入室一窥堂奥的扶梯,仍被内力深厚的50后及60后诗人把持。而在70后诗人的背后,真正成长于商业时代礼崩乐坏渴望一夜成名的80后和90后写作群体,正浑身尽裹黄金甲,如钱江潮汛呼啸而来。急于在潮起潮落间隙抓住点什么的70后诗人要么抱团呼吸,要么剑走偏锋,指望在落草和招安之间觅得纵马良机,占得一席之地,搏个封妻荫子。倒也成就了不少人。只是,此类抢占先机的弄潮儿的作品大多单薄,可供推敲细赏和问难者寥寥。一度,在现实的压力和写作策略的盘谋下,“叙事”成为众多诗人希翼脱苦海吸引眼目的救命稻草。遍地都是口语即景式的新闻叙事,以及家族叙事、打工叙事和颇具把玩情调的文化叙事。“叙事”引入诗歌,的确对米兰.昆德拉称之为“刻奇”的美学观,进行了修正:诗歌不再将一种诗意性的社会化和美学模式加强于读者。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贴地叙事贴身叙述,远远不能与今日中国一日三变的奇观至景相匹配;而叙述式的感叹,也根本无力追撵时代动车的疾驰和侧翻。在“六经注我”的炫急时间,诗人还需要更精确地调整自我的方向盘,把握好稳定器,以诗歌巨灵的内在特性,实现“我注六经”。
在喧哗众声中,泉子的喟叹清澈入耳。
很难说,是泉子的具体哪一首诗打动了我——所有作品——在《杂事诗》中,所有诗歌带着片段性质(仿佛冰川的一个个棱柱),又在书叶中集合(仿佛众星体构成的某个可以不断延展的整体)。这样的诗歌品相与时间的状态暗合,你可以从任何一首诗读起,穿插缠绕,顶磨冲突,风景自在。而每一首诗歌的很多句子同样具有或曾潜在地具有不断延绵和再生的能力,仿佛是引向新的天地的起首。这些血管一样温热而绵长的句子,带着她们色彩不同的音节,在完全被你的眼睛或舌头点亮字词的黑暗之后,便马上归于湮灭,只在你的腔留下某种回响,但又马上在下一行诗句中重生,犹如波浪不断在滩涂地带留下足迹和贝类,还有某种看不见的、来自更深远的气息(仿佛某种大多数人都曾在生命经验中存在过、闪现过的神秘漂流瓶),当然也会留下时代表层的垃圾弃物;如此,诗句循环往复,等待你再次默读或吟诵,再次冲刷大地,或者在诗句中成为另一个你,眺望海波叠波正从远处如同马群缓慢地疾驰而来。
检读《杂事诗》,首先感觉诗歌的魅力来自诗人思维的行动。简单地说,泉子并不是一种将纳入诗歌的事物赋予宗教感的纵深、高远和宽阔的诗人;泉子的能力在于对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梳理,在于对于某一事物或悄态的静观、细读和辨证。这样的努力,使得诗人的写作既摆脱了即成的各种神学谱系的高空辐射,也与就事论事的狭隘天然地保持了疏离的姿态。以《雾越来越浓密》一诗为例,诗歌从大雾中的辨认和辨别开始,宝石山、尖塔等等在生活中每天呈现的标志性事物开始一一呈相,然后从实体和貌似熟稔的场景转化为对生命感觉的描述与探讨——由是“住进各色花瓣的春天”适时进入视界,并且在回忆中与父亲讲述的故事形成因果,”一张白纸剪裁成的鸟,被谁的嘴巴吹了口气/便在湖面上,在一棵柳树与另一棵柳树之间穿梭……“在如此这般的转述中,我们似乎听到“创世纪”的另一个版本的画外音;可是,泉子诗的着力点并不在于只是唤醒我们心底共同的某种原型,并且与之共鸣;“雾越来越浓”继续执拗地高低盘旋,左右触探,诗人冷静而严密地写下如下推导:“如果雾能从夜那里获得启示与力量/并将白色的边界推向我的眼睛/我又会获得什么发现”——诗人对着神启般的浓雾或者梦魇般的浓雾提出巨大疑问,同时也向面对浓雾的自我发出疑问。泉子诗的力量显现为思维的脚足的行进,能够在我们习以为常(日常的和知识谱系的)司空见惯的景幕中撕开一道缝隙,继而踩踏出一条不知其所终的羊肠小道。因为,诗人本身就是探路者,而其探索的是生命和生活、历史和现实、实境和幻境的纠合探路。在此诗的最后,诗歌焦点对准了自己(“当我说出,并写下孤独,并不意味着我真的看到了什么”);也对准了星辰(星辰们裹挟着远古的光芒);对准了先人(先人们的眼睛像极黑色的宝石,深陷在黑色的眼眶中),并且,“他们一言不发/并没说出我们所期待的启示和箴言”——诗歌的最后一句,将前半部分温热的春天,残酷而必然地推向了南极冰雪地带。
诗人最后的宣告,实际上是对现实感的再次指认和抽空,是对人类叠积的各种知识和神话之虚的论实。从这个角度看,泉子貌似缠绵敦厚的诗歌其实极具杀伤力:他的诗歌生成既来自于肉身对于各种事物、现象的体验,也在于对于事物、现象和及其关联的饰物的剔除。
读《杂事诗》,又因几乎在每个句子中都能看到诗人的“在场”,使得诗歌的某种荒凉感生成了“我身如是,我心如是”的疼痛感,是一种风吹肉身、沙磨骨桠的生命诗学。回观泉子诗歌的形体,泉子之所以采用集聚性极强,在视觉和听觉高度延展回环的句式,旨在期望长句子中生长出无数指爪,紧紧锲住地层和肉体,在急骤的流水中呈现瞬刻的凝止,从而立体地刻写时间的不可逆性,并以体温打量生命的亮与暗。
因此,泉子的诗歌看上去也不乏叙事,却和口语式懒惰而讨巧的叙事有别,也与学院文本采集、修辞游戏式的叙事有别, 呈现出一种“随笔”式的精神品相。
何谓随笔,随笔与其他文体区别何在,随笔精神意味着什么?在此文中,我无力对此作出学术论文式的追述与分析,仅摘录穆齐尔在其巨著《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一段话以为定义,这段话出自以上小说主人公乌尔里希之口:差不多就像一篇随笔按段落顺序从不同方向讨论一个事物,但却并不完全地去把握它一样,因为一个完全把握了的事物一下子会失去它的广度而演变成一个概念,他相信,以这种方式他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世界和自己的生活。这样定义随笔,不但表明了随笔的审慎的特性,也契合人的自身有限性的实际境地,以及人在有限性中不断追索和探进的历史行为。
在文学写作的历史中,随笔这种有着悠远历史的文体,这种渗透着小说塑造力、诗歌自由精神和戏剧感的文体,在近现代作家诗人笔下返魂苏醒。无论陀斯妥耶夫斯小说的尖利世界,无论卡夫卡笔下人物的钝感;亦或在昆德拉、格拉克的笔下,如果去除随笔的肌体,这些大师的作品简直会顷刻坍塌。在诗歌坐标上,瓦尔特.惠特曼和艾米丽、狄金森同为美国现代诗歌鼻祖,他们风格迥异的诗体,却同样让随笔式思维借体生花,芬芳动人。在影响世界诗风最甚的法风,自波德.莱尔以降,马拉美、蓝波、洛特雷阿蒙、蓬热、亨利.米肖、勒内.夏尔等等天才,直接拆去了诗歌与散文的界桩,让随笔精神借助“散文诗”这一有着奇怪命名的文体,大放光华。回到中国现代诗歌,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野草》,此地的诗歌景区必然会再降一星。这条脉线隐伏多年,突然近些年杂树生花,于昌耀、西川、欧阳江河、于坚、廖亦武等人的作品中突拔而起,成为这二三十年中国诗歌的重要收获。
随笔式写作,在近现代于不同文化区域喷涌辐射,乃与时变之巨剧有关。直接原因是,“全知视角”在今天已无说服力,而“整饬的韵脚”实在无法于百年嘈声中提纯。“随笔”一词源于法语,其拉丁语本意则为“尝试”“试验”。德国学者克劳斯.海因里希认为,“尝试”这个词指向未完成之物,它对“完成”这一概念提出抗议,因为这一概念将立体的自由至于可疑境地。这就是说,随笔的精神让个体在面对貌似完善、包罗一切的逻辑或世界秩序时具有说“不”的权利。
泉子在向谁说不,泉子为什么要说不?
在泉子的诗歌中,隐伏着另一个泉子——这个泉子的生命形态应是诗人夭故的兄长。也许,我们可以在泉子亡兄这里找到泉子诗歌动力:诗人的探索、观照、诗性推理莫不因“生 死”二字而起。在这个巨大链条中,星辰山水世相人心,莫不忽此忽彼调换阵营辨证说理。泉子的痴,就在于无可所解处求解,又于门户大开、似乎不证自明之处的反推和怀疑。换句话说,泉子诗是一个不断说“不”,直到或许于某处含泪说“是”的过程。他的诗歌既是对“流水”的追逐与不甘,也是对“岸上之人“的深刻同情。
“亡兄死于二十八岁,那年我二十又五,
如今,我已经整整年长他一轮了
如果在今天,我们再一次相见
在北山路的一条长椅旁
或是千岛湖畔一条向山顶蜿蜒的小路上
他是否能辨认出这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呢
而我是否有足够勇气,与一张如此熟悉
如此年轻英俊的脸庞相认”
——泉子诗《二十八岁》
我完整地抄录下这首名为《二十八岁》的诗歌,是想说明泉子诗歌的基本特性,即诗成经验,诗成推测,诗成考问。在泉子的这首诗中,诗人排练了与亡兄突遇的一幕:然而,死亡让一切变得荒诞,“我”已经比亡兄年长一轮,更令人迟疑和痛苦的是,亡兄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而“我”已经两鬓斑白羞与兄相认——诗人的羞惭来自生命的蒙尘污感。熟悉的陌生感在诗句中自然生成,同时花开两枝,一枝指向碌碌于尘世的我,一枝指向因死亡而年轻俊美的亡兄。诗人之于亡兄的情感跃然于诗句,诗人为死亡造成的残酷的美久久不能释怀。再慢一点读此诗,竟然会发现诗人多少有些痴迷于死亡的吸引力和创造力;诗人正是借助死亡之力来言说生命要义。在《生命之壮美》一诗中,诗人直白地言说:“对一个不曾思考过死亡的人/我不知道能跟他说什么”;在另一首诗中,泉子禁不住礼赞死亡:“除了死亡/没有任何别的事物能将万物锻造成一面镜子(《如你一日的逝去》)——泉子在此处使用了绝对的语气;“死亡将万物锻造成一面镜子”——主语的力量和位置不容置疑。万物在死亡的俯视下相互观照,并且折射死亡。泉子还有一首短诗,直接命题为《死亡》,可以目为前一首诗的指南:是死亡赋予了生命以深度/或者说,是事物的有限性/为万物开掘出了那通往幽深而无垠的通道。一部《杂事诗》喷绘了死亡的各种行姿,留辑了死亡的各种调门,测度了死亡的多种流变。一言而概之,即在于指述死亡,认识死亡,反抗死亡,并且为“死亡所照亮的生命”发声,直到“光对漫长的黑夜持续的穿透。”这是泉子诗歌的生命哲学,是泉子诗歌世界呈现的神话图景,是泉子诗歌挥发的基本功能。
在“生与死”这个大主题的烤炙下,泉子其他题材的写作基本被滤干了特征,而趋于普遍性。回到具体写作中,泉子的双重式乃至多重混响式的诗性思辨,使得“江南”这个极具历史地理文化特征的文化符号,只是成为了自古诗歌母题的某种背景。在泉子的诗歌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诗人出生的母地,在中国文化系统中长久占有明灿位置的“江南”如何成为诗歌生长的强力支点——恰恰相反,在泉子诗中,江南风物在绵长、曲折的诗句中尽洗 附丽,成为了与诗中其他事物露水蚊虫一般的直接反映生存之核的镜像:“不要成为他人指尖的一根刺/也不要成为自己手中的一把匕首”(《保俶塔》)——与其把这样的诗句看做中国传统哲学式的平衡表达,或者禅宗式的欲言又止,还不如理解为对“保俶塔”这个名称的抽空和抹平之后的呈述。这就是说“保俶塔”这个出自人类的衍生物,这个可能是由砖木构成的形体,这个在视觉和文化上都具有尖凸形态的无生命物,其实和所有有机生命体一样,需要接受存在和消失的循环链动。在泉子笔下,“西湖”“杭州”等等江南地标,尽管多少留下了些特有的文化肌理,但归根结底奏响的仍然是风吹肉身,沙磨骨桠的时间吹拉之声。泉子即使以这种身处其间的地理写诗,也不过是将江南等同于燕赵、川蜀、西域、青藏等等文化地理区域,其特殊性固然理所当然,但更重要的在于把握其普遍性和共同点。泉子的瞄准器并不在于发扬和广大地理文化特性,而在于强调普遍生存的情景和公理。曾经名重浙江的南宋诗人孙花翁,在泉子笔下的功能主要是用来推理偶然与必然,遮蔽和显现;西湖与此相似,“如果它不能成为我们生命和记忆的一部分”,就无法称之为西湖——显而易见,在泉子的言说中,纯粹的审美和文化地理形态从来就小于生命的体验和言说。在名为《江南》的一首诗中,泉子甚至写到:“而我已厌倦了江南/这细小的、这软体动的脊梁/这词语和词语编织的精致的陷阱。”
回到“随笔精神”上来,一个在精神上不够强大,不能反观自我的人,实在是不配说“不”的。在江南才子普遍的吟哦中,泉子诗歌以一种暗藏的硬度而有别于众人。《江南》一诗强硬地表达了诗人对被文化规训、并过度消费之后,生命形态细小化、脊梁软体化的批判,而最后一句“词语和词语编织的精致的陷阱”,揭开了一种文化叙述的欺瞒,是对一种既定腔调的警醒。诗人很清醒,从大的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所有认知和描述,从本质上讲仍然是虚渺和脆弱的;具体视之,所谓关于荆南的种种“词语与词语”编织,亦不过是浮皮潦草的陈陈相因,距离本质存在和表达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泉子异于他人的地方,是他的怀疑精神、审慎的态度和诗歌逻辑推导很少停留于轻松的、轻易的当口;泉子的写作很少倚恃什么外力进行,而是扎稳马步迎接各种纷至沓来的物象,并统统以“脑后之眼”作出观照和摄影。
泉子诗歌的敞开,使得他并不畏惧处理当下题材。很多时候,泉子甚至迎向时代、社会的种种情景主动判断和发言。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与生活现象、事件、人物、情节短兵相接,先是就事论事,接着越界和跨界,深透其历史和命运的本质,而归于对“存在”这个大命题的思考。《为什么》一诗的启动,从诗人女儿两岁时的发问开始:“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我真的不想上幼儿园!”诗人从生活中的凡常一幕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质问和思考,直指我们社会构成的残忍和虚弱的部分;艰难地讨论人类之爱,并隐隐显现出大于人世的一种显影。而在《反对》一诗中,泉子回忆初来杭州,在视觉记忆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车过庆春路建国路口,玻璃幕墙上/一个着三点式的西方女子剧烈地扭动着身体/并唱着与喊着/尖厉而高亢的声音被阻隔在幕墙背后……“你能听得出泉子独有的那种不疾不徐的叙述腔调,在某个时候突然急转而下,接着嘟嘟囔囔地从活色生香的生活场景,深入到对时间的流量的探讨。
《杂事诗》中不时出现9.11、卡扎菲、经济时代等等热度很高的词语和诗行,但是经过诗人的淬火和提炼都闪烁着一种钢铁或水晶般寒凉气息。简而言之,泉子和皮肤之外的世界的关系,既是一种水深火热、山高路长的互为映照和讨论;诗人又自觉地与之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泉子对所观赏和探讨的事物并没有采用做爱式的贴近和深入,也不是十分理性地远眺旁观,而类似于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极具克制感和分寸感的触握、疏离和吸引;从而制造出另一种“孤绝”。
泉子的作品,经常出现第二人称。在陈述者和你之间的对话、应和和问诘,以及身份处境的互换,使诗歌获得了多重意味的阅读效果。他的声调通常是内敛的、安静的,语言带有一种游移的、未完成的气质。在这样似乎定迟疑着看见、感受和说出中,语言呈具多样复杂的生态样貌。双重以及多重视角,使诗歌兼具贯穿阴阳的可能性。泉子的诗歌常常让我们在“理所当然”的各种神话谱系知识修辞中洞见其苍白和脆弱的一面;又善于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的场景、甚至粗鄙不堪的底部,烛照到生命的庄严、感受到生命的温热。颇显一种“道可道”的执著之力,颇有一种“非常道”的语言嚼咀力。
泉子是一位有着写作母题的诗人。概而言之,他所吟咏的是生命在这个世界的美和损,繁茂和衰亡;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事物无不是风吹肉身之后的种种铭记,而骨桠亦是沙粒必然损磨的种种征象。再说一遍,泉子诗歌的动人之处在于“肉身在场”。其实,诗人对生命的存在,带着一种宿命式的绝望;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诗歌在毫不掩饰地指向荒凉的真境和真相的同时,又因深沉地表达了生命对荒凉的理解和抗争,而这使得人的体温的下降过程在语言中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庄重和美。“你因白茫茫、肃静、寥廓的大地/而喜欢上这刺骨的严寒/这夜空中凝固的浑圆/这因一只乌鸦飞与止/因它的静默与啼鸣而如此不同的宇宙(《冬日》)
我们无从解读亡兄对于泉子诗歌的影响还会有多么深远;但是,现在可以肯定,诗人的注意力凝聚于生命质量的轻与重,生命状态的盈与亡,必定与此有关。泉子式的诗的感叹,无论从世相或生活感受起始,都饱蘸着血液的色彩,涂抹“灵魂”的质地和反应。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谈论灵魂,泉子则在诗歌中制造着处身于时代,又超拔于时代的“孤绝”。在“小叙事”于当今诗歌泛滥之际,泉子的追问和反问犹显珍贵——这是一种具有审慎、反思和锲而不舍的随笔精神。
泉子的语言有着一种经过水洗风吹般的呈述意味。他的呈述,不是机器物理式的精密的零度叙述,而是充溢着人类长久以来以追求和拷问的精神,力图在指述、观察和推理的过程中,让生命呈现风吹沙磨的种种形态,让灵魂在这样的过程中现身。这是一种最本真的追问自我和洞见自我的言说,是一种诗人因历史和现实物事劈面而来,迎身作答,并归捋生死大命题的写作。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写作只能是诗与随笔合体并衣,在保持诗歌悦耳的语调和深长韵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拓展和纵身诗歌固有体例的身量。
向随笔讨回诗歌消凉的肉感,在诗句的长与短之间自由换马乘骑,让目力所及任何事物入诗——泉子的诗歌已有通联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古希腊时代残篇断简的气象——诗人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喜悦,让我们留待时间来回答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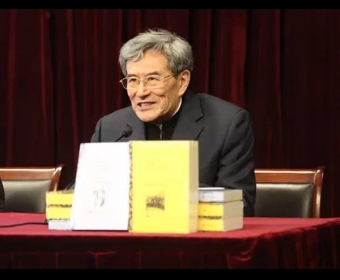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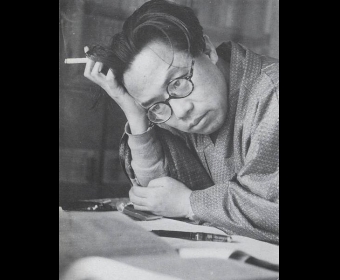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